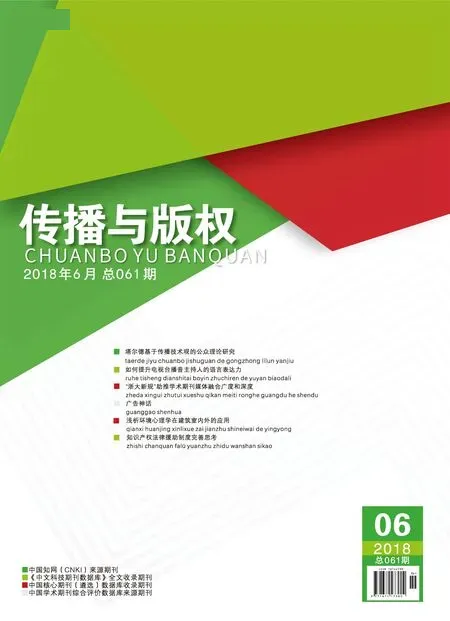自媒體環境下非自愿公眾人物隱私權保護
張永秀
對于如今的網絡環境,杰弗里·羅森提出“全視監獄”的概念,即多數觀看多數。①轉引自胡泳:《眾聲喧嘩:網絡空間的個人表達與公共討論》,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61頁。這一環境狀態的變化與自媒體技術的發展息息相關。自媒體環境下,公民的表達自由得以彰顯,公共空間與私人空間的邊界也漸趨融合。這一方面使得公民的表達渠道更加暢通,社會監督變得更加便利、高效。同時也使得諸多普通公眾成為非自愿公眾人物,加之報道的不專業等因素,其隱私無處藏身。另一方面,公民傳播權的膨脹,使得每個人都處于被圍觀、被侵入的狀態。當普通公眾因卷入偶發事件成為非自愿公眾人物時,其個人隱私信息也就成了諸多網友的“獵物”,更有甚者通過“人肉搜索”等極端的方式對其私人信息和生活進行挖掘和散布。這些都使得非自愿公眾人物的合法權益受到侵犯,但是作為普通公民,其維權成本高,且難度大。因而在自媒體環境下探討非自愿公眾人物的隱私權保護十分重要。
一、自媒體對非自愿公眾人物隱私權的影響
表達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權利自由之一,它是指公民在法律規定或認可的情況下,使用各種媒介或方式表明、顯示或公開傳遞思想、意見、觀點、主張、情感、信息或只是等內容不受他人干涉、約束或懲罰的自主性狀態。②甄樹青:《論表達自由》,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11-19頁。網絡技術的發展,使得“人人都有麥克風”,進而形成更加民主、平等的表達環境。但自由只是相對的,表達自由運用不當,會帶來不良的社會后果。非自愿公眾人物隱私權面臨的風險是自媒體表達自由使用不當的重要注腳。
(一)自媒體侵犯非自愿公眾人物隱私權的方式
1.草根報道。草根報道是自媒體時代公眾行使表達自由權,進行社會監督的重要方式。自媒體使得民眾可以隨時隨地對身邊發生的事情進行傳播,比如在重大突發事件、災難性事件中,身處第一現場的民眾可以實時進行信息的發布,從而引起社會的關注,而這也在無形中使得被卷入事件的當事人成為非自愿公眾人物。但是不可忽略的是自媒體的普遍性、低門檻,使用自媒體的公民媒介素養參差不齊,同時公民沒有進行過專業的新聞報道訓練,對于報道內容的邊界缺乏清晰地認知和職業倫理的約束。
2.對非自愿公眾人物隱私進行過度挖掘。當公民因為偶然事件的卷入而成為非自愿公眾人物時,其便引起了廣大民眾的關注。通常尤其是牽涉道德品質相關的事件,更是會驅使民眾的好奇心。一方面公民強大的信息搜索和曝光能力,有利于事件真相的披露,倒逼事件的解決,但是同時也帶來了隱私的侵犯。人們習慣以道德制高點的立場對當事人進行道德審判,而對其隱私信息和私人生活進行挖掘則是重要的懲罰的方式。“人肉搜索”就是公民常用的最具影響力同時也是嚴重侵害公民隱私權的方式。比如“重慶暴打女司機”案,人肉搜索帶來了案件的真相,同時也帶來了當事人一方的生活被侵擾,精神極大的痛苦。不可忽略的是即使是犯罪嫌疑人也是有自己的人權的,何況在此案中當事人的生活作風與事件并沒有必然的關系,在人格權面前,每個人不管出于何種境地,都該是平等的。
(二)自媒體侵害非自愿公眾人物隱私權的特點
1.侵權更便利,且隨時發生。在傳統媒體時代,由于傳播范圍小,非自愿公眾人物較少,且其隱私不容易被公眾關注。自媒體技術的發展帶來了熟人社會向陌生人社會轉變,每個人都被“彌散的陌生人”包圍,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變得淡漠,進而也變得孤獨,天然的窺私欲以及化解孤獨的需要,助長了人們對于身邊人隱私的窺探欲。而自媒體的發展也使得普通民眾擁有了表達的自由,進而為侵犯隱私提供了便利。相比于自愿性公眾人物,非自愿公眾人物通常都是相對弱勢的,自我權利的保護意識和能力都較弱,因而其隱私權更容易被侵犯,自媒體成為民眾侵權的利器。
2.侵權后果更嚴重。一方面,在自媒體時代,人們對于網絡更加依賴,所有的信息都在網絡空間進行存儲,事無巨細,增加了其隱私被侵犯的風險。另一方面,與傳統媒體時代相比,自媒體時代信息的傳播速度更快,傳播范圍更廣,一旦隱私信息被曝光,便會很快傳遍網絡空間,這使得被侵權者面臨更大范圍的議論和壓力。尤其一些非理性的網友,通過電話、郵件等對其私人生活進行騷擾。在“江歌”案中便是如此,縱使“江歌”的閨蜜是有錯的,但是其依然享有一個公民正常的人格權,但由于其隱私的被曝光,其遭受到了非理性網絡的網絡暴力,電話威脅等不斷發生。此外,相比于自愿性公眾人物,非自愿公眾人物的隱私保護能力、個人心理承受能力、隱私曝光的獲利方面等都處于劣勢,因而其隱私被侵犯后果更嚴重。
二、公共利益——自媒體傳播非自愿公眾人物隱私的邊界
公眾人物的隱私權涵蓋了對自由、尊嚴以及秩序價值的追求,而表達自由與知情權則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著社會的公共利益。①郭玉坤、賀天洋:《公眾人物隱私權的價值與邊界》,《法制與社會》,2014年第29期,第263-265頁。這也意味著在自媒體對非自愿公眾人物隱私權的侵犯實則是公共利益與個人隱私權的沖突。隨著個人權利意識的增強和表達自由環境的寬松,兩者的沖突越來越激烈,因而需要更好的平衡公共利益與表達自由,既發揮自媒體的社會監督作用,又能保護公民的人格權益。筆者以為公眾對于非自愿公眾人物隱私的傳播應該以公共利益為界限,且其被傳播的隱私必須是事件的必要組成部分。
何謂公共利益,并無統一界定,使得公共利益在實際運用中呈現出種種亂象,許多人打著“偽公共利益”隨意侵犯他人權益,使得公共利益無限擴大。正如學者范振國所說,“真正的公共利益必須屬于不特定的多數人的、是有排他性、非競爭性的利益。真正的公共利益絕對不能是被某些少數人壟斷的利益,無論這一小部分人是國家公權力工作人員還是少數私主體。人們要時刻保持警惕、防止公共利益‘泛化’和‘虛化’現象的出現”。②范振國:《公共利益的法律界定與限制研究》,吉林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187頁。相對于自愿性公眾人物,不享有公權力;并未因其公眾人物的身份而獲利;相反大多數情況下非自愿性公眾人物因其公眾人物身份所帶來的是私生活的被侵擾、精神的痛苦等,因而對于非自愿公眾人物的隱私權應該給予更多的保護,對于公共利益的界定更應嚴謹,保證好公共利益限制個人權利的正當性。從而使得公眾的表達自由權在充分發揮的同時,還非自愿公眾人物私生活以寧靜,一方權利的行使不該以犧牲另一方的權利為代價,這樣就顯示公平了。法學方法論中的“利益衡量”原則為我們處理公共利益與個人隱私權保護的沖突提供了很好的參照。
利益衡量簡單而言即是在法律法規的適用時,法官需要根據當事人的利益狀況進行具體的選擇,使得沖突的權利之間互相妥協,從而雙方權益的動態平衡。正如學者齊曉丹所說:“權利的行使都要在一定的范圍之內,但是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不可能采用數學的方法,畫一個四邊形或者多邊形就可界定。權利與權利之間的邊界也在不斷地發生變化,或者是隨著社會的發展,權利的范圍不斷擴張或者限縮;或者權利之間本來即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③齊曉丹:《權利的邊界:公眾人物人格權的限制與保護》,法律出版社,2015年,第217頁。當面對公共利益與個人隱私產生沖突時,并不是一味地認為公共利益優先或者個人隱私保護優先,而是對雙方權益進行衡量和比較,當個人隱私權益較大時,則優先保護個人的隱私權利;而當公共利益的權益較大時,在保護公共利益的同時,對于個人隱私進行合理適度的保護。
三、自媒體時代保護非自愿公眾人物隱私權的策略
(一)探討“被遺忘權”的本土化發展路徑
在自媒體時代,相比于自愿性公眾人物,非自愿公眾人物更應享有“被遺忘權”,讓自己的相關隱私等信息被刪除,被遺忘于網絡空間。因為自愿性公眾人物通常要么享有公權力,要么因其身份可以從社會中獲得財富、聲望等收益,而一般而言非自愿性公眾人物既不享有公權力,也不像明星等群體能夠從社會獲得財富等資源;從權利救濟的角度而言,自愿性公眾人物一般有更多的資源、渠道以及話語權,比如影視明星,當期權利被侵犯時除了法律途徑,其還有強大的公關團隊,能夠幫助其盡快消除影響。而對于非自愿性公眾而言,其是由于重大的新聞事件等的發生偶然進入公眾視野,一般來說其處于弱勢地位,缺乏相應的能力、資金、渠道去應對侵權帶來的影響。如此一來非自愿性公眾人物享有的權利與其承擔的壓力和義務明顯的缺失公平。而如今網絡技術的發展,使得網絡空間成為數據的儲存庫,成為人們言行的記憶庫,也是社會的記憶,處于網絡空間的數據隨時都能被人們進行搜索、轉發等,造成二次傷害。
而我國雖在“被遺忘權”上有了積極的法律推進,但目前而言并沒有明確具體的界定,比如數據的管理主體是誰、刪除范圍多大等,我國作為最大的網絡用戶國家,“被遺忘權”雖然還存在諸多爭議,但是處于弱勢地位普通網民提供了捍衛自己隱私權益渠道,具有重大的意義。因而如何借鑒歐盟、美國的經驗,規避技術發展的負面影響,尋求“被遺忘權”的本土化發展是個重要的課題。
(二)培養公民適合自媒體時代的媒介素養
自媒體改變了傳統媒體單向傳播的模式,普通民眾既是信息的接受者,也是信息的傳播者,這其中不免摻入個人的情感宣泄、虛假信息等。同時資本控制以隱形的狀態存在與自媒體之中,主要是網絡炒作、網絡推手以及一些公關團隊、網絡水軍。整個網絡環境中形成了自我披露、鍵盤俠道德綁架等文化;網絡環境中信息量龐大,而且紛繁復雜,需要民眾在進行信息傳播時具有分辨力、判斷力,否則會造成傳播權的濫用,侵權現象的發生等。而且民眾的媒介素養不足也會使得新的媒介技術不能很好地服務于社會,使得資源浪費,因而在自媒體時代我們需要培養公民與之相適應的媒介素養。
筆者贊同學者彭蘭的觀點,她認為社會化媒體的媒介素養主要應體現在:其一,媒介使用素養;其二,信息消費素養;其三,信息生產素養;其四,社會交往素養;其五,社會協作素養;其六,社會參與素養。①彭蘭:《社會化媒體時代的三種媒介素養及其關系》,《上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3期,第52-60頁。從總體而言,筆者認為自媒體時代普通民眾的媒介素養即是要求其對于媒介的使用在掌握基本的技術之外,更應承擔起作為公民的社會責任,采用合理合法的方式行使自己的權利,使得信息的發布、網民之間的交流高效有用;對于涉及他人的信息能夠謹慎處理。尊重他人的合理合法的權益,行使自身權利的同時不侵犯別人的隱私等權利。
對于自媒體時代公民的媒介素養培養,可以有以下幾種途徑:其一,對其進行新聞傳播的基本規律、基本理論的普及很重要。民眾掌握了基本的新聞傳播理念,當其處于新聞事件的第一現場時更有利于新聞信息高質量的發布與傳播,也有助于侵權現象的減少。其二,將媒介素養進行分層,強調不同層次的媒介使用者應該有不同的媒介素養要求,還要有不同的知識、技能、能力和態度目標。②盧峰:《媒介素養之塔:新媒體技術影響下的媒介素養構成》,《國際新聞界》,2015年第4期,第129-141頁。其三,借鑒西方的經驗把媒介素養教育納入國家的教育體制當中,讓學校教育幫助培養民眾的媒介素養能力,從而更好地促進網絡空間的信息流通和交流。
(三)用“波特圖式”分析法應對自媒體傳播侵犯隱私權的倫理困境
自媒體環境下,非自愿公眾人物隱私被侵害頻發,且有些新聞還時常引起各方的爭議,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爭論的各方采用不同的價值觀和倫理傾向。“波特圖式”分析法為進行新聞傳播的主體面臨倫理困境時提供了解決思路,以便更好地處理隱私權與其他權利的沖突。
“波特圖式”分析法是美國學者博士拉爾夫·波特所設計的一種道德推理模式,其主要包括四個方面:定義、價值、原則和忠誠。也即先對所面臨的問題進行梳理,厘清所面臨的情景,而后進行價值的篩選和倫理原則的選擇,最后得出自己所忠誠的那一方,從而解決自身所面臨的倫理困境。在這一方法的運用中,西方的一些主流的倫理原則為我們提供了十分有價值的參考,倫理的約束有助于在進行傳播時衡量隱私利益與各方利益的沖突。這些倫理原則主要包括:其一,亞里士多德的中庸之道;其二,康德的絕對命令;其三,穆勒的功利主義;其四,羅爾斯的無知之幕:“只有當忽視一切社會差別時,爭議才會出現”。其五,猶太教、基督教將人作為目的,“像愛自己一樣愛人”。③顧承衛:《論路易斯·愛爾文·戴伊的媒介倫理觀——翻譯〈媒介倫理學〉札記》,《涪陵師范學院報》,2007年第1期,第128-131頁。
“中庸之道”的思想理念給予我們的啟示在于:完全曝光非自愿公眾人物隱私或者該隱私即使是新聞事件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完全不涉及的極端做法是不合理的,其要么損害隱私權,要么損害民眾的知情權等,更為合理的處理方法是采用折中的方式對利益進行衡量。“絕對命令”的關鍵在于強調個人的責任意識,將個人的道德理念上升為普遍的適用準則。在面對網絡空間的隱私消費、隨意傳播他人的隱私亂象時,人們應該尊重他人的人格尊嚴,建立自身的責任感,用合理合法的方式傳播和接受信息。“功利主義”的原則主要在于強調社會的公共利益,當面臨個人隱私保護與其他權益的沖突時,我們應該將不損害公共利益作為信息接受和傳播的原則。“無知之幕”的準則主要強調人與人之間的平等,并給予弱勢群體以關懷。與我們的啟示即在于在進行信息的傳播時,我們也需要考慮當事人的處境和精神痛苦,比如如今盛行于網絡空間的“人肉搜索”,雖然一方面其對于監督腐敗起到過積極作用,然而對于一些弱勢群體或者比如一些非自愿公眾人物等則會造成莫大的傷害,侵犯其生活安寧等隱私權益。而“愛”的理念則主要在強調人們的人文關懷與善良對待他人。我們雖然“人人都有麥克風”但不該惡意散布他人的隱私。造成他人的人格尊嚴的損害。在這些倫理原則的基礎上,結合“波特圖式”的分析方法,有利于平衡表達自由與隱私侵權的沖突,使得公民更好地行使自身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