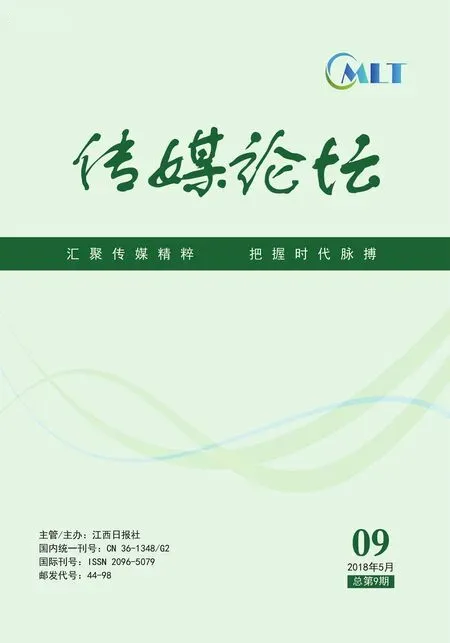論“山寨文化”發展與新媒體網絡傳播的關系
顏財斌
(東南網,福建 福州 350000)
再說“山寨”現象。而今流行的“山寨”最早出自于電信行業,是指某些科技公司使用技術,仿造市場上最新最受歡迎的手機樣式,進行整合創新,模仿生產出質量不錯又價格低廉的手機。由于這種手機或不是經過官方批準生產的,或與主流不合,或相識度極高,因此也被戲稱為“山寨手機”。由山寨手機開路,“山寨”一詞風頭一時無二,似乎只要是與模仿有關的,幾乎都能被冠以“山寨”產品的稱號。手機、包包,如果我們不給它們冠上山寨的頭銜,它們大可以被稱為仿冒品,也就是我們通常說的假貨。撞臉明星、電視節目、電視劇之類的,我們也大可不必把它們當成山寨行為,它們就是模仿再加工生產的產品。
而真正導致這個山寨風越刮越猛的原因就在于網絡傳播獨特的優越性,再加上近幾年“草根階級”“平民精神”的盛行,山寨簡直成了“平民文化”的代名詞。隨著“山寨文化”從網絡話題一躍成為全民話題,我們不得不說,這么多年的時間,“山寨”現象儼然已經成為了一種大眾休閑娛樂文化,盡管它依然倍受爭議。
一、網絡孕育了“山寨文化”
且說互聯網給大眾生活帶來的便利,我們可以足不出戶,通過鍵盤和鼠標順利完成一天的工作任務。從最初的電子郵件,到后來的遠程教育,再到網上購物,溝通、學習、生活這三個生存最基本的保障,我們都只需要一臺電腦就能輕易完成。而網絡作為一種與廣播、電視、報紙并列的媒介,其優勢還體現在信息交流系統的交互性、方式的綜合性、運行的實時性、范圍的廣泛性,以及信息內容的開放性等特點。正是因為網絡具備了這些傳統媒介所不能媲美的優越性,所以,網絡才成為了“山寨文化”滋生繁衍的土壤。
(一)網絡傳播過程由單向變為雙向
互聯網時代,網民既是信息的接收者,也是網絡信息的發布者。當傳統媒介還沒引以為然的時候,網絡上就開始了對山寨產品的傳播討論。網民們可以在自己的個人空間(個人日志、博客、微信朋友圈、公眾號等)自由發表購買山寨產品后的心得體會,直接表明自己的看法和意見。然后,其他網民便隨著開始關注這一話題并與之互動。雖然,傳統的大眾傳播媒介已經很努力地在打破單向傳播的這種模式,而且也已經取得了不錯的效果。但是網絡傳播獨有的這種“實時”的交流方式帶來的巨大沖擊力是不容小覷的。
(二)網絡傳播者:嬗變的“把關人”
網絡傳播過程由單向變為了雙向,這也就意味著受眾傳統的角色已經發生了位移,在網絡傳播中,只要具備發表言論的可能性,受眾就可以轉身變為傳播者,參與到整個傳播過程中。
無障礙式的雙向信息傳輸,也宣告了“無人把關”的傳播時代來臨。在這樣一個大而雜的網絡體系中,只要有一個人關注了山寨產品或是山寨現象,隨之而來的肯定是一大批的關注者,而在這個一大批的關注者中同樣肯定會誕生一大批的二次傳播者。試想,如果傳統的“把關人”還存在的話,一旦“山寨”這個詞匯被把關人給淘汰,就不會引發相應的蝴蝶效應。而恰恰因為互聯網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把關人,傳播者也發生了相應的位移,這才讓“山寨文化”之風盛行有了繼續往前發展的契機。
二、網民心理特征與“山寨文化”形成的聯系
為什么“山寨”可以借網絡成功上位,華麗變身為一種大眾文化呢?源自于:網民的好奇心理。在網絡這個浩瀚無垠的信息系統里,我們總是能不斷地接觸到一些新鮮的事情。當山寨作為一個網絡流行語出現的時候,網民們甚至都不能容許自己不明白這個詞語的身世來歷。如果真不明白,絕大多數的網民都是會去認真查閱相關信息,去了解清楚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
(一)網民的求真心理
“山寨趙薇事件”曾在網絡上火極一時,網上莉莉·艾倫和趙薇的照片放在一起真是相差無幾,瞬間,便有很多網友發表言論說中國山寨火了外國人,并呼吁大家把山寨精神堅持到底。對于娛樂圈的事情,很多網民都是本著娛樂的精神一笑置之,當然無所謂莉莉·艾倫到底是什么人。但是好像已經形成了這么一個怪圈,只要一跟“山寨”掛上名,網民們似乎就很樂于“湊熱鬧”。可想而知,網民們無窮的想象力讓網絡上關于這件事的標題立刻變得五花八門了,要多怪異就有多怪異。事后很長一段時間,有網友突報莉莉·艾倫早就已經是成名的女歌手和時尚偶像了。
(二)網民的匿名心理
匿名性是互聯網的特性之一,網民們往往會用一個昵稱來隱匿自己的真實身份。這也就意味著,在一定程度上,網民的言論是沒有社會道德和價值觀約束的,一切都可以依照自己的好惡來進行,選擇自己想要關注的信息,發表自己想要發表的言論,只要不會被自動屏蔽。當“山寨”從一種流行語漸漸延伸到人們生活中去的時候,在網絡上形成了正反兩方的辯論,其參與人數更是無可估量。有一部分網民認為,山寨現象從其本質上就是一種盜版文化,是對知識產權的侵犯,是不值得被推崇的,也有人則是站在平民草根階級的角度為“山寨文化”辯護,稱其是平民階級的文化,它更多的是一種娛樂精神,并非是對主流文化的攻擊和背叛。
(三)網民的娛樂心理
互聯網,除了用來學習和獲取信息之外,最大的功能恐怕就是休閑娛樂。要說“山寨”從商業產品的前綴,發展成為“文化”的前綴,整個變化過程體現出來的就是網民的娛樂精神。在網民的內心深處,“山寨”是靠“仿冒品”起家的,不管什么東西,只要冠上“山寨”的頭銜,都似乎包含著對主流文化的一種消解。正是這種原因,所以它便理所當然地成為了草根階級堅持守護“山寨文化”的堅強后盾。
評選“山寨諾貝爾獎”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乍一看,其實這些都是段子,本可一笑而過,但是卻被網民們津津樂道,甚至還設置評選比賽,從網民們熱心投票分析研究“山寨諾貝爾獎”這件事情開始,到最后挑出最具代表性的獲獎者,就足以證明網民的娛樂心理在網絡傳播中舉足輕重的作用。
三、網絡言論的特點有助于推動“山寨文化”的發展
要說網絡言論的出現最重大的意義就在于它給了所有人更多的話語權和知情權。當“山寨”以壓倒式的速度席卷人們生活的時候,我們才后知后覺地發現網絡言論的力量是如此之大。從最初的山寨手機,到后來的山寨明星,山寨電視劇,山寨電影,山寨綜藝節目,到現在的山寨搜索引擎,山寨諾貝爾獎等等,山寨幾乎無處不在。而所有的這些,也幾乎都是大家自發組織的,可以說是“集體智慧”的結晶。
四、規范網絡輿論,使“山寨文化”與主流文化走向融合
假設要給“山寨”定義的話,可以從兩方面加以理解。一是物質層面,也就是“山寨”這個詞語的字面意思,表現為山寨產品,其特點表現為仿造性,快速化,平民化。第二是從精神層面上,即表現為“山寨文化”,包含了其折射出的民眾的社會心理、審美取向和社會思潮的出現、價值體系的新建等。顯然,精神層面折射出來的意義正是研究“山寨文化”的核心。按照“存在即合理”的哲學觀點,我們再來探討山寨文化到底是該繼續生存還是消亡毀滅似乎沒有多大的意義,但是如果通過規范網絡輿論來使“山寨文化”與主流文化走向融合才是一個雙贏的策略。
(一)議程設置功能
我們知道,大眾傳播有一種“議程設置”的功能,通過各種媒介的新聞報道和信息傳達活動以賦予各種“議題”不同程度的注意力,來影響公眾對已發生或正在發生的“大事”進行分析判斷。然而對于互聯網這個“把關人”作用不占據主導優勢的媒介,我們同樣可以有意識地設計話題和主題以供網民們了解、討論。對于“山寨”這個曾經一度成為最火網絡詞匯,我們要清醒地看到利弊兩個方面。
不得不說,有些山寨產品確實侵害原創者的利益,是對原創者的巧取豪奪,造成了不公平的競爭秩序。市場經濟的特征就是競爭,而有些山寨行為則破壞“游戲規則”,甚至藐視法律,通過山寨假冒品牌、制售劣品、剽竊技術、仿造證照等不正當競爭手段搶占市場,造成優而不勝,劣而不汰的現象,最終造成損害消費者利益的惡劣后果。這些年來的假冒偽劣產品泛濫,已經泛化到人們的吃、穿、住、行甚至醫藥方面,受害報道也不絕于耳。對于部分山寨產品,我們需要謹慎行事,甚至于敬而遠之。
所以在“打假”和維護知識產權這方面,網絡就可以發揮它海量信息和最強時效性的優勢,給公眾提供“議題設置”,以便更好地維護整個社會正常有序地發展,維護公眾最基本的利益。
(二)提供真實的新聞報道
畢竟,網絡新聞報道的真實性確實還不能與傳統媒介相提并論。曾經某論壇上看到過“山寨一條街”的帖子。帖子說一條掛滿“山寨”招牌的商業街驚現南京文安街,曲同氏(假冒屈臣氏)、必勝糊(假冒必勝客)、李明(假冒李寧)、巴克星(假冒星巴克)、哈根波斯(假冒哈根達斯)等等各大品牌都慘遭毒手。至于這條新聞到底是真是假,盡管最終也沒有得到準確的答案,但是,卻顯著地增加了大家對“山寨”這個詞匯的感受。或許“山寨”已經擺脫了產品和現象的說法,慢慢演變成了一種行為,一種全民娛樂心理。
(三)重視“意見領袖”的作用
網絡上的“意見領袖”可以是網民當中專業權威的發言人士,也可以是網站特派的負責人。對于網絡上沸沸揚揚的議題,網絡媒介可以借鑒傳統媒介的一些方式方法,比如邀請專家學者發表權威觀點。畢竟,一個有理有據的言論好過風風火火的七嘴八舌。
五、結語
不可否認,“山寨文化”起步于對“主流文化”的模仿,畢竟,當主流已經建立起它的品牌,甚至已經形成市場壟斷時,模仿并嵌入幾乎是唯一的方法。但是模仿歸模仿,我們更應看到的是山寨文化的創新性和超越性。
總之,“山寨文化”是一個引人注目,也是引起非常大爭議的一種現象。它幾乎是中國特有的,而且現象之普遍、規模之大、參與人數之多、內容之龐雜來看,也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而在互聯網這個大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山寨文化”本身就帶有下里巴人的氣息,它的平民、草根、仿造和創新是最應該被我們所關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