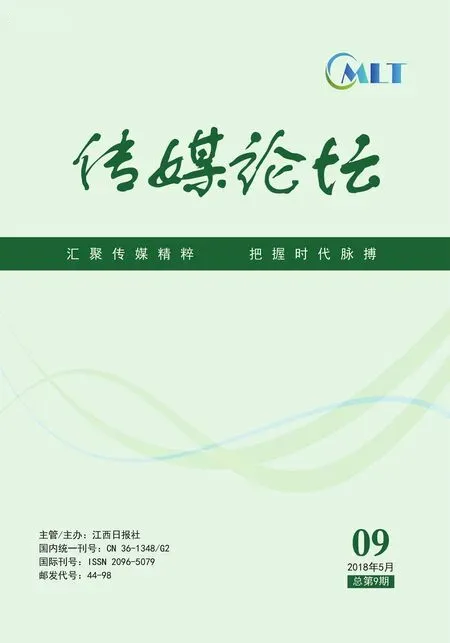“知識付費”模式下看傳統媒體的機遇和挑戰
——以《三聯生活周刊》為例
吳麗婷
(浙江樹人大學,浙江 杭州 310015)
伴隨著中國移動支付的普及和新媒體的快速發展,大眾生活節奏加快。與之不相稱的是獲取信息內容深度的缺失,碎片化時間的分散無法使知識很好地內化,用戶對于優質內容付費的認可度和意愿也隨之提升。如何利用碎片化時間獲取精確有深度信息成了當下的痛點,知識付費以線上支付獲得內容的形式重新回歸,傳統媒體轉型或許能有契機。
一、知識付費模式及其發展現狀
對于業界和學界一直很火的詞“知識付費”,主要是指內容創造者將書籍、理論知識、信息資訊等知識與自身認知積累融合,并對其進行系統化和結構化后梳理轉化成標準化的付費產品,借助知識付費平臺所搭建的付費機制與業務模式傳遞給用戶,以滿足用戶自身認知提升、階級歸屬、豐富談資等需求的創新產業形態。其實知識付費從嚴格意義上而言并不算新鮮事物,傳統意義上的付費買書、訂閱報刊等都算是對知識的付費,但目前而言的知識付費多是特指在互聯網領域下內容交換的新形態。
(一)知識付費形態及模式
自知識付費得到關注以來,互聯網領域的產品形態呈多元化展現,目前主要產品形態分為:音視頻直錄播、圖文分享、在線問答、一對一咨詢等,得到、知乎、喜馬拉雅FM、果殼等是體量較大的入場者,各自發展的模式也不同。根據歸納,目前知識付費主要以兩大模式為主:單次付費模式和長期付費模式。單次付費模式指用戶查看某一特定內容時僅需付費一次即可獲得。以分答APP、微博、悟空問答為例,付費即可獲得想要的答案;長期付費模式指用戶根據自己的喜好對某一產品主動訂閱。這一訂閱模式較為穩定,付費價格高,受眾對媒介產品的黏性較強,例如得到、豆瓣等。根據易觀千帆發布的《2017中國知識付費行業發展白皮書》中還提到一種模式是打賞、授權轉載付費模式,即指用戶查看內容后或要轉載時為內容付費。以簡書、公眾號打賞轉載為例,可見知識付費發展空間極其廣闊。
(二)知識付費的發展現狀
2016年,業內人士稱為知識付費元年,知乎、果殼(在行分答)、喜馬拉雅FM、得到及其他知識付費平臺相繼出現。2017年各大互聯網媒介平臺紛紛入局,生產者和消費者迅速增多,智能推薦、社交渠道和線下場景逐漸引入。知識付費向一個更成熟、更多元的產品形態,乃至商業生態進化。隨著2018的到來,“知識付費”這個概念已經邁入了它的第三個年頭,信息焦慮更顯嚴重,知識付費的用戶迅速增長,知識付費產品面臨井噴。從2018年“網易開年大課”開始,以社交場地為主的知識付費野蠻生長。從現實發展形態可得出,知識付費的風口正在到來,優質內容必然成為主流選擇。
二、傳統媒體優勢分析
回顧新媒體的發展,短期內改變了受眾的閱讀習慣,碎片化時間侵襲著人們的生活。傳統媒體因其龐大特性不能很好地滿足受眾需求。在嘗試轉型的路上,多數在悄然落沒。互聯網將大眾本就有的付費意識培養成了免費意識,信息時代前進到一定程度時,會出現物極必反的效果。人們發現免費帶來的是信息的極度泛濫,我們的周圍成為信息堆放場,卻很難找到對自己有用的信息,時間和效率成本的攀升,使內容深度回歸成為必然。在這樣的情形下,一直唱衰的傳統媒體或許能夠靠這場知識付費再度入局。畢竟,傳統媒體在知識付費方面有其獨到的優勢。
(一)在內容深耕方面有一定的積累
傳統媒體專業化程度高是社會各界的共同認知,這個專業化的背景是它最好的信任背書,尤其是經歷了幾十年的沉淀,優勝劣汰下能存留下來的都是有一定口碑和群眾基礎的。例如《三聯生活周刊》很好地發揮了它這方面的優勢,取得了成功。所以傳統媒體可以在提供基礎性公共內容基礎上,深耕跨界度高的、精粹度高的內容,在大眾化市場完成本職,在分眾化市場實現盈利。
(二)把關人角色的認可度高、公信力強
當下信息的泛濫,信息魚龍混雜,受眾每天都要處理互聯網上大量無序化的信息,知識爆炸時代使得人們對信息獲取渠道有了更高的要求,信息“把關人”的角色越來越為社會所需,為了能尋求高效準確真實的信息,人們會開始有了付費意識,對權威的渴求比以往更高。傳統媒體多數屬于權威認證過的機構組織,其生產內容本身把關嚴謹,人們的信任和依賴感高于互聯網媒體。與一些平臺型媒體內容的浮夸和不實相比,有著其不可替代的一面,可以憑借此做好付費內容。
(三)政府依托、頭部力量集中
如上一條我國的傳統媒體基本上都是國有的,所以大方向的輿論都是政府在引導,就連新媒體上的一些官媒,也是傳統媒體衍生出來的分支。也因此能集中到更多的專業人士,提供更垂直化的需求。而這些恰恰是新媒體所不足的,傳統媒體如果借勢,應發揮這方面的資源優勢。
(四)有可能提供更為豐富、系統的知識,讓知識回歸它本身,而不是只“知”不“識”
自知識付費興起之時,付費內容泛濫后其效果一直飽受爭議。用戶每天花10~20分鐘的碎片時間來聽課,看似是節省了時間,但實際上恐怕只能做到“知”,很難做到“識”。這正是目前知識付費市場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這也意味著市場空白仍很大。而傳統媒體自身的知識架構及體系較為完善,對優質內容的打磨有一定的優勢,更可給消費者提供一個系統性的內容需求。
三、《三聯生活周刊》的突圍
如上,知識付費對傳統媒體而言確實是一個機會,《三聯生活周刊》作為我國老牌傳統雜志,借助知識付費實現突圍。《三聯》在2017年上線了“中讀”,旨在基于20多年的積淀,從紙刊到方寸屏幕,從文字到聲音,開始做音頻付費,受到眾多讀者的歡迎。2018年春節,年卡“68元”的活動在朋友圈刷屏,原定銷量首日中午就完成,APP流量翻了不止一倍,《三聯生活周刊》實現了一個大的跨越。對它的解讀,也許可以更透徹地理解知識付費對傳統媒體轉型蘊含的新機遇。
(一)認識到知識體系的重要性,封面故事構建起知識地圖
它從一開始便將封面作為一個大的亮點,設立了“封面大使”和“封面書單”等兩個核心欄目,將其做成了一個新聞閱讀產品和知識鏈的產品,在測評期中,欄目訂閱超過了5000份。封面故事可謂是三聯“IP中的IP”,消耗著編委會最多的智力討論和人力成本,過去僅停留在了文字產品的階段,中讀APP將其衍生以提供更為多元和系統的知識服務。
(二)立足于IP本身,和讀者講故事和情懷
《三聯生活周刊》本身就是一個很強大的IP, 1995年恢復刊物至今,已經有了多年積累的品牌優勢以及潛在粉絲。在傳統媒體日漸式微的今天,它能深諳用戶心理,春節期間的年卡以“十年故事內容”打動了很多人,造成了刷屏。能成就《三聯》現象的,還是《三聯》本身。
(三)意識到新媒體時代渠道的重要性,與時俱進
《三聯》能及時調整自身,堅持“內容為體,服務為用”。從上線“中讀”到“年卡”刷屏,都能很好地做出對策,及時入場。并能虛心的和互聯網公司學習和取經,走自己道路的同時又放低姿態,利用分銷機制,打響了春節后社交圈的付費戰爭。
四、傳統媒體的轉型新機遇
傳統媒體從生產形態上來說屬于文化出版業。文化出版第一次產業變革發生在1995年,亞馬遜獨樹一幟,首創網絡書店,改變了原先支付、物流、倉儲的模式,成為線上圖書零售巨頭,從此互聯網發展迅速,傳統媒體沒能趕得上時代開始落后。而現下“知識付費”的回歸,是文化出版業的第二次產業升級,有識人士已窺見這是傳統媒體轉型的一次機遇。傳統媒體如若能借勢知識付費,可以集傳統意義上經紀人、出版商、批發商、零售商于一體,《三聯》便是最好的借鑒,優質內容戰勝時代焦慮成為大勢所趨。
五、結束語
業內人士稱從2018年開始是“后知識付費時代”,但是針對絕大多數三四線城市來說,知識付費還處于初級階段。其帶來的是機遇更是挑戰,傳統媒體應當思考好如何把握好知識付費的風口,憑借自身的優勢,實現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