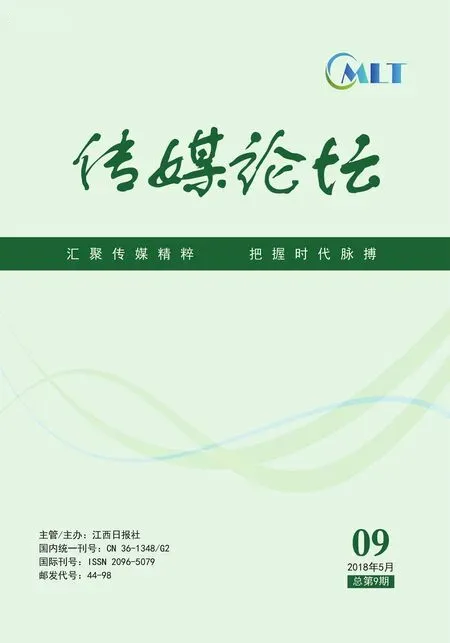《國家寶藏》的經營策略研究
鄭錦晶
(蘭州大學,甘肅 蘭州 730000)
激烈的競爭迫使媒介組織不斷因時因勢調整經營策略,在電視領域不乏成功鮮活的媒介經營案例,尤其是某一王牌欄目的誕生與發展頗值得研究。當下,我國電視綜藝節目眾多,娛樂類占比極大,但缺乏有深度和內涵的節目,《國家寶藏》作為一檔兼具歷史知識和綜藝形式的節目,能在娛樂綜藝當道的市場突圍取得不錯的反響,本身就值得研究。“在各經營領域都在強調資源整合、集約經營以達到效率至上、成本優先的大背景下,如何利用傳統媒體既有的優勢資源,同時以合作的思路以全面激活媒介經營的各個環節,是傳統媒體需要解決的關鍵課題之一。”《國家寶藏》就是整合利用資源的典型,本文著重分析其“紀錄+綜藝”的形式,從中抽象出其成功的獨特之處。
一、《國家寶藏》異軍突起
2016和2017年,被視為綜藝文化節目的起勢之年,繼《中國詩詞大會》《朗讀者》之后,2017年末,央視推出的《國家寶藏》掀起了又一波高潮,這一精心打磨的力作借助綜藝形式推送了歷史文物,普及了歷史知識,傳播了傳統文化。該節目定位為文博探索類節目,自12月3日起每周日晚19:30與觀眾見面,開播兩期在豆瓣上就有2萬多人評價,收獲9.3的評分。節目尚未播出前,宣傳片和主題曲一曝光即引發熱議,不少網友在領略了其中的燈光和舞美后驚呼,央視的這檔新綜藝“燃爆了”,節目名甚至沖上新浪微博熱搜,在以年輕觀眾為主體的B站上更是被置于“推薦”界面。隨著節目播出,其熱度持續發酵,“梁家輝港普”“王凱”“乾隆農家樂審美”等更是霸占熱搜榜,“微博的超強互動性與裂變式的傳播特性讓節目在新興網絡平臺上迅速升溫。”
《國家寶藏》首播平臺是央視綜藝頻道,盡管主創團隊強調不追求收視率,但它已擁有較高收視是不爭的事實。除央視網外,騰訊、優酷、愛奇藝、B站也同步播出,首播期間,前三集的均播放量在700萬左右。截至目前,B站上的十期節目總播放量達1550多萬次,彈幕達107萬條,與此相關的片段視頻更是推陳出新。節目的播出俘獲了大批觀眾,豆瓣上先后有5萬多人評分,形成了良好的口碑,這些受眾成為節目的“自來水”,其中尤以年輕人居多。
二、內容經營:優質核心是發動機
“內容是吸引的實質,也是傳播的基石,而互聯網思維的關鍵在于如何將‘以用戶為中心做到極致’。”《國家寶藏》傾心于對內容的經營,通過分析節目本身即可窺見一斑。
(一)經營節目內涵
良好的媒介經營管理,能給品牌傳播帶來良好的傳播效果,“還可以延伸到更為富有意義的文化內涵積淀。”《國家寶藏》開場語是“讓國寶活起來”,其中心是被譽為國寶的文物,整個敘事框架也圍繞它展開:邀請史學界人士和權威機構推薦、詮釋文物;設置特定時代情景,由明星演繹文物前世;尋找當代文物守護人講述其今生故事,以綜藝的外衣,通過演繹和講述來傳播文物知識,傳承中華文化。
隱含于節目中的內涵之一是對傳統文化的認同感,這是“一種主觀意識和態度”。當文物以“前世傳奇”“今生故事”相結合的形式呈現于眼前,觀眾看到的是精美絕倫的文物,更是凝聚其中的古人智慧,會為中華文明喝彩,會對傳統文化有一種認同感。其次,對文化傳承理念的經營。在內容制作中使用年輕受眾熟悉的方式,在較活潑的語境下講述文物故事,激起年輕一代的興趣和認同,進而傳承傳統文化。節目在文化普及的過程中也傳遞著愛國的價值觀,如第三期在介紹云紋銅禁的制作時,提及國際通行的熔模鑄造法的核心是我國的“失蠟法”,這種對比敘述其實也是于另一面培養觀眾的愛國情結。
(二)經營制作手段
《國家寶藏》與國寶文物相匹配的硬件設施是精心考量的,從舞美燈光到環節設計,從明星選擇到后期制作,都是“高配”,正如制作人于新玲所說:“我們的文物,配得上最高貴的儀式感。”整個舞臺將獨特的古典韻味與現代科技結合:利用360度全息幻影成像系統,實現三維畫面的3D立體顯示,具有強烈的縱深感;9根LED冰屏柱利用其位置調整和透明質感的呈現,用變幻的造型“繪制了‘內與外’‘虛與實’‘前與后’的多維、立體的舞臺空間”;加之燈光的“動靜皆宜”,整個舞臺給人極大的視覺沖擊。現場利用立體音響效果,使用多種音效,配以契合文物及時代特質的背景音樂,在聲畫融合中呈現一場視聽盛宴。正是基于高端的設備和出色的剪輯,才有了精良的節目。
三、形式經營:量體包裝是助推器
(一)打磨節目形式
《國家寶藏》主創團隊經過兩年打磨才有了日趨明朗的模式,對比央視前期的文博節目,不難發現其知識性和娛樂性的比重失衡。2003年推出的《鑒寶》以演播室現場鑒定的形式辨別藏品真假,兼有收藏的軼事及專家評述,其娛樂性更重;2004年播出的《國寶檔案》在介紹文物時,以主持人講述和實地拍攝的方式呈現文物故事,但其單一的影像播放和主持人講述,使得節目過于死板,與觀眾的互動性減弱。而“網絡媒體的出現大大提高了受眾的地位,并培養起以受眾為中心的傳播習慣。”《國家寶藏》深諳其中之道,它邀請九大國家級重點博物館館長提供專業知識;邀請明星擔當“國寶守護人”,經典再現,這就實現了對嚴肅的專業知識和輕松的綜藝氣氛的調和,不再偏重一隅,滿足了“新”受眾的口味。
(二)另類表達方式
節目主創人員用獨特的視角令“冷門”不再“冷”,他們認為“任何一個好節目都是講故事”,這檔綜藝摒棄了專家照本宣科的陳述,避免給觀眾帶來上課感;由明星擔任“國寶守護人”,講述文物的歷史浮沉,由學者和文博人員講述國寶的當下,并將二者以某種線索相連。這種獨辟蹊徑的思維,從另類角度解讀文化資源,為節目制作構建起基本的敘事框架,而這恰恰是信息傳播者制作媒介產品尤為重要的一步。
另一方面,參與錄制的文博專家及明星的認真嚴謹為節目內容增色。《國家寶藏》將文物置于特定情景和歷史背景下,由明星通過小劇場的形式呈現文物的前世,由與之相關的專家學者講述國寶的今生。在這一過程中,文博人員會適時穿插文物知識,優秀的演員憑借精湛的演技和自身對文物的理解為觀眾帶來千年前的逼真“場景”,如梁家輝飾演司馬光演繹出其所護國寶石鼓的前世傳奇,段奕宏化身“越王勾踐劍”,以“劍”的身份為國寶代言;賈湖骨笛研究者蕭興華老師眼泛淚光地將珍藏的骨質原料交于學生并殷殷囑托……這些片段的精彩演繹和學者對文物的虔誠與熱愛豐富了節目內容,在體現綜藝感的同時更有一份厚重感。
四、媒介經營:內外聯動是引擎
《國家寶藏》注重組合運用媒介,其首播平臺在央視綜藝頻道,隨著節目的播出,系統內外的傳播機構也逐漸被納入節目的傳播渠道版圖,這些資源的規劃和自發使用,一起架構起了《國家寶藏》的傳播渠道。
(一)系統內渠道建構
央視臺屬資源聯合推廣。在節目播出前后,包括央視新聞、央視中文國際、央視音樂等多個臺屬頻道均對其以新聞、文化、音樂等類別加以報道,利用中央電視臺內部頻道資源為節目宣傳造勢、預熱。
地方電視臺分散報道形成助力。各博物館所在地的電視臺會進行預告性報道,節目播出后開展新聞回顧,甚至其他地方媒體也自發充當宣傳者。如遼寧、陜西、湖南衛視都在自己的相關節目中提及本地博物館推薦的文物,甚至為此制作節目,而諸如山西衛視等“地緣”性省電視臺也加入報道的大軍,這些零散的媒體報道構成了聯動宣傳。
(二)系統外渠道建構
電視是《國家寶藏》的傳播媒介之一,但在互聯網時代,網絡是更重要的傳播渠道,節目組官方微博、微信及央視網構成了其在電視之外最近的傳播渠道圈,通過在微博、微信等平臺提前放出演員定妝照來吸引觀眾;將整期節目剪輯成小片段,并加入一定的話題在微博上發布,不僅適應當下短小快的觀看方式,也可在轉發和話題下帶來更多熱議。參與拍攝的專業機構如各博物館官微也發布微博,在宣傳自我之時為節目傳播助力。參演的明星更是宣傳的重要推手,明星及其坐擁的粉絲為節目帶來流量,轉發、點贊都可放大傳播效果。
另一方面,愛奇藝、騰訊視頻、優酷視頻、嗶哩嗶哩彈幕網站等則形成了僅次于內環的又一層傳播圈,不斷將節目影響向外輻射。前三者擁有數量龐大的觀眾,甚至網站會員,這是節目借勢傳播的優勢。而B站作為國內最大的年輕人潮流文化娛樂社區,用戶群主要以90后和00后為主,《國家寶藏》成為該網站的“流量大戶”,打開視頻,十多萬彈幕飄了起來。這些鮮明的彈幕文化不僅是網民傳遞觀點的手段,也是和制作者交流的方式,如《國家寶藏》制作人就將在B站彈幕中看到的“文物是中華民族的共享記憶”寫入下一期的開場白中,“央視綜藝官方”是該節目在B站的官方up主,他通過及時更新劇集,借助活躍的傳播載體實現節目輸出。
五、結語
正如北京師范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教授所言,“《國家寶藏》之所以成為一個現象級產品,最重要在于其激活年輕人的心、激活文物價值、激活電視機構探索自身獨特的創作本領。”它通過節目本身的情感交流和人文內涵打動人心,從文化的角度出發,帶有一種娓娓道來的歷史感。它從文博領域吸取知識和資源來提升節目品質,是跨界方面的標兵;用優秀的內容填補觀眾的文化產品空缺;嘗試使用貼近當下潮流的敘事方式和話語體系制作節目;利用不同形式的媒介為節目預熱,并根據播出反響及時進行調整。它的成功源于新奇全新的表達;源于對珍貴文物內涵和傳統文化認同感的經營;源于自身內容和形式與各種媒介資源尤其是互聯網線上資源的契合;同時更是源于媒介運營組合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