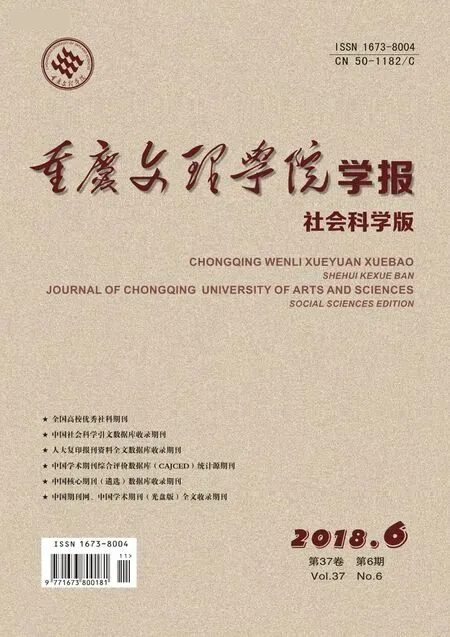上黨細樂的傳承機制與生存策略
劉彥
(山西省音樂舞蹈曲藝研究所,山西 太原030001)
上黨位于山西省東南部,處在與河北、河南交界的地帶,丹河、沁河穿行而過,是中原通往三晉的重要通道,又因居太行山之巔,故被稱為“上黨”。漢代劉熙《釋名·釋州國》載:“黨,所也。在于山上,其所最高,與天為黨,故曰上黨。”古上黨作為京畿之地,經濟發達,文化繁盛,民俗文化形態特色鮮明、多姿多彩。上黨民俗禮儀細樂(以下簡稱上黨細樂)是當地流布最廣、儲量最大的民間音樂形式。2009年,上黨細樂以“壺關縣牛府鼓樂社”為保護單位,入選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上黨細樂主要服務于當地的廟會賽社、婚喪嫁娶等民俗活動。傳承上黨細樂文化的樂人群體又稱“樂戶”,多以家族為單位結成相對固定的班社,在特定的禮俗活動中以其擅長的執禮人身份指導執行社會群體的生活規范與秩序,并以靈活的藝術實踐表達著豐富的地方文化和當地人民的認知與情感。據喬建、劉貫文及山西社科院學者在1994年的調查,上黨地區各地散居的樂戶約有151戶,其中分布最為集中的地區有壺關、陵川兩縣。在此基礎上,筆者在2012年至2015年期間,重點對壺關、潞城、陵川等地進行了調查,發現各地樂戶無論從傳承分布范圍還是規模來看,總體呈現逐漸縮小之勢。從其文化生態現實狀況來看,上黨細樂在長久的傳承歷史過程中仍然保持著鮮明的文化特征。
在村落生活中,藝術的創作和傳承主要是滿足鄉民的精神需求,是與人民群眾的各種交往活動緊密結合的[1]。上黨細樂在當地形成了周期性的表演和活態的存續形式,至今在村落民俗活動中依然得以完整呈現。筆者跟蹤調查了壺關縣國家級傳承人牛其云①的執儀活動,共參加了9次禮俗活動,有5次是葬禮,2次為賽社,2次為婚禮。各類禮儀活動舊時一般三至四天,禮節煩冗,現在則大多只有一至兩天,但上黨細樂的行業活動始終執行、傳承著傳統的“禮制”,各式祭祀必有儀式,儀式中也必用樂。在這一過程中我們看到,樂人群體在社會交際、藝術實踐、行業管理等方面,一直自覺并嚴格遵循“禮順人情”的傳統思想觀念與認識,在講求“禮”的規約性的同時也更加注重順乎人情,通過不同方式鞏固和增進與鄉民的情感聯系以及維系行內的“親情”關系,并通過特定的行規、制度、組織形式予以保證和實現。它所代表的不僅僅是一個群體的意愿,更多的還是禮俗慣制的力量,即它是傳統的。
一、順乎人情:樂人在社會互動中的生存之道
情禮關系是我國禮學思想的重要內容,緣情制禮或禮順人情是先哲早有的思想,視真情實感為禮的根本[2]。歷代儒家繼承禮學思想多主張禮為情作,禮因人情而為。后來,人們納情于禮,以禮制情,使禮制人情化、人性化,表現出濃重的情、禮并重傾向[3]。筆者在調查中,樂人牛其云講到樂戶時會常常提到“進情”。對于行外人來說,一時并不能清楚地理解,但從中始終能感受到樂人對“進情”的重視,隱約表達了這是關乎其生存的一種重要約定或基本規則。樂人們對于此“情”力量的了解與掌握與傳統社會人們一樣,都是源于其在這個世界上生存的必要。樂戶傳藝千年,與社會聯系與相處講究的就是一個“情”字,進一步講應是“人情”。于樂人而言,“進情”不僅是順乎人情社會的,也是對傳統禮樂文化在現實生活中的鮮活運用與傳承,更是以身作則積極踐行“以禮制情”的行為表達。
其一,歷史上樂人群體是一個獨特的社會群體,因社會地位低下,與廣大士、農、工、商各階層一直有著一道屏障,之間的關系只是一種生活禮儀需求而產生的雇傭或買賣關系。但職業行藝活動需要他們與其賴以生存的“衣飯”②建立起良好而穩定的社會關系。樂人們為了生存要“串百家門,吃百家飯”,更要通過合乎“情”與“禮”的行動來走進千村萬社,與群眾有深切的感情溝通,追求和諧、禮尚往來是其重要表征。長久以來,當地樂戶在禮俗活動中特別講究遵守“進情”的規矩。比如,某村王家,王老先生的兒子結緣迎娶,要雇他們吹奏助興,他們就利用這個機會拿上一份喜禮呈上;某村李家老太太過八十大壽雇他們去吹奏慶賀,他們也拿上一份賀禮呈上。當場執事總管深知是一份無親緣關系的禮品,只是一份“進情”,然后要還禮。還禮有舉一返三或舉一返二的,上黨民間稱還禮為“回頭”。這是一份特殊的高于“來頭”的“回頭”,返還的是現金③。但行“進情”禮只是“坡路”內的科頭或樂戶行有名的把式,曾經一直是細樂行獨家營生。可以說,“進情”進入了大小村社,進入了千家萬戶。
其二,樂人遵守的“進情”禮加深了樂人群體與村落的聯系,體現出樂人與“恩主”在長時間的互動中追求互惠與平衡的原則,并把這種人情互動自然地融入禮俗過程。舊時上黨地區樂戶有“討正月”習俗,細樂藝人裝扮神鬼逐家為人祈福禳災,代以糊口,是形同乞討的一種活動,從臘月二十三開始可以延續到正月十五前后。村莊也都愿意圖個吉利。這項活動幾乎成了樂戶在“坡路”內承攬的一項必不可少的活動,甚至關系到其一年中的辦事行藝。高平建寧村樂人余和氣老人講,有一年他的父親沒有去“坡路”內的常山村“討正月”,事后常山村社首竟不依,認為是看不起他們,幾乎要免去余家去該村辦事的資格。余和氣父親說了不少好話,并答應下次在該村辦廟上祭祀時多增加一場吹戲才算完事[4]135。從這件小事中可以看到,樂人與村莊間的“人情”禮數是樂人生活、辦事的重要組成部分,從來不能忽視和怠慢。因此,樂人與村落社會互惠互利、彼此尊重的基本關系和原則、禮節、規范等皆因情而設,而這種人情互動也自然地融入禮俗過程并與之渾然一體。
二、行藝規矩:禮儀傳承實踐中的自我規范
順乎人情所制定的禮能鞏固和增進維系樂人與人民群眾間的情感關系,同時,守禮更有利于其安身立命。上黨細樂行常把學藝、行藝等各項規矩稱為禮,這既是對人際交往的要求,也有對操持“禮事”的自我認同和規范。但樂人們的講述中還常常傳達出另一層重要的意義,即遵禮行藝是職業樂人的生存之道,是一種行業尊嚴。
其一,樂器的存放。樂戶藝人所用的樂器在吹奏時怎樣用,用后怎樣放都有禮規。藝人的樂器有多種,而鼓是“樂中之王”。在當地,樂人有俗言:“樂戶不離鼓和鑼,五音六律要相和,圪啦打板按宮商,圣朝要動圣朝樂。”鼓雖是一種粗樂,但樂人是尊崇的,關于鼓如何保護與存放有講究:“用時要支起來,用畢不摞起來。裝箱要豎起來,行走要背起來。用鼓要穿起來,用畢要包起來。”④如果有人用畢將兩鼓摞起來放,就違背了行業禮規,意思是將“大王”垛起來,以后再沒事可辦了。正如農民賣牛馬不能賣“籠頭”一樣,這也是樂戶行人必須牢記的禮規。
其二,樂人的服飾。上黨樂戶群體是村落社會中的特殊成員,作為特定禮俗活動的儀式執行者,他們舉行禮儀活動時身著的服飾是其職業標識。上黨樂人的服飾形式獨特,俗稱“行頭”,因使用場合不同主要分為四類:紅事服、白事服、社火故事服、戲服。紅事服只用于節日慶典、迎神賽社、官家祭祀、婚禮、壽誕等。白事服裝只用于葬禮。社火故事服用于節日慶典、迎神賽社、喜事慶典等。戲服又有隊戲、院本、雜劇等,因劇目而有所不同,多為神廟神誕、許愿戲、還愿戲演出。在一些特定場合,服飾的形制還有一些特殊的樣式。民間流傳的俗語“頭戴七折八扣,身穿有領無袖,腳踏五福捧壽,手拿一尺不夠”,形象地描繪出樂戶藝人在執事活動中的服飾樣式。樂戶藝人對氅服保護與存放也有規矩,通常由專人管理。樂人們在儀式活動前更衣,必須上香叩拜方可穿戴。穿戴整齊后不得隨地隨意亂坐,演后完整歸箱跪叩致謝。平時要確保氅衣整潔干凈,如有損壞要處罰并賠償。
其三,執禮時的規矩。為保證儀式的準確與莊嚴,細樂行在執儀過程中有一套嚴格而又復雜的自我規范體系。如迎神賽社活動有專門告知樂人的《省令樂人文》,其中有諸多關于樂人執禮儀規的內容:
“吹彈歌舞、鼓樂吹笙者務須精誠嚴整。衣帽新鮮,鼓樂齊備。不可懈怠茍安,聊且斯事……先記大曲四十,后記小令三千……按詞章而動樂,依律呂而奉神。須要曲真調正,婉轉詞意,不可流于鄭聲;又要舞熊出象,曲尺古事,不必隨于世俗。誠心爾事,切莫怠慢。恐一時之忽略,貽他日之后悔。為此省令,殷勤慎行。”[5]505
上文記載了迎神賽社時對樂人的執禮要求、行規禁忌等。這應是樂人參加重大樂事活動最基本的“禮”的準則。另外,樂人們還通過講禮規進一步明確分工,有俗言“先生的嘴,茶房的腿”,講的就是“主禮”與“茶房”。“主禮”作為參辦禮事的總指揮,在舉禮時站在神前方桌的左上方,稱“禮位”,俗稱“托桌角子”,只是口說指揮,不動手。“茶房”在迎神賽社中又稱“前行”“后行”,舉禮時要站在桌前右下方,主要負責禮事中所用的一切禮具用品,召喚樂人、參祭人及其他執事人按時到場等。細樂與禮的統一在迎神祭祀的執儀規范中得到進一步強化。
樂人群體對“禮”的遵循不僅是指其掌握的禮儀知識或技藝,還包括基于禮制要求或生存之需所形成的一整套行藝規矩,在長期不斷的禮儀實踐中已經融于“禮”的全過程,成為構建當地村落禮俗生活的重要內容。因此,上黨細樂和樂人群體因其所具備的“禮樂”屬性以及嚴謹的禮儀實踐,在當地眾多鄉民藝術體系中一直占據中心地位,既在構建村落禮俗空間中發生著作用,又成為樂人實現自我生存及細樂文化有序傳承的重要策略和動力機制。
三、行業崇拜:樂人群體共享的文化空間
上黨細樂在文化功能上符合傳統社會情與禮的需要,但樂人群體長久處于社會底層并與社會有一定隔離,使其高度重視內部的相互合作,逐漸形成以咽喉神信仰為核心的行會組織、管理活動和習俗規約,實現著對內部行業運行關系的制度化。其目的在于維護堅固的行業內部共同體,構建一個既規范行業運行又為成員所共享的文化“家園”。
其一,上黨細樂的信仰空間。上黨地區的樂戶敬奉咽喉神。現存咽喉祠八處,主要分布于高平、陽城、陵川、沁水、澤州,主要有陵川禮義鎮東陳丈溝咽喉神廟、澤州縣府城村玉皇高咽喉殿、晉城市李寨鄉望城頭村開元宮咽喉祠、沁水縣玉皇廟咽喉殿、澤州縣五聚堂咽喉祠、神南村咽喉神殿、陽城縣潤城鎮上伏村咽喉殿、高平縣浩莊咽喉祠。其中,以晉城玉皇廟咽喉祠為最早。各處咽喉祠在歷代增建過程中,資金募捐的主體多為樂戶。如晉城咽喉祠所存的《增建咽喉祠志》⑤碑陰《計開衍施銀姓氏》中,所列一百余姓氏都是周邊樂戶。凡有咽喉祠,必有樂戶祭祀;凡有樂戶集體祭祀,必有樂戶集體行業活動。每年臘月初八祀咽喉神,由各家科頭輪流主持祀典,儀式隆重,全縣樂戶班均來祀神、唱戲。如高平咽喉祠每年有兩次神事活動,分別是在元宵節和臘月初八。樂人祭祀通常有廟祭、戶祭、轉祭等形式。廟祭前,主辦科頭及祝廟人員先作香會采辦準備,提前一日把供神祭饌、燈籠牌匾、燭臺祭器安放妥當。初七上午全縣樂戶到廟,耽誤者要以行規處罰,午飯后開始焚香稟神。敬神禮規類同賽事供盞,有茶房主禮、主科頭及各科頭拜祭。戶祭通常是在樂戶家中都有敬奉咽喉神之位,每月初一、十五上供焚香。每年的祭祀活動除了樂戶行獻藝娛神、祈求對樂人的護佑外,一般群眾家中有病人也要敬拜咽喉神[6]。咽喉祠是樂戶傳習技藝的重要場所,其凝聚行業精神的作用突出,成為樂戶行共同的精神空間。
其二,上黨細樂的行會組織。各地樂人每年必須參加的“咽喉神”臘八節香會賽除了交流技藝外,更為重要的是由行會組織對各班一年的執事活動情況進行總結。舊時上黨各縣樂戶都有共同的香會、公議會等行會組織,多由當地科頭組成。科頭即樂戶中的領事人,能夠分到坡路的樂戶具有獨立承應辦事的能力。據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的調查資料,“陵川縣管理樂戶應差的科頭有12家,陽城縣有樂戶科頭10家,潞城縣樂戶科頭有8家”[5]9。科頭還管著若干樂戶,如潞城微子鎮的朱家,四支為一家戶頭,號稱“朱四戶”,每支有三四家。為了管理與協調,每縣樂戶行各家科頭中再產生一名總科頭,內部糾紛可交總科頭決斷,處理不了的再交官方決斷。陵川樂戶還有一種公議會組織,成員由科頭組成,從中推選一名會長,會長卻不同于總科頭。這樣的組織除了調解內部糾紛,還兼有維護所屬樂戶權利不受侵害的責任,對不嚴格遵守在本“坡路”辦事行規等行為進行公議處理。據樂戶侯成有講,早年其父輩曾將原承攬的十個村莊的坡路典租給了高平建寧村余家樂戶,后來要贖回時,余家不讓,最后依靠公議會交涉才達到目的[4]128。嚴格的行規是上黨細樂有別于其他行業群體的重要因素,如在技藝傳承方面,過去拜師學藝無論是到行家學還是親戚家學,都要嚴格遵守三年學徒、四年謝師的行規,并有傳男不傳女、學武不學文的規矩,行內曲譜及絕技也不得傳外。此外,行內樂人各家舉辦紅白事,當地樂戶均要參加且操樂辦事一律不掙錢等。這都成為上黨細樂行業內部共同遵循的規約制度,形成了其在行業組織運行方面獨特的文化傳統,在一定意義上保證了上黨細樂的久遠傳承,也隱性影響著當地禮俗生活的有序運行。
上黨樂戶以咽喉神信仰為中心締結的行會是一種兼具宗教、聯誼、仲裁、經濟等多種功能的行內組織,通過共同的咽喉神崇拜實現全行業的精神整合;而由行會制度達成的整合則指向樂人行內情感增進、利益認同、信息聯系、規約依據和民主參與等,用制度保障了群體內部的秩序,使上黨細樂在世代傳承中始終保持著較為持久的生命力。
四、結語
藝術人類學關注的主要有兩個向度:“一方面,透過藝術看文化,考究特定群體的‘藝術活動’與當地社會文化內涵之間的索引性關聯,亦即藝術的文化表達問題;另一方面,從文化語境切入闡釋藝術,探討特定‘框束’條件下的諸如人對藝術活動的賦義、具體藝術形式的產生、藝術的即興創作等論題,即文化的藝術呈現問題。”[7]上黨細樂作為村落文化體系中的民間藝術形態,有自己的歷史演化過程與個性特征。樂人群體首先是作為村落中的村民,其次是特定儀式、音樂的執行與傳播者。在參與村落社會秩序規范與地方歷史文化的構建過程中,面對自身生存與藝術傳承問題時,樂人群體不僅要在儀式性民俗實踐中嚴守禮制,更要在適應社會生活的過程中謹慎而自律,形成了一整套以“禮順人情”為主要特征的行藝制度、生活準則和行業規約。這在一定意義上揭示了鄉民藝術在生存模式和傳承策略選擇上的某些“文化邏輯”。
首先,在社會互動中追求情禮相合的統一性。禮不僅反映了情,而且禮一旦形成制度儀式,還會對情發揮積極的促進作用。上黨細樂群體對于情禮關系的認識與體驗較之其他行業更為深刻,不僅通過自身掌握的禮樂知識操持各種民俗禮儀,維系和鞏固合乎人情的社會秩序,并在行內的運行控制中自覺發揮情禮關系相互促進的積極作用,鞏固并增進與外部社會的關系,真正做到循禮而動、與禮合一。其次,在藝術實踐中始終堅持禮樂的主體性。上黨細樂在村落禮俗生活當中,主要滿足鄉民的精神需求,與群眾的生活交往活動是緊密結合的。上黨細樂通過參與村落禮儀空間的象征性表達和社會生活秩序的規范建構,并在內部的技藝傳承與行業管理中始終圍繞其承擔的“禮樂”功能而展開,保證了其在社會中存在的合理性與權威性。此外,傳承群體對內部規范有著強烈的自覺性。樂人在歷史上一直處于社會底層,基于對自我的“生活史”即共同文化習慣的認同,在群體思維、行為中會形成一種出于生存壓力下的自我保護意識,即如何與社會各階層建立良好的交際模式并借助掌握的禮樂技藝取得更受尊重的社會地位。因此,對行業內部運行秩序的規范成為重要內容。尊崇祭祀行業的咽喉神、建立嚴格的行規制度、成立嚴密的行會組織等一系列行為,始終貫穿著一套追求內部自治與有序傳承的自覺意識。在他們身上既體現了地方社會的文化共性,又因其特殊的“職業”而具有獨特個性。他們不僅將禮樂文化的信息帶到村落生活的各個角落,同時又以自身在社會進程中的個性化選擇反作用于地方文化傳統的構成。本文從樂人生存的社會語境出發,對上黨細樂在禮儀傳承過程中“講情遵禮”的思維認識及表達形式進行探究,希望能對鄉民藝術特別是其傳承主體——鄉民做出新的解讀和表達。
注釋:
① 牛其云,漢族,1950年生,山西省壺關縣黃山鄉沙窟村人,2009年入選為第三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代表性傳承人。
② 舊時由官府對樂戶職業活動范圍予以劃定并可世代繼承,各樂戶的執業收入均來自于職屬范圍內村落各類禮俗活動,故稱賴以生存的職業活動范圍為“衣飯”,也叫“鄉道”“坡路”。
③ 據牛其云口述內容整理。訪談時間:2015年1月1日。采錄地點:山西省壺關縣其家中。
④ 穿起來意為穿鼓衣,包起來意為打鼓包。
⑤ 碑現存于山西省晉城市澤州縣府城村玉皇廟咽喉殿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