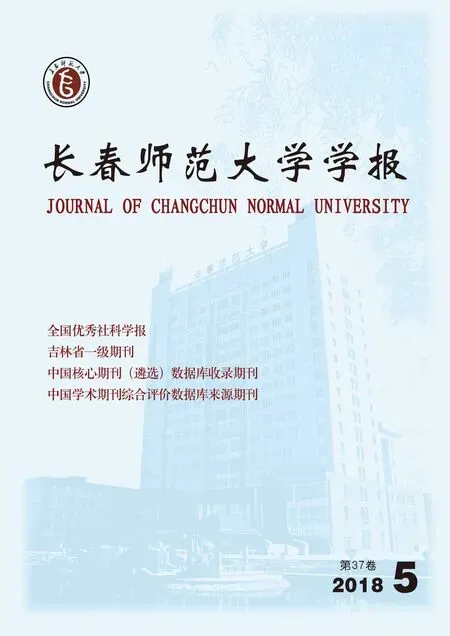《文選》編者考
馬朝陽
(東北師范大學 文學院,吉林 長春 130024)
在傳統文選學基礎上,現代文選學的研究領域不斷擴大。日本學者神田喜一郎與清水凱夫先生提出了“新文選學”,游志誠、許逸民先生等學者相繼論述了新文選學的內容。許逸民先生在《“新文選學”界說》一文中,將新文選學總結為“八學”:第一,文選注釋學;第二,文選校勘學;第三,文選評論學;第四,文選索引學;第五,文選版本學;第六,文選文獻學;第七,文選編纂學;第八,文選文藝學。其中“文選編纂學”涉及《文選》成書的諸多問題,被日本學者清水凱夫稱為“《文選》的真相”。許逸民認為這一領域為“近十年來的熱點”:“編纂學研究的起點應是探明《文選》編纂時的真相,如成于眾手問題、實際主持人問題、成書時間問題、編纂目的問題等。其次,要弄清編纂體例,如編者文學觀問題、選錄標準問題、所選作品之間的內在規律問題等。這些文體的解決恐非易事,因史料匱乏,人言人殊在所不免。第三,《文選》對后世編選總集的影響,也是編纂學應該研究的問題。從駱鴻凱的《文選學著錄》中所開列的‘補遺廣續文之屬’,我們可以明顯看到《文選》一書的強大沖擊力。”[1]以《文選》的編者問題為出發點,能夠探究《文選》反映了何者的文評觀念,從而促進對《文選》成書問題的深入研究。
一、關于《文選》編者的三派意見
對于《文選》的編者問題,學界有三種意見。其一是傳統觀點:蕭統主編,蕭統的學士加以輔助。這一觀點受到歷代學者的支持。其二是蕭統掛名,劉孝綽主編。持此觀點的代表學者為日本清水凱夫先生。其三,蕭統獨編說。持此觀點的代表學者為力之先生。
(一)傳統觀點:蕭統主編,學士協助
根據《梁書》《南史》等史書記載,《文選》主編者確為蕭統。又根據日釋空海《文鏡秘府論》、王應麟《玉海》等書記載,蕭統的學士對編撰工作加以協助。對其輔助之人,學界有不同意見,有昭明太子十學士、高齋學士、文選樓學士、劉孝綽及何遜等說法。這一觀點有歷代文獻記載,也符合蕭統“愛好文學”、廣招學士的史實,所以,“蕭統主編說”作為流傳千年的傳統觀點,受到歷代學者的廣泛認同。在現代文選學研究中,清水凱夫、力之先生對此觀點進行了質疑,進而提出了“蕭統掛名說”與“蕭統獨編說”。
(二)蕭統掛名說
清水凱夫先生認為,劉孝綽為《文選》的實際編撰者,而蕭統只是掛名。他提出了幾點例證:其一,學術研究不能被“定評”限制。根據史書記載,蕭統編纂《文選》三十卷,歷代學者皆延續此說。但古代有一慣例:古代帝王對下屬下達編輯的命令,下屬承擔編輯任務,帝王并無實際工作,最后署上帝王的名字,或帝王只是書寫序文。所以根據史書的記載認定《文選》的主編為蕭統,并不可信。又根據日釋空海《文鏡秘府論》、王應麟《玉海》對劉孝綽的記載,《文選》的編撰是以劉孝綽為中心的。其二,對《文選》文本的解讀,要結合史實,參照時代大背景。如《廣絕交論》是劉孝綽為報復到洽而選入《文選》;《劉先生夫人墓志》是劉孝綽為恢復父親先師劉瓛及其夫人名譽而選,等等。這些《文選》中的文本都是“劉孝綽中心說”的有力證據。其三,蕭統與劉孝綽的文學批評觀念存在一定差異。最有力的證據是,蕭統在《陶淵明文集序》中批評陶淵明的《閑情賦》是“白璧微瑕”,卻在《文選》中選錄風格相近的《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洛神賦》等以“情”為主題的篇章,不符合蕭統“兼文質,而無傷風教”的選篇標準。這種作品選擇方面的互相矛盾,只能用劉孝綽為《文選》的主編來進行解釋。其四,《文選》選錄了相當數量的“永明體”風格的詩文,這是由于劉孝綽崇尚“永明體”。這一文學理論是由沈約、任昉、范云、謝朓、王融、劉孝綽的父親劉繪為中心的共同理論。劉孝綽具體的選篇標準也集中在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一文中。綜上所述,劉孝綽是《文選》的編者,而蕭統并未參與實際的編撰工作,只是掛名。
清水凱夫先生跳出常規的研究方法,認為“選擇作品時,未必能說是編者先確立理論再按照理論作批判的選擇。實際上多數情況與此相反,最先以編者的思想、信念、愛憎、資質等極其主觀的鑒賞和實感進行批判的選擇,然后確立其理論根據。”[2]1清水凱夫先生的新觀點、新方法、新視角促進了對《文選》編者以及《文選》選錄標準的新思考,打開了新文選學的局面,拓展了《文選》成書研究的領域,尤其引起了學界對劉孝綽突出貢獻的認識與肯定。
(三)蕭統獨編說
力之先生認為《文選》系由蕭統獨自編撰,未有他人協助。他在文獻與情理等方面進行了論證:其一,從可靠的文獻記載來看,《梁書》《南史》《隋志》《唐志》等史書均記載《文選》三十卷為蕭統所編,未指出有協助者。這些文獻是正史材料,堅實可信。同時,還要區別那些不可靠的文獻。《文鏡秘府論》《玉海》引《中興書》這樣的文獻,多有不符合史實的錯誤,所以不可輕信其關于劉孝綽等人協助的說法。其二,從情理方面來看,蕭統雖引納才學之士,但這與《文選》的編撰并非一回事,而且現存的可靠史料并不能證明劉孝綽等昭明太子十學士參與了《文選》的編撰。此外,蕭統在《文選》與《陶淵明集》中采用了不同的價值取向,不能以《陶淵明集》的價值觀念來看待《文選》。所以,從情理方面來看,劉孝綽等學士參與編撰《文選》的說法難以成立。其三,從總集編撰與相關書籍的編撰工作量看,編選《文選》的工作量并非如朱彝尊所說“聞有千卷”,相反,編選《文選》的工作量并不大。與類書、子書不同,《文選》的編撰在于“采摘孔翠”,所以在編選開始就縮小了范圍。而在蕭統之前,魏晉南朝人多有編撰總集,很多人都是憑借一己之力完成的,如摯虞的《文章流別集》及劉勰的《文心雕龍》。這些史實更加印證了蕭統獨編說的合理性。
力之先生以跳出《文選》觀《文選》的方法,基于文本,針對當時的文化大背景,以整體見部分,以可靠文獻為根據,“將古人的問題還歸古人”,再從邏輯的角度分析,為《文選》的成書研究開辟了新思路,啟發了《文選》成書問題以及相關領域的研究。
二、蕭統主編說更合情合理
筆者傾向傳統觀點:蕭統主編,學士輔助。這一觀點有詳實可靠的文獻記載,且受到千余年來歷代學者的肯定。蕭統“愛好文學”,對創作有自己的見解,這是不爭的事實。《文選序》載,蕭統“居多暇日”,說明蕭統有能力與時間發展文化事業。《文選》是蕭統“化成天下”的文化大典,集中體現了蕭統的價值導向與泛文學觀念。蕭統常與眾多學士“商榷古今”,從而出現了“昭明太子十學士”的說法。蕭統身為一國太子,在編撰文集時選定價值導向與選錄標準,再下達命令,其手下進行協助,這是非常符合邏輯的。所以,《文選》系蕭統主編,他的學士協助完成。
(一)蕭統為《文選》主編有可靠文獻記載
蕭統是《文選》的主編者,有《梁書》《南史》《隋書》《唐書》等堅實可靠的文獻支撐。《梁書·昭明太子傳》:“(昭明太子)所著……《文選》三十卷。”[3]171《南史·梁武帝諸子》:“(昭明太子)所著……《文選》三十卷。”[4]1312《隋書·經籍志》:“《文選》三十卷,梁昭明太子撰。”《舊唐書·經籍志》:“《文選》三十卷,梁昭明太子撰。”《新唐書·藝文志》:“梁昭明太子《文選》三十卷。”李善《唐李崇賢上<文選>注表》:“昭明太子……撰斯一集,名曰《文選》。”[5]3呂延祚《進五臣集注<文選>表》:“梁昭明太子所撰《文選》三十卷。”[6]1
筆者以為,《梁書》《南史》等史書的記載是可信的。力之先生針對古代掛名的問題提出了梁代的三證:其一,梁武帝命徐勉主持編撰《華林遍略》,徐勉推舉何思澄等五人,但《梁書》《南史》《隋志》并未將此書署名梁武帝。其二,蕭綱在《法寶連璧》成書后命蕭繹作序,蕭繹在序文中詳細地交代了參與編撰的蕭子顯等三十七人。如此“實話實說”,說明身為皇太子的蕭綱不在意這些。其三,梁安成王蕭秀命劉孝標編撰《類苑》。《隋志》子部雜類著錄《類苑》,署名劉孝標,并未署名下令之人蕭秀。力之舉出的例證皆出自梁代,有力證明了史料文獻的可靠性。又有經常與《文選》相比較的《玉臺新詠》,兩書成書背景相似,一同流傳至今。蕭綱位居太子時,命令左右編撰《玉臺新詠》,但署名者為實際編撰人徐陵,而非蕭綱。唐劉肅《大唐新語》:“梁簡文帝為太子,好作艷詩,境內化之,浸以成俗,謂之宮體。晚年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撰《玉臺集》,以大其體。”[7]42蕭繹在《金樓子序》中也說:“常笑淮南之假手,每嗤不韋之托人”[8]1,還在《著書篇》中寫明了《金樓子》成書的具體情況。這些例證一則說明了梁代蕭氏兄弟滿腹文才,編集著述不需要假借他人之手;二則說明即使是命令他人編撰,也會說明實情,屬上實際主編者的名字,而不會辱沒他人之功。清水凱夫先生所述古代掛名之慣例確有,而不是全部現象。縱觀梁代皇帝、太子等貴族,多有命令下屬撰集的情況,但他們并不在意后世知道,從而屬上實際編撰者的名字。古代皇帝、太子作為統治階級的最高層,有不勝其數的人在方方面面為他們服務。從撰文的角度來說,皇帝有時自己撰文,而大多數時候是命令手下寫詔書、圣旨。這些詔書、圣旨雖然不是出自皇帝之手,卻實實在在反映了皇帝的意志,其思想內容與代筆人毫無關系。而編撰文集的情況比較復雜,手下之人根據上層的意見進行選錄、刪減,難免滲透手下之人的主觀傾向,但文集的面貌在內容與形式等方面所反映的還是上層的基本意志。如此,便不能說此文集假他人之手。筆者以為,在一千多年的浩瀚歷史中,史料文獻的記載便是今人乃至古人最有力的證據之一。
根據隋唐史籍的記載,《文選》確系蕭統主編。這一觀點受到歷代學者的肯定,直到當代學者清水凱夫先生提出“蕭統掛名說”。在肯定清水凱夫先生研究貢獻的基礎上,顧農、穆克宏、力之、陳延嘉先生等學者對“蕭統掛名說”的觀點進行了商榷,認為此說不能成立。其一,古代編集、著述掛名的現象確實存在,但具體問題需要具體分析,并不能以此來斷定《文選》的主編者不是蕭統。正如顧農先生所說,蕭統是一位“內行”,不宜架空。蕭統雖身為太子,但他多有暇日,且“愛好文學”,不僅自己創作詩文,也有編集的經歷,所以蕭統有能力與時間主編《文選》。其二,清水凱夫先生所舉的《文選》中的詩文并不能證明劉孝綽的主編地位。首先,力之先生指出,根據《南齊書·劉暄傳》的記載,早在齊和帝中興元年(501),劉暄就已經被平反了。顧農先生也指出,南朝大姓之間都有些沾親帶故,若用此方法排查,簡直數不勝數。所以劉孝綽“徇私情”的說法不能成立。而《廣絕交論》《頭陀寺碑文》等文章文質兼美,符合蕭統的選錄標準,這些作品被選入《文選》實至名歸。其次,陳延嘉先生指出,劉孝綽雖然性格狂妄自大,但對待梁武帝是畢恭畢敬的。如果是太子都不敢選的作者,他身為一個臣子又怎敢輕易忤逆君主呢?《文選》中選錄了劉孝標等人的作品,正說明了《文選》的主編者為蕭統。《廣絕交論》是清水先生“劉孝綽中心說”的重要證據,具有學術增長點,促進了《文選》成書領域的深入研究。但正如清水先生所說,對《文選》編者問題的研究應回歸《文選》文本。陳延嘉先生指出,深究《廣絕交論》一文,更可得出此文不為劉孝綽徇私情的證據。此文借朱穆《絕交論》而發揮,直指到氏兄弟對任昉的忘恩負義。《南史·到溉傳》記載,到氏兄弟因任昉的提攜而“廣為身價”,但任昉死后,其子流落街頭卻無人問津。值得注意的是,任昉愛才,他雖然與到氏兄弟關系密切,有升堂拜母之舉,但同時任昉也提攜了其他許多有才之士,這其中就包括劉孝綽。如劉孝綽想以此文抨擊到氏兄弟忘恩絕情,那豈不是連自己也抨擊了!況且《廣絕交論》絕非僅述一事,而是針對一切人際交往,抨擊“利交”而提倡“素交”,以廣闊的視角反映了世態炎涼、人情寡淡的社會現狀,是一篇具有教化深義的作品,非常符合蕭統“化成天下”、教化萬民的編撰意圖、以儒為宗的價值觀念以及“事出于沉思,義歸乎翰藻”的選錄標準。所以,選此文不是劉孝綽徇私情,而是蕭統授意的。蕭統與梁武帝的關系是變化發展的。俞紹初先生指出:“蕭統因埋蠟鵝事發而遭梁武帝猜忌。”[9]3在蕭統之母丁貴嬪去世之前,父子關系還很融洽;而在丁貴嬪去世之后,兩人關系漸有生疏。至“蠟鵝事件”,蕭統已完全失信于梁武帝,地位大不如前,時刻處于武帝的監視之中。蕭統深知,自己被廢去太子之位是早晚的事,此時的蕭統與梁武帝的思想已經拉開了距離。最明顯的例證是,蕭統上奏《請停吳興等三郡丁役疏》,反對武帝的《發上東三郡民丁開渠詔》,這說明此時梁武帝的態度對蕭統來說已經不重要了。所以,此時放下名利、順從本心的蕭統自然會在《文選》中選錄即使梁武帝不喜歡而自己認為意旨深遠的作品,如《辯命論》《廣絕交論》。屈守元先生指出,這些地方體現出了蕭統的氣魄與卓識。正是蕭統作為選者的包容萬緒,才使《文選》如燦爛星空般閃爍著熠熠光輝,經久不衰。所以,清水凱夫以“徇私情”來證明劉孝綽為主編者的方法似未圓照。其三,《文選》收錄《神女賦》等作品并不與《陶淵明集序》中對《閑情賦》的批評相矛盾。顧農指出,好的選家要有寬容的態度。所以《文選》在內容上包羅萬象,就不可能不涉及“情”類的作品。蕭統編撰《文選》以“雅正”為目的,故其所收“情”類作品如《神女賦》《洛神賦》皆未見淫靡之情,卻可見神女“自持”之美德,符合蕭統“教化”的編選深意。《詩經》同樣不乏歌頌后妃之德的詩歌。而《閑情賦》多情愛隱喻,陶淵明是蕭統的知音,是蕭統心靈的歸宿,所以評價《閑情賦》“白璧微瑕”并不為過。
此問題經過眾多學者多年商榷,已見其端倪。清水凱夫先生所言之例證未能言之鑿鑿,其“劉孝綽中心說”的觀點也似未圓照。清水凱夫先生是一位價值中立的學者,在不斷的商榷后,他在1999年發文指出:“至今為止的研究已證明了《文選》的編撰決非昭明太子一人所為,乃是依靠近臣的協助完成的。”[10]清水凱夫先生此說明確了蕭統是《文選》的編撰者,但還有一些近臣加以協助,這無疑修正了其之前發表的“劉孝綽中心說”。
根據《梁書》《南史》《隋書》《唐書》等堅實可靠的文獻記載,《文選》的主編者無疑是蕭統本人,《文選》所體現出的政治、文化、社會、人生等諸多觀念,皆是蕭統思想的集大成載體。
(二)蕭統有時間與能力編撰《文選》
蕭統為《文選》主編者的另一有力證據是《文選序》。《文選序》作為《文選》的綱領,不僅集中體現了蕭統編撰《文選》的選錄標準、《文選》作品選錄的年代、《文選》文體的分類等《文選》成書的基本樣貌,也記錄了蕭統編撰《文選》的創作意圖及編撰的基本情況。蕭統“居多暇日”而又“泛覽辭林”,于是對超過千年的龐雜作品有了“略其蕪穢,集其清英”的想法。換言之,蕭統撰集的意愿正是他在“泛覽辭林”的過程中所產生的。根據史書記載與蕭統的實際情況來看,蕭統確有能力與時間編撰《文選》。
1.蕭統居多暇日,有時間親自編撰《文選》
根據《梁書》記載,梁武帝曾授命蕭統進行判定案件等監國事宜。持“蕭統掛名說”的相關學者常以蕭統監國繁忙,無瑕親自編撰《文選》為理由。《梁書·昭明太子傳》:“太子自加元服,高祖便使省萬機,內外百官奏事者填塞于前。”[3]167但《昭明太子傳》在后文接著說:“閑則繼以文章著述,率以為常。”[3]167蕭統雖身負監國重任,但他仍然有“閑”,能夠“繼以文章著述”并“率以為常”。陳延嘉先生指出,“監撫”確實是重任,毋庸置疑。但蕭統到底擔負了多少重任,應具體分析。據《梁書》之《武帝本紀》和《昭明太子傳》記載,蕭統從沒有撫軍之舉。從蕭統加元服后,梁朝一直處于上升期。武帝富于春秋,身強力健,太子被訓練準備接班,日理萬機的是武帝。梁武帝長壽,而且多疑,輕易不會將大權下放。不僅《昭明太子傳》可證蕭統有“閑”,蕭統《文選序》也明確道出了自己有“暇日”:“余監撫余閑,居多暇日”。蕭統生存之時,是魏晉南北朝難得的穩定時期——政治相對穩定,經濟逐漸繁榮,而且梁武帝勤政。對于蕭統來說,監國的情況都是較少的。不論是《昭明太子集》《文選序》還是《梁書·昭明太子傳》都明確指出,蕭統“監撫余閑,居多暇日”。所以,蕭統有時間親自編撰《文選》。
2.蕭統博覽古今、能文善作,有能力編撰《文選》
蕭統“愛好文學”,又有很多空閑的時間,自然“厲觀文囿,泛覽辭林”。蕭統的閱讀范圍非常廣泛:“自姬漢以來,眇焉悠邈,時更七代,數逾千祀。詞人才子,則名溢于縹囊;飛文染翰,則卷盈乎緗帙。”蕭統并非對古代作品一眼掠過,而是廣泛地閱讀佳作名篇,并且有自己的見解。正因為蕭統有如此博大的閱讀量,對這些年代跨度很大、內容豐富、數量龐大的作品有所感悟,才有了“略其蕪穢,集其清英”的編撰意圖。雖然這項工程“太半難矣”,但筆者以為蕭統不僅有充足的時間,更有足夠的能力可以勝任主編一職。
其一,據史書記載,蕭統生而聰慧,“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遍讀《五經》……(九歲)于壽安殿講《孝經》,盡通大義。”[3]165蕭自幼便有眾多名師大家對其加以培養,正所謂“名師出高徒”。蕭統不僅博覽古今,還常常自己屬文,現有《昭明太子集》傳世。
其二,《昭明太子集》中的詩文可證蕭統對《文選》中的篇章爛熟于心。蕭統常常在自己的詩文中引用《文選》中的典故、章句。如蕭統《與晉安綱令》:“皆海內之俊乂,東序之秘寶。”《文選》收陸士衡《演連珠》有言:“俊乂之臣”;任彥生《為蕭揚州薦士表》有言:“并東旭之秘寶”。蕭統知識淵博、涉獵廣泛,儒釋道無所不通,經史子集無所不讀,又怎會沒有能力主編《文選》呢?
其三,蕭統已有編撰文集的經驗,他有自己的文評觀念、選錄標準,所以對文章的“略其蕪穢,集其清英”有準確判斷。在《文選》成書之前,蕭統已經撰成五言詩集《文章英華》,而蕭統對此書并不十分滿意,這也是促成《文選》編撰的原因之一。蕭統自小被重點培養,其校勘、版本等文獻功底也無可懷疑。簡文帝《昭明太子集序》總結了蕭統的十四德,第十四就是蕭統“降貴紆尊,躬刊手掇”[9]250,即蕭統親自抄寫書籍,做校勘工作。這不僅說明蕭統學術功底深厚,更說明他對編集著述的細微之處都親力親為。又如劉孝綽《昭明太子集序》:“靈臺辟雍之疑,禋宗祭祀之謬,明章申老之議,通顏理王之說,量核然否,剖析同異,察言抗論,窮理盡微。”[9]244-245對古代學府所不能解決的問題,宗廟禮法之事以及古代名家的學說,蕭統都懂得,并且能夠“剖析同異”“窮理盡微”。與蕭統關系密切的劉孝綽最能證明蕭統的博學與卓識。同時,蕭統還有一大批學士進行輔助,更加促成了《文選》的高質量成書。
其四,在《文選》問世以前,梁代已經有選集,如《文章流別集》。現代文選學也提出了《文選》為再選本的觀點。雖然在《文選》之前,蕭統已看到一些選本,但這些書并不能讓他滿意。《文選》得以流傳至今,成為現存最早的泛文學總集,意義深遠。雖然這些選集已經被歷史湮沒,但在蕭統生活的年代,給了蕭統一定的借鑒。《文選》的內容包羅萬象,語言華麗典雅,堪稱百科全書,這也正是蕭統作為太子的視角所體現的權威意識,更是蕭統學識與能力的體現。
蕭統“監撫”有“閑”,“居多暇日”,且“愛好文學”、博覽群籍,對創作有自己的見解。他在閱讀古籍的過程中,萌生了“略其蕪穢,集其清英”的想法,所以攜眾學士編撰成《文選》一書。蕭統身為太子,以政治的眼光滲透于《文選》的編撰,使之成為促成大一統的文化大典。所以,《文選》的選錄標準也是復雜的、多層次的。
(三)蕭統學士的輔助作用
在《文選》編撰的過程中,蕭統身為主編,把握主要航向;他的眾多學士為他充當馬力,輔助他乘風破浪。所以,東宮眾學士的重要價值不能忽視。從歷代文獻中皆可見眾學者對東宮學士的重視。這其中有“東宮十學士”說、“劉孝綽”說等。不管參與編撰者為何人、數量多少,東宮學士皆在編撰《文選》的過程中做出了一定的貢獻。
1.學士輔助系歷代文獻記載
除史書記載《文選》主編為蕭統,唐以來眾多文獻記載了蕭統學士的協助之功。唐代日釋空海《文鏡秘府論·南卷·集論》:“至如昭明太子蕭統與劉孝綽等,撰集《文選》,自謂畢乎天地,懸諸日月。然于取舍,非無舛謬。”《敦煌四部書六十年提綱·雜鈔》中說:“梁昭明太子召天下才子相共撰,謂之《文選》。”南宋王應麟《玉海》引《中興書目》“著錄《文選》六十卷”,并注釋為:“《文選》昭明太子蕭統集子夏、屈原、宋玉、李斯及漢迄梁文人才士所著賦、詩、騷……行狀等為三十卷。”文末又加注:“與何遜、劉孝綽等選集。”歷代學者并沒有對蕭統作為《文選》編者的地位加以懷疑,并認為在蕭統主編的基礎上,學士劉孝綽等人進行了輔助。北宋邵思在《姓解》中首次提出了“昭明太子十學士”,并明確指出“劉孝綽、張纘、張率、張緬、到洽、陸倕、王筠”七人共同協助蕭統。北宋《太平御覽》引《襄沔記》:“金城內刺史有‘高齋’,梁昭明太子于此齋造《文選》焉。”南宋王應麟《玉海》、明代董斯章《廣博物志》等沿用“高齋學士”之說。明人楊慎《升庵外集》在此基礎上認為“高齋十學士”——劉孝威、庾肩吾、徐防、江伯操、孔敬通、惠子悅、徐陵、王囿、孔爍、鮑至輔助蕭統編成《文選》。清代孫志祖在《文選理學權輿補》中也指出蕭統與“高齋十學士”共集成《文選》。南宋祝穆《方輿勝覽》在“《文選》樓”一條下釋文為:“梁昭明太子立,聚賢士共集《文選》。”清代《湖廣通志》等又沿用“《文選》樓學士”之說。據此,學界對輔助學士有“昭明太子十學士”“高齋十學士”“《文選》樓學士”三說。其中“昭明太子十學士”與“《文選》樓學士”并不矛盾;而根據蕭統的交游情況,“高齋十學士”并不可靠,受到文選學研究者的質疑。清代高步瀛在《文選李注義疏》中對“高齋十學士”進行考證,從而辨明高齋學士為“簡文遺跡,而無關昭明選文也。”[11]5王立群先生指出:“楊慎之說固陋,但楊慎說反映出諸學士撰集《文選》之事至明已流布甚廣。”[12]173現當代學者錢鍾書、屈守元、曹道衡、穆克宏、陳延嘉、俞紹初、許逸民、顧農、王立群、傅剛先生等學者均支持蕭統主編、學士協助的傳統觀點。“錢先生認為,昭明太子是主《選》政者,亦有學士協助。學士之操做必經太子同意,才可確定下來,否則無可能。”[13]149穆克宏先生指出:“《文選》的主編為昭明太子蕭統,這是沒有疑義的”[14]98,并在此立論的基礎上,認為以劉孝綽、王筠為主的“昭明太子十學士”等學士都參與了《文選》編撰工作。
力之先生提出的《文選》編選工作量不大的觀點,受到眾多選學研究者的認可,但這并不能證明《文選》為蕭統獨編。編撰《文選》最重要的工作不是閱八代千卷典籍,也不是繁瑣的校勘,而是從八代典籍中篩選出適宜入《文選》之文。這一最重要的工作是需要蕭統完成的,而其余的輔助工作完全可以由學士完成,此其一。其二,史書對歷史的記載也是有傾向性的,后人在解讀時也要基于情理,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學術研究需要堅實的文獻加以支撐,但不合情理的文獻未必“堅實”。陳延嘉先生指出,對歷史記載既不能盲目相信,亦不可輕易否定。東宮學士輔助蕭統完成編撰工作是其分內之事,不在字字如金的史書中加以體現也不為過,不能因史書未明確指出有蕭統學士加以協助而認定《文選》為蕭統“獨編”。《文鏡秘府論》《敦煌四部書六十年提綱》《玉海》等文獻雖不是史書,但其中關于蕭統有學士輔助的記載也未必通不可信。而以蕭綱命蕭繹編集,都指明何者參與編撰;李善等人也未指明有人輔助蕭統這樣的例證,亦是推論,都不能作為堅實的文獻依據。所以,根據文獻記載與情理層面來看,“蕭統獨編說”似未圓照。東宮學士協助的說法流傳千年,且年代與梁代較近的唐代文獻也多有此說,說明此說可信度很高。
2.東宮學士的職責
《梁書·昭明太子傳》記載蕭統“引納才學之士”“商榷古今”,于是東宮出現了“晉、宋以來未之有也”的“文學”盛況。對于參與編撰《文選》的東宮學士的情況,有“劉孝綽等”、“梁昭明太子召天下才子相共撰”、“昭明太子十學士”、“文選樓學士”等說法。這其中,有文獻記載的就有何遜、張纘、張率、張緬、到洽、陸倕、王筠等多人。經過何融的考證,任職于蕭統東宮之人有40人之多。而太子洗馬、太子舍人都是掌管文記的官職。史書雖未明確記載這些“才學之士”協助蕭統編撰《文選》,但輔助太子編集著述本來就是這些門士的職責,而蕭統又愿意與他們商討。而且八代的詩文“卷盈乎緗帙”,數量較多又良莠不齊,需要門士加以協助。所以,于情于理,東宮學士都會輔助蕭統編成《文選》。陳延嘉先生指出,學士的協助工作在于三個方面:其一,為蕭統的需要去查找資料。“東宮有書幾三萬卷”,需要學士逐一查找;其二,蕭統讓學士對篇目、文體等具體問題提供自己的意見。這樣才符合《梁書》中“討論墳藉”“商榷古今”之“恒”“常”。正是由于不斷地學習與研討,蕭統才能在文評理論上不斷進步,不滿足于已經編撰好的《詩苑英華》,而繼續編撰了流傳至今、意義深遠的《文選》。其三,對《文選》詩文的語言進行修改。蕭統編集著述,東宮學士加以輔助是分內之事,《史書》不必一一記載。古代有掛名的習慣,但也有編撰圖書的協助之士未被記載的慣例。曹之稱此為古代的習慣用法,就如劉義慶的《世說新語》一樣,本來有眾人輔助,卻并沒記載他們的名字,這在古代是合情合理的。錢鍾書先生在《管錐編》中指出:“《古詩十九首》……裁剪長短句作五言詩,移易其前后,皆出‘文選樓中學士’之手。”“《贈白馬王彪》……是原詩題暨小序皆遭‘文選樓中學士’芟削也。”錢鍾書先生認為,《文選》中的詩文字句被刪改,多是“文選樓中學士”所為,而這種刪改多數是“潛改而不言”的,錢鍾書對此也持肯定態度。“錢先生認為,昭明太子是主《選》政者,亦有學士協助。學士之操做必經太子同意,才可確定下來,否則無可能。”[13]149這也說明了眾多學士協助,但把握方向、起決定作用的人依然是蕭統。
《文選》編撰過程中東宮學士加以輔助的觀點,受到歷代學者的認同,其中劉孝綽的受關注度最高。雖然清水凱夫先生的“劉孝綽中心說”似未圓照,但劉孝綽的重要作用已經引起學界的廣泛關注。曹道衡、顧農、傅剛先生等學者也指出了劉孝綽的重要貢獻。《梁書·劉孝綽傳》記載蕭統與劉孝綽關系密切。劉孝綽編成《昭明太子集》并在《序》中說:“居陪出從,逝將二紀。”曹道衡、傅剛先生指出:“從他《序》中所言看,劉孝綽的文學思想與蕭統是一致的,這也可能是蕭統特別看重他的原因之一。”[15]157蕭統對劉孝綽的重用,是因為劉孝綽與自己的思想比較一致。在編撰的工作中,劉孝綽能夠較好地領會蕭統的意志,蕭統任用劉孝綽更加得心應手。所以,《文選》所體現的主要意志還是來自于蕭統。
根據史書記載、歷代學者的支持,以及蕭統有時間與能力進行《文選》的編撰,可見從文獻與情理的多角度分析皆可得出蕭統是《文選》主編者的結論。而東宮學士協助蕭統完成了編選工作,功不可沒。孔子擁有“至夫子繼圣,獨秀前哲”[16]2的地位,繼承了過去的圣人并超過了他們;而蕭統之《文選》超越了梁代以前的所有選集,在代代相襲的傳承與接受中,依然是選本中的精華。所以,蕭統“選圣”之冠實至名歸。
[參考文獻]
[1]許逸民.“新文選學”界說[J].鄭州大學學報,2010(5).
[2]清水凱夫.六朝文學論文集[M].韓基國,譯.重慶出版社,1989:1.
[3]姚思廉.梁書[M].北京:中華書局,2014:171,167,167,165.
[4]李延壽.南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5:1312.
[5]蕭統.文選[M].北京:中華書局,2013:3.
[6]蕭統編,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注.六臣注文選[M].北京:中華書局,2012:1.
[7]劉肅.大唐新語[M].北京:中華書局,1984:42.
[8]蕭繹撰,許逸民校箋.金樓子校箋上冊[M].北京:中華書局,2011:1.
[9]蕭統著,俞紹初校注.昭明太子集校注[M].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3,250,244-245.
[10]清水凱夫.從全部收錄作品的統計上看《文選》的基本特征[J].長春師范學院學報,1999(1).
[11]高步瀛.文選李注義疏[M].北京:中華書局,1985:5.
[12]王立群.現代《文選》學史[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173.
[13]陳延嘉.錢鍾書文選學述評[M].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1:149.
[14]穆克宏.文選學研究[M].廈門:鷺江出版社,2008:98.
[15]曹道衡,傅剛.蕭統評傳[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157.
[16]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