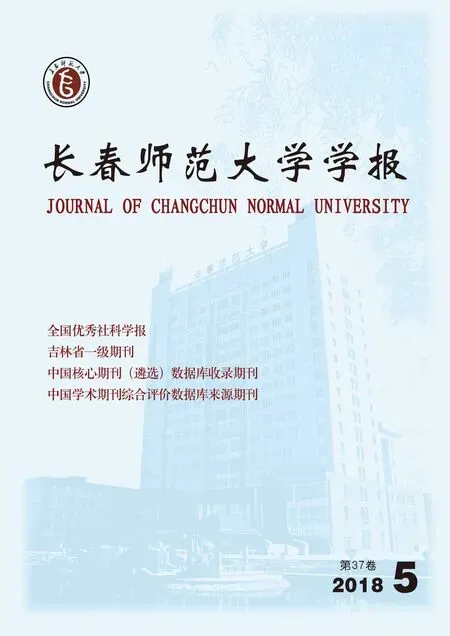從“審名察形”到“太上無刑”
——“名”視域下《黃帝四經》之治道及其現代價值
廖同真
(安徽大學,安徽 合肥 230031)
1973年,長沙馬王堆三號古墓出土了一批帛書,包括《經法》《十大經》(又稱十六經)《稱》《道原》。經專家鑒定,它們就是古佚書《黃帝四經》。[1]《黃帝四經》的理論體系繼承了道家老子的學說,又發展了老子學說。其對道家思想的發展表現在道論、天地自然和道治天下等方面,也表現在對法家、陰陽家的批判吸取。它在道治的前提下引入法治,以陰陽學說解答自然和人事,解釋刑德生殺。《黃帝四經》治道的方法建立在事物發展的對立雙方能夠相互轉化的基礎上,只有掌握事物發展的“靜養相作”“相與相成”,才能使自己立于不敗之地。在此方法下,它提出“刑名”確立下“無為而治”的社會政治思想。“名”是《黃帝四經》治道的重要部分,“刑(形)名立,則黑白之分已”[2]10,“故執道者之觀于天下也,必審觀事之所始起,審其刑(形)名”[2]187,“天下有事,必審其名”[2]173,“名功相抱,是故長久。名功不相抱,名進實退,是謂失道,其卒必有身咎”[2]421。“名”不僅能夠界定事物性質,而且是社會政治治理與否的重要因素,它貫穿于《黃帝四經》治道的整個過程。文章以“名”為線索來梳理《黃帝四經》治道理論。
一、《黃帝四經》治道之起始
“欲知得失情,必審名察形”[2]336。審“名”察“形”是《黃帝四經》治道的起始,之所以如此,源于《黃帝四經》對“名”“形”的設定以及“道”“名”“法”三者的內在關系。
與《老子》一樣,《黃帝四經》將“道”置于至高的地位,認為它是產生萬物的根源。《經法·道法》說:“虛無刑(形),其寂冥冥,萬物之所從生”,“無刑(形)無名,先天地生”[2]5。“道”使得“萬物得之以生,百事得之以成”[2]440。“道”生的每一事物都有其本然的形態,以及與其本然形態相對應的位置稱謂——“名”。當物的形態與其位置、稱謂一致的時候,事物自然而然地得其所“正”。“凡事無小大,物自為舍。逆順死生,物自為名。名形已定,物自為正”[2]25,“是故天下有事,無不自為刑(形)聲號矣。刑(形)名已立,聲號已建,則無所逃跡匿正矣。”[2]10“道”的存在首先體現在萬物之“形”中。《稱》說:“有物將來,其形先之。建以其形,名以其名。”“道”生物的時候,“形”是先出現的,“名”在“形”之后出現。同時,物的“名”“形”出現是一種“自”現,即自然而然地出現。自現的“形”“名”相符,事物得以成立。“‘名’的產生是隨著‘形’自然而來的,一旦‘形’‘名’搭配穩妥之際,該事物也同時自然成立。”[3]事物本然的“名”是其最理想的狀態,人要想知曉事物的這種理想狀態,首先要做的是“虛無有”。只有達到“無執”“無處”“無為”“無私”的“虛無有”狀態,才能接近“道”,進而照見事物的本來面目。
《經法·道法》說:“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繩,而明曲直者也。故執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廢也。故能自引以繩,然后見知天下而不惑矣。”“法”由“道”而生,“名”也是由“道”而來,“道”“法”“名”相互聯系著。由于“名”含義的多重性,“道”“名”“法”之間的關系也有三種情況。
其一,“名”與“道”含義相似,有時候都作為“法”的依據。如:“昔天地既成,正若有名,合若有刑(形)。乃以守一名。上淦之天,下施之四海。吾聞天下成法,故曰不多,一言而止。循名復一,民無亂紀”[2]286。在這里,“名”是事物的本然狀態,它既是事物的發展必先確定的事項,又是事物發展的最終目的。只有明確事物的本然狀態,現實事物的狀態才會有所參照,發展起來才知道從哪里著手;只有明確事物發展的最終目的,發展才會有所指向。
其二,“名”和“法”含義相同,都指職分、制度,“道”是它們的形上根據。如“道生法”一段中,“生法”的主語有兩個:一個是“道”,一個是“執道者”。二者都生“法”,但它們所生的法含義有所區別:“道生法”所生之“法”是從形而上層面來說的,與此相適應的“法”應該也具有形上的性質,是抽象性、普遍性的“法”,可以稱為“道”的規律;“執道者”所生之“法”是從形而下的層面來說的,更多的是指國家政治層面的制度、法度、職分。后者的“法”在含義上與作為職分、制度之“名”的含義是相同的。“故有時候《黃帝四經》也將名刑并用、名禁連用,如‘正名修刑’、‘正名施(弛)刑’、‘名禁而不王者死’等。”[4]社會政治治理中“職分”“制度”的重要性,在于它們規定了社會政治中各項人事的具體位置,使人的活動和事的處理有了明確的指導而不陷入混亂。
其三,“名”是“道”與“法”的媒介。《經法·名理》說:“天下有事,必審其名。名(理者),循名究理之所之,是必為福,非必為(災)。是非有分,以法斷之;虛靜謹聽,以法為符。”在這里,天下有事先審“名”定“分”,之后再用“法”判斷事與名是否相符。從這點上講,“名”在邏輯上是先于“法”而在的,有“名”再有“法”。故有些學者也說,“名”是“道”與“法”的媒介。如王沛先生認為,“‘名’實際上是‘道生法’必要的媒介,若‘無名’也就‘無法’;‘名’則是聯絡‘道’和‘法’的節點所在。”[5]白奚先生認為,“《黃帝四經》雖然開宗明義聲稱‘道生法’,但畢竟使人一時難于理解和把握。在道與法之間有了‘名’這一中介,便顯得更加順理成章易于把握,其法理學說也顯得更加充實、豐滿了。”[6]曹峰先生認為,“對于《黃帝四經》中所見三大概念——‘道’‘名’‘法’,過去只重視‘道’‘法’,而輕視‘名’,對于《黃帝四經》的思想結構,只講‘道法’關系二元結構,而不講‘道名法’關系三元結構。”“‘道’在最前端,‘名’是從‘道’到‘法’的媒介和過渡階段,‘法’則是最終的目標與手段。”[7]作為“道”“法”之間的載體,“名”是“道”的普遍之“法”得以下貫的媒介。因為只有審定了“名”,“道”和“法”才有承載者;只有審定了“名”,“道”“法”才能通過“名”對萬物的涵攝作用,將《黃帝四經》的治道輻射到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
二、《黃帝四經》治道之過程
《黃帝四經》認為,君主治理國家,首要干的事情是“審其形名”。當對象之“名”定了之后,就可以獲知對象是逆是順、是死是生、是存是亡、是興是壞,才能從事“立天子、置三公”的重大政治決策。就是說,君主查“名”,即事物本然的那個位置,是為了確立政治生活中各種事務處理的標準。“一旦‘名’(有時候稱‘形名’)系統得以確立,并能保持在‘正名’之狀態,‘執道者’就可以依賴‘名’(形名)系統自發地發揮作用,從而達到‘無為’的境界。”[8]確立了事務處理的標準,把事物維持在正“名”的狀態是《黃帝四經》治道的過程,也是事物向“道”復歸的過程,這個過程就是“循名復一”。“循名復一”展開為刑德生殺等一系列正“名”的過程。
然而,現實政治生活中的各種事物的“名”,即其現實所處的位置未必是其初始的那個自然而然的位置:有些“名”是“奇”的,有些是實際狀態與其本然之“名”不相符,這都會引起混亂。“名功相抱,是故長久。名功不相抱,名進實退,是謂失道,其卒必有身咎”[2]421,“名實相應則定,名實不相應則爭”[2]423,“名正者治,名奇者亂”[2]434。而君主如何規正不得其然的事物之名,使得名“正”?《黃帝四經》認為,君主首先要“無執”“無私”“無處”“無為”,成為“執道者”;其次要參照“天地之恒道”,觀照現實政治的具體事物,并進行相應的賞罰。君主成為“執道者”,照見事物本然之“名”,這一步是循“名”,它側重君主內在的修為;參照“天地之恒道”,使事物維持在其“正名”的狀態下,這一步是“復一”,它側重君主的外在事功。整體上,《黃帝四經》文本的側重點不在君主內在的修為,而在于君主外在的事功。故,對“天地之道”的參照可以說是其治道過程的絕大部分內容。天地之恒道的內容是什么?君主如何參照?《黃帝四經》中有多個地方論及,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點內容。
第一,“天地之道”是天地四時自身的運行規律。“道”生天地萬物,但具體的化生過程是由天地陰陽來協作完成的。“道”“始判為兩,分為陰陽,離為四時,剛柔相成,萬物乃生”[2]427。獨陰獨陽皆不能成物;陰陽協調,變化才能產生。“地俗德以靜,而天正名以作。靜作相養,德虐相成。兩若有名,相與則成。陰陽備物,化變乃生”[2]429。天地陰陽的相與相成,進一步演變成四時的更替。春夏秋三個時節是天地生養收獲的季節,冬是天地肅殺潛藏的季節,四季生殺有序地更替著。天地陰陽以及四時的更替規律成為現實政治生活效仿的對象,尊卑之事、貴賤之位因天地陰陽而得以確定。政治生活中養伐之事,因天地之道、四時交替的規律而有了治理標準。
第二,“天地之道”表現為“動靜有時”以及“刑德”二柄的準確應用。事物因其“名”而有分,現實政治之事因為天地之道而得以判定,并得以向其本然之“名”復歸。因順天地之道,該養則養,該伐則伐。《黃帝四經》說:“毋止生以死,毋御死以生,毋為虛聲。聲溢于實,是謂滅名。極陽以殺,極陰以生,是謂逆陰陽之命。極陽殺于外,極陰生于內。已逆陰陽,又逆其位,大則國亡,小則身受其殃。故因陽伐死,因陰建生。當者有數,極而反,盛而衰:天地之道也,人之理也。逆順同道而異理,審知逆順,是謂道紀”[2]420。尊卑合位,動靜遵時,養伐合度,則名形相合無有不順。“天執一,明三,定二,建八正,行七法,然后施于四極,而四極之中無不聽命矣”[2]421。“六順六逆乃存亡興壞之分也。主上執六分以生殺,以賞罰,以必伐。天下太平,正以明德,參之于天地,而兼覆載而無私也,故王天下”[2]419。相反,如果陰陽錯位、動靜不時,則會名形相溢而發生逆亂。“動靜不時,種樹失地之宜,則天地之道逆矣。臣不親其主,下不親其上,百族不親其事,則內理逆矣。逆之所在,謂之死國,死國伐之。反此之謂順,順之所在,謂之生國,生國養之”[2]422。
第三,“天地之道”注重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十大經·姓爭》說:“明明至微,時反以為幾。天道環周,于人反為之客。爭作得時,天地與之。爭不衰,時靜不靜,國家不定。可作不作,天稽環周,人反為之客。靜作得時,天地與之;靜作失時,天地奪之。”能熟練掌握天地的“養生伐死”規律,人就能懂得時機的把握和風險危害的規避,并由客反主,促進自身的成功,“作爭者兇,不爭亦無成功”[2]427,“圣人正以待之,靜以須人。不達天刑,不襦不傳。當天時,與之皆斷;當斷不斷,反受其亂”[2]427。《黃帝四經》并沒有一味地強調不爭,而是認為根據事物發展的規律該爭的時候就得爭,該斷的時候就得斷,這與老子著重突出的守雌不爭是不同的。此外,依據陰陽四時的規律,在事物發展的過程中,人必定以陰陽刑德、四時養伐相與相成的矛盾態度看待事物,從而動態地把握事物的發展,掌握事物量變質變之度,使得萬物的發展恒處于“度”之內,得以刑名合當。
三、《黃帝四經》治道之目的
《稱》說:“善為國者,太上無刑,其次正法,其下斗果訟果,太上不斗不訟不果。夫太上爭于化,其次爭于明,其下救患禍。”對國家社會政治的治理而言,最理想的狀態是不用設置刑罰,其次是法度的正定,再其次是能夠以果斷堅決的態度和行動處理天下的爭端和國內的獄訴,最次的是不能果斷堅決地處理爭端和訴訟。國家政治事務的治理不用到刑罰,說明政治事務恒處于陰陽得位、生養持續的平穩狀態,即“名形相應”“名正”的狀態。“太上”之政爭于“化”,指的是好的國家治理在于民眾的教化,民眾“化”則自然“無刑”。民之“化”,從君主的角度講,是君主領導下政治生活領域中法度、名分制度的合理恰當;從民的角度講,是民的自“正”。
“上人正一,下人靜之;正以待天,靜以須人”[2]429,民化的前提是“上人”之“正”,“上人”即君主。在君主“正”的前提下,才有民一系列的“化”。前文已述,“上人”之“正”主要是“上人”做到“虛靜”,順“道”,上化下的手段主要是依據陰陽四時的規律而進行相應的“刑德相養”。民在君主“正”的前提下而不斷走向“化”,拿國家的征戰而言,“一年從其俗,二年用其德,三年而民有得。四年而發號令,五年而以刑正,六年而民畏敬,七年而可以正。一年從其俗,則知民則。二年用其德,則民力。三年無賦斂,則民不幸。六年民畏敬,則知刑罰。七年而可以正,則勝強敵”[2]417。又如,“人之本在地,地之本在宜,宜之生在時,時之用在民,民之用在力,力之用在節。知地宜,須時而樹,節民力以使,則財生,賦斂有度則民富,民富則有恥,有恥則號令成俗而刑伐不犯,號令成俗而刑伐不犯則守固戰勝之道也”[2]418。“天道壽壽,播于下土,施于九州島。是故王公慎令,民知所由。天有恒日,民自則之。爽則損命,環自服之。天之道也”[2]433。從知“民則”到“民不倖”,從民“有恥”到民“刑罰不犯”,再到“民自則之”,這既是統治者自“正”的結果,也是民自身不斷走向對其名分的認肯和自覺,即民自“正”的結果。
雖然都自“正”,但作為“上”的君主與作為“下”的民的具體職分是不一樣的。《黃帝四經》承認這種區分的存在,而且認為“等級是天經地義的,名分是必須遵守的。”[9]“天地有恒常,萬民有恒事,貴賤有恒位,畜臣有恒道,使民有恒度。天地之恒常,四時、晦明、生殺、輮(柔)剛。萬民之恒事,男農、女工。貴賤之恒位,賢不肖不相放(方)。畜臣之恒道,任能母過其所長。使民之恒度,去私而立公”[2]416。所以,君和民自“正”的內容是有別的:在“上”的君主主要在“虛無有”以及“審名”的前提下撥正事物之“名”,教化萬民;而在“下”的民要做到對其自身名分、職責的循守和對“上”之政治的安順。作為“上”的君主從自身的“虛無有”出發,借助天地之道的“刑德相養”之道來審名察形,使得國家各方事務刑名相合、名聲章名,進而使萬民得到教化,國家達到無刑。這是走了一條從“無為”到“有為”,再從“有為”到“無為”的道治之路。《黃帝四經》講求“循名復一”,從無為之道出發,最終還是要回復到無為之“道”中去。
四、《黃帝四經》治道之現代價值
《黃帝四經》從審核事物本始之形名出發,以事物初始的形名為基點來觀照現實政治生活中的事物,進而因順“法”,即天地之道,涵養“名正”之事物和伐殺“名奇”之事物,促使其向本然之“名”回歸,并最終使得國家政治的治理提升到“無刑”的狀態。這個過程包含著法的權威與對人的關懷,體現了尊重自然生態規律的態度以及謙下包容的精神。
《經法·道法》說:“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繩,而明曲直者也。〔故〕執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廢〔也〕。”這段話中既有道生法,也有圣人制法,它“從理論與現實、形上與形下兩個層面闡明了法律的發生。”[10]現實中判斷一切是非曲直的“法”,以至高無上之“道”為依據。作為形下的“立法者”,制定了法度之后不能凌駕于法度之上。這不僅從形上之“道”的角度確立了“法”的權威,也從形下之“法”的不可侵犯性彰明其權威性。依法治國是我國的一項重要任務,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全面依法治國,十九大繼續明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依法治國,重要的一環就是要保證法的權威性與不可侵犯性。《黃帝四經》強調法的權威性對當今的依法治國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四經》確立了以“名”為核心、刑德相養的道治系統。通過“正名”,萬事萬物向其本然的位置回歸而各得其安。“名”雖然有等級之分,但作為領導者,必須是無私無執的“執道者”,才能實現萬物的“正名”。《黃帝四經》的道治固然使得萬物向“道”復歸,但這個過程在現實政治生活中同時也是充分實現自身發展的過程,這體現了《黃帝四經》對“人”的關懷。《黃帝四經》有時會把利民提升到“義”的角度,如:“圣人舉事也,合于天地,順于民,祥于鬼神,使民同利,萬夫賴之,所謂義也”[2]426。對“人”的關懷,實現人全面的發展,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一個重要目標。十九大報告強調堅持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保證全體人民在共建共享發展中有更多獲得感,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黃帝四經》中的利民、安民思想是可以助力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
《黃帝四經》對天地的自然運行規律有著細致的觀察,如:“天建八正以行七法:明以正者,天之道也;適者,天度也;信者,天之期也;極而反者,天之性也;必者,天之命也;順正者,天之稽也;有常者,天之所以為物命也:此之謂七法”[2]422。“四時有度,天地之理也;日月星辰有數,天地之紀也。三時成功,一時刑殺,天地之道也”[2]424。同時,《黃帝四經》認為,人事只有因順天地之道才能夠趨福避禍,“天天則得其神,重地則得其根。順四時之度而民不有疾”[2]421;而“不天天則失其神,不重地則失其根,不順四時之度而民疾”[2]426。《黃帝四經》細致地觀察天地自然之道,并自覺地將之作為行事的原則,這一方面表現了其對天地自然之道的敬畏,另一方面則表現了其對天地自然之道的依賴。這種尊重天地自然的規律、與天地之道相融合的思想,包含著濃濃的自然生態意義。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正朝著美麗中國的方向前進,不斷推進生態文明建設,這體現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思想,與《黃帝四經》對天地自然的因順遙相呼應。
《黃帝四經》認為在政治生活中,統治者(圣人)審核名形,首先必須無私、無執、無處,只有如此才能本真地照見事物的名形。“見知之道,唯虛無有”[2]415,“公者明,至明者有功。至正者靜,至靜者圣。無私者知(智),至知(智)者為天下稽”[2]415。只有虛靜才能近“道”,才能沒有偏見地觀照事物,這體現了“道”對萬物的無私與包容。同樣,作為“執道者”的統治者只有對萬物無私和包容,才能很好地對事物進行管理。《黃帝四經》的這個思想來自于老子。《老子》云:“致虛極,守靜篤。”“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只有虛靜知常,才能做到包容和公正;只有做到包容和公正,才能長久地存在下去。《黃帝四經》的這個道理,對我國當今的文化建設及世界各國和諧共處有重要的借鑒意義。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只有積極開拓創新,不斷與世界各種文化交互借鑒,才能不斷向前發展。在當今的國際局勢中,我們堅持推動構建穩定的國際秩序和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二者的前提必須是世界各國能夠平等包容地對待彼此,尊重彼此所選擇的發展道路,不然則無法達到。
[參考文獻]
[1]唐蘭.黃帝四經初探[J].文物,1974(10):48-52.
[2]陳鼓應.黃帝四經今注今譯[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
[3]陳桂麗.戰國時期的黃老思想[M].臺北:經聯出版社,1991:73.
[4]艾永明.黃帝四經中“名”的法律意義[J].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2):177.
[5]王沛.黃老“法”理論源流考[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67-70.
[6]白奚.黃帝四經與百家之學[J].哲學研究,1995(4).
[7]曹峰.“名”是黃帝四經最重要的概念之一[A].徐炳.黃帝思想與道、理、法研究[C].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244:247.
[8]曹峰.黃帝四經所見“執道者”與“名”的關系[J].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3):19.
[9]白奚.稷下學研究:中國古代的思想自由與百家爭鳴[M].上海:三聯書店,1998:122.
[10]陸建華.黃帝四經——黃老道學的奠基之作[J].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3):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