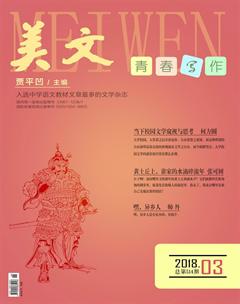日子1
沈姚覦
從老家回來的時候,已經很晚了。
燈紅酒綠的沉迷在夜色里的城市,以一種不同于農村靜謐的喧囂迎接著每一位闖入的客人,快節奏的生活打亂了人們古老而精準的生物鐘。走到大門前,三樓的燈依然堅持地亮著,依稀能看到一個忙碌的身影。回到家,家里的時鐘剛好響起,撕下一頁舊日歷,日子便又過了一天。
回老家只是一時的興起。
老家許久沒見的黃狗已經對我陌生了,一看見我便汪汪大叫,犬吠著不讓我進來。奶奶走出來,一臉驚喜,拘謹地把手在圍裙上擦了又擦,連聲喚我進來。
鍋里正煮著米,旁邊的水燒開了,咕嚕嚕的冒著氣泡。古舊的八仙桌上依然擺著那張太爺爺的遺像,桌上裝著的瓜果也沒變,仿佛不曾受過時間的侵蝕似的。奶奶曾說過,太爺爺是在日軍侵華的時候死掉的。
我出生得太晚,對此毫無印象,只能做無聊的無邊際的幻想。想象當年戰亂的年代,家里沒了頂梁柱,日子是如何度過的。想象家里人生活艱苦,連野菜都挖不到;想象炮彈亂竄,日本人拿著裝著刺刀的槍,挨家挨戶的搜查,人們躲在避難的洞里瑟瑟發抖。然而每次問奶奶,她總會輕描淡寫的說:“日子就這樣過來的。”幼時的我總不信,現在卻像明悟了什么,對著遺像恭敬地鞠三個躬,然后想著今天中午吃什么。
出門在鄉間小路上散步,常青藤散發著生機,田里的水稻油油的綠著,花開的很好,像是在期待明天,沐浴著平凡而溫柔的歲月。
看見一個藍布衣裳的女人,挽著褲腳,手持塑料紅盆到河邊浣洗,白色的泡沫隨著女人搓揉的動作于不甚清明的湖面上浮動。女人大抵是不知道這條河曾染過先烈的鮮血的,可她仍然跪在青石鋪的階上,以一種虔誠的神圣的動作揉洗著,莊重的樣子仿佛她正在浣洗的是她的整個世界。
也看見了傍晚每家每戶裊裊飄起的炊煙,灰蒙的綢帶迎著風起舞融入玫瑰色的天際,配樂是鍋鏟碰撞著鍋底的叮當聲。天色算不上很晚,公雞也沒有按時的啼鳴,只是家家戶戶都心有靈犀般的改了時辰,像是被時代急促的步伐催促的緊了,又像只是幾個人無趣時的臨時起意——那炒菜的聲音也是不急不緩的,沿著莫名的韻律丁丁當當愣是要敲出生活的圓舞曲。
或許當年也是如此吧,小孩在不久前留下的彈坑上玩耍嬉戲,大人一邊挑采著果腹用的野菜一邊聊著鄉里的家常,學過點東西的便談談政治,眉眼間是無法忽略的不被戰爭所侵蝕的安穩平和。是人骨子里的處變不驚,造就了歲月靜好的安寧。
忽然想起曾經看過的一篇文章,題目與作者皆記不清了,只是依稀記得那段很喜歡的結尾,翻來覆去讀過好幾遍:
“從(南京大屠殺)紀念館里出來,陽光很好,人們嬉笑著談論著趣事,孩子們圍著攤販買糖。”
逝者已逝,生命永流。
回家的路上,我經過一座正在施工的大樓,看到一被抱在懷中的孩子,吮著手指,踢踏著小腿,以一種純凈無暇的眼神望著我,動作一如孩提時的自己。世界總是在變,日子走在人的前面。只是人在追趕日子的同時,他的許多也以一種頑強而堅韌的姿態矗立在那,坦然自若。
不是日子支配了我們,而是我們征服了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