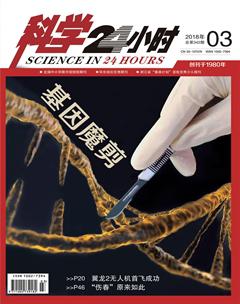地震預報為什么難
船舷
目前,在地震學界內有兩種截然對立的觀點:一種是地震不可知論,認為在人類對地球內部知之甚少的情況下,預報地震是不可能的;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地震是有規律可循的,探索其規律進行短期預報并非完全不可能。兩種觀點的對立十分尖銳,因不可知論占據主流地位,所以社會上一度形成這樣的鑒別標準:說地震不可知的是科學家;說地震可以預報的可能是騙子。

不錯,就人類當下的科技水平而言,要想清晰地搞清地殼的運動規律還存在一定困難,在此背景下進行地震預報研究仍是難題。據說在納稅人的呼吁下,美國和日本等西方國家相繼壓縮用于地震預報的科研經費,特別是日本正式宣布退出地震預報的合作研究。他們認為,與其讓遙遙無期的空洞研究浪費資金,還不如扎扎實實地做好防災救災的實際工作。固執的美國科學家則不然。他們繼續深鉆大陸板塊連接處的廢棄油井,然后把監視感應器放置其中,試圖以此了解板塊運動的規律和地震發生之前的異常征兆。
而我國的情況有點復雜。從形式和規模上來看,我國的地震研究監測機構無疑是全世界最健全、最龐大的。可遺憾的是,近些年我國科研人員能拿得出手的研究成果卻越來越少。雖然他們的經費來源由政府直接撥付,不受納稅人態度的左右,但唐山和汶川大地震讓他們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壓力,網絡上責難他們無能的聲音始終沒有停止過。
中國的地震專家真的如此無能嗎?其實不然,就筆者熟知的地震學界的幾位專家學者,他們對地震研究都有自己的貢獻,也都有過比較準確預報地震的經歷。目前,世界短臨預報的最高準確紀錄是30%左右,這個記錄就是由中國保持的。
即使如此,地震預報卻仍然是全世界公認的棘手難題。其原因很簡單,我們對地震這個復雜的自然現象的整體認識尚處在模糊的探索階段。從科學上講,預測地震有兩條途徑:一是尋找地震前出現并且與地震發生有明確關系的自然現象,也就是所謂的震兆,進而利用震兆預測地震。二是認識從地震孕育到發生的基本規律,即震因,利用震因對地震的孕育發生過程做出準的確識別。關注震兆與研究震因兩者缺一不可。
遺憾的是,震兆與震因至今仍如兩座科學山峰橫亙在我們面前,讓我們難以逾越。

在地震史上,中國號稱曾成功預報了海城和青龍地震,但世界地震學界對此的評價是:偶然的運氣。有人說,我們曾經成功預報過海城和青龍地震,為什么不能把這兩次預報的經驗發揚光大,進行后續的地震預報工作呢?
問題的關鍵就在這里,地震預報難就難在它的成因、 機理和觸發條件等非常復雜多變,預測方法具有不可復制性。這次成功有效的預報手段,很可能在下一次地震預報中就失靈了。
正如著名探險家兼地質學家位夢華所說的,地震預測迄今還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不論在國內還是國際上,還很難完全準確地預報地震。另外,目前一些地震預測的研究方法也不完善,比如一些地震前兆、動物習性的變化具有很復雜的因素。有些動物行為,地震學家解釋為地震前兆,而生物學家的解釋可能又是從生物學的角度出發。還有一點就是,大部分的震兆也都是在地震后又被翻出來討論、研究后得出的,如唐山大地震。
地震預報的難度,核心問題還在于人類對地球構造運動理論的認識尚不成熟。人類對地球內部的了解,可能還不如對月球,甚至是對火星的了解深入。即便有一些經驗和知識,也是此一時的知識和經驗,不能用于彼一時,如海城的經驗無法用于唐山地震,也不可能完全應用于后來的汶川等一系列地震。
此外,地震預報,特別是短臨預報之所以成為世界性難題,是因為政府和公眾的需求與科學現狀之間存在著無法破解的矛盾。當地震檢測機構將可能發生地震的推斷上報給政府時,負責決策的官員會嚴肅地發問:“你們的把握有多大?”這就讓檢測機構犯難了。最終只得“繼續檢測”。
政府的確有政府的難處,它的著眼點是盡量保證整個國家的正常秩序不被打亂。如果接到一個把握只有30%的大地震預報,無論是東西方哪一個國家的政府,都是一樣的戰戰兢兢,不知該如何是好。

為此,聯合國相關機構建議各國政府采取開放型的防災備災策略,變被動為主動。
開放型的地震預報,就是向局部的社會公眾開誠布公,既告訴大家地震研究中的困局現狀,也告知大家你腳下地殼的活動情況以及可能帶來的災害后果,將避險判斷和決定權交給公眾。在有可能出現震情的日子里,每天都有信息公布,至于采取什么樣的避險措施,聽憑公眾自己的判斷,就如天氣預報播報的降雨概率是30%,帶不帶雨傘純粹是你個人的事情。
當然,地震預報屬于危機管理范疇,就必須納入危機處理的軌道。比如,根據當下社會整體形勢,地震預報選擇在什么時候播報,先公布到什么程度等等,都是有講究的,需由哪個層面的專家綜合判斷,以怎樣的方式公布信息等,也都是需要處理危機問題的專家們周密斟酌的,必須防止事態由自然危機轉變為社會危機。
可以肯定的是,即使所有的科學難題都解決了,要想圓滿順利地預報地震,仍然不是一件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