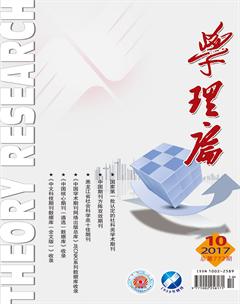20世紀(jì)30年代中國(guó)本位文化討論再認(rèn)識(shí)
康健
摘 要:關(guān)于20世紀(jì)30年代的中國(guó)本位文化討論,學(xué)界一直將其概括為西化派與中國(guó)本位派之間的論爭(zhēng),但是詳細(xì)研究當(dāng)時(shí)知識(shí)分子參與討論的文章及表達(dá)的觀點(diǎn)與思想,里面?zhèn)鬟f了更深的思考與更開(kāi)闊的思路。這次文化討論中知識(shí)分子對(duì)于民族認(rèn)同與文化選擇的理性思考既超越了之前文化論爭(zhēng)中復(fù)古與西化的極端,也擺脫了簡(jiǎn)單的文化折中主義,是以本民族特色、本國(guó)國(guó)情為出發(fā)點(diǎn),提倡在固有文明與西方文明之外建設(shè)一種全新的民族新文化,這是人們對(duì)于中國(guó)文化問(wèn)題認(rèn)知的進(jìn)步,也對(duì)未來(lái)中國(guó)文化發(fā)展的路向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
關(guān)鍵詞:中國(guó)本位;文化討論;民族文化觀
中圖分類號(hào):G04 文獻(xiàn)標(biāo)志碼:A 文章編號(hào):1002-2589(2017)10-0188-02
1935年1月,王新命、陶希圣、黃文山等十位大學(xué)教授聯(lián)合署名的《中國(guó)本位的文化建設(shè)宣言》在《文化建設(shè)》月刊上發(fā)表,《宣言》反思了當(dāng)時(shí)社會(huì)流行的復(fù)古與西化的文化思潮,倡導(dǎo)了一種以“中國(guó)本位”為核心的新文化觀。《宣言》一出,各地紛紛召開(kāi)文化座談會(huì),報(bào)紙、雜志、名流學(xué)者、政客紛紛發(fā)表文章參與討論,相關(guān)文章多達(dá)150多篇,討論持續(xù)半年之久,在整個(gè)社會(huì)引起廣泛思考。這次文化大討論是鴉片戰(zhàn)爭(zhēng)以來(lái)人們對(duì)于文化的古今東西問(wèn)題爭(zhēng)鳴激辯的延續(xù),是20世紀(jì)30年代中華民族面臨亡國(guó)滅種的民族危機(jī)之下,知識(shí)分子對(duì)于民族認(rèn)同與文化選擇的理性思考,促成了以民族為本位的新型現(xiàn)代民族文化觀的初步形成,在近代中國(guó)文化轉(zhuǎn)型的道路上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huán)。
一、五四以來(lái)文化價(jià)值判斷與取向的理性思考
對(duì)于20世紀(jì)30年代中國(guó)本位文化討論,學(xué)界曾批評(píng)其為國(guó)民黨文化統(tǒng)治政策立言的意識(shí)形態(tài),并將其概括為中國(guó)本位派與全盤西化派之間的論戰(zhàn),但詳細(xì)研究當(dāng)時(shí)參與討論的人員以及發(fā)表的相關(guān)文章,這次討論雖有政治背景,但更是對(duì)于文化問(wèn)題的深入思考與理性分析,參與討論的不僅有以十教授為代表的中國(guó)本位派和以陳序經(jīng)為代表的全盤西化派,還有胡適等理性西化派,吳景超、潘光旦等溫和中間派,討論中各方各派就中國(guó)文化的發(fā)展方向,如何創(chuàng)新中國(guó)文化,如何實(shí)現(xiàn)中國(guó)文化現(xiàn)代化等問(wèn)題展開(kāi)激烈的討論,體現(xiàn)了五四以來(lái)知識(shí)分子對(duì)東西文化價(jià)值判斷與取向的理性思考。
不可否認(rèn),在20世紀(jì)30年代國(guó)民黨加強(qiáng)對(duì)全社會(huì)思想控制的時(shí)代背景下,中國(guó)本位文化討論能在全社會(huì)激起文化討論的大波瀾,肯定離不開(kāi)南京政府的支持。十位教授以學(xué)者的身份,通過(guò)民間的名義打出中國(guó)本位的文化大旗,正好配合了國(guó)民黨當(dāng)時(shí)力倡的“新生活運(yùn)動(dòng)”與三民主義宣傳,這不排除為國(guó)民黨提供意識(shí)形態(tài)支持的可能性。但是,十教授的身份背景非常復(fù)雜,有為國(guó)民黨搖旗吶喊,充當(dāng)國(guó)民黨文化宣傳口舌的,也有具有獨(dú)立見(jiàn)解,以國(guó)家危難、民族利益為使命的。另外,十教授的“宣言”在文化領(lǐng)域一石激起千層浪,支持者有之,批評(píng)者有之,一時(shí)間引起人們關(guān)于文化問(wèn)題更廣泛、更深刻的討論,這已經(jīng)超過(guò)國(guó)民黨所能控制的范疇,導(dǎo)致陳立夫在文化討論中明確宣示“訓(xùn)政者,亦即文明建設(shè)之工作也”[1]8,強(qiáng)調(diào)必須以“三民主義”為文化工作最高指導(dǎo)思想,以“建國(guó)大綱”為文化建設(shè)的基本綱領(lǐng),可見(jiàn),中國(guó)本位文化討論實(shí)際上是背離了國(guó)民黨以三民主義為文化建設(shè)最高原則的初衷的。雖有政治背景,但十教授的“宣言”卻重啟了人們對(duì)于文化問(wèn)題的思考,引起各派名流學(xué)者的積極回應(yīng),形成了五四以后又一次關(guān)于中國(guó)文化出路的大討論。
中國(guó)本位文化討論之所以能在社會(huì)上引起廣泛共鳴,造成轟動(dòng)效應(yīng),除了國(guó)民黨的暗中推動(dòng),更有其深層的時(shí)代因素與文化背景。西學(xué)東漸因受制于道器、體用、本末之說(shuō),并沒(méi)有給遭遇喪權(quán)與屈辱的近代中國(guó)帶來(lái)一線生機(jī),在民族生存危機(jī)面前,國(guó)人的民族觀與文化觀出現(xiàn)激烈沖突,陳獨(dú)秀一句“若是決計(jì)革新,一切都應(yīng)該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國(guó)粹、國(guó)情等鬼話來(lái)?yè)v亂”[2]道出了新文化派將西方文化視作現(xiàn)代文明的代表與救世良方的普遍心理。雖然,陳獨(dú)秀也并未完全否定固有文明,并未徹底放棄傳統(tǒng)文化,但在當(dāng)時(shí)的社會(huì)環(huán)境下,還是傳遞了一種只有以西方文明代替中國(guó)文明才能實(shí)現(xiàn)救亡圖存的觀念信號(hào),當(dāng)然,這種文化判斷與選擇的盲目性就容易造成民族特征的消失與民族精神的淪喪,這也是十教授為代表的一批知識(shí)精英所擔(dān)心的,因而,《宣言》開(kāi)篇即提出在文化的領(lǐng)域,已經(jīng)“看不見(jiàn)現(xiàn)在的中國(guó)了”[3]1。另一方面,一戰(zhàn)后西方世界的破落與蕭條引起學(xué)界一股告別西方,尋求救國(guó)新路徑的浪潮,東方文化派的興起、科玄論戰(zhàn)、中國(guó)社會(huì)史論戰(zhàn)等都體現(xiàn)了思想界對(duì)于西化的質(zhì)疑以及復(fù)歸傳統(tǒng)的要求,加之20世紀(jì)30年代日本加緊侵華的背景,知識(shí)精英們普遍意識(shí)到 “目前最為迫切的不是談文化等問(wèn)題,而是如何求得民族的生存、國(guó)家的復(fù)興”[4]196,如何認(rèn)識(shí)民族文化與民族存亡關(guān)系的重要性成為人們關(guān)注的焦點(diǎn)。此時(shí)的文化討論已經(jīng)告別了全盤西化與文化復(fù)古的極端,既不主張割裂傳統(tǒng),也不主張盲目學(xué)習(xí)西方,而是開(kāi)始采用一種“世界的眼光”來(lái)重新審視中國(guó)的固有文明,重新思考中國(guó)新文化的更生,這實(shí)際上體現(xiàn)出五四以來(lái)思想界對(duì)于古今東西文化的價(jià)值判斷與取向進(jìn)入了一個(gè)新的方向。此時(shí)的知識(shí)分子基于時(shí)代的考量開(kāi)始重新審視民族文化與民族復(fù)興的關(guān)系,是在繼承前人基礎(chǔ)上的一種歷史進(jìn)步,在關(guān)注文化的時(shí)代性與變革性的同時(shí),強(qiáng)調(diào)文化的民族性與獨(dú)立性。
二、以中國(guó)為本位還是以中國(guó)文化為本位
30年代的中國(guó)本位文化討論中,持批評(píng)態(tài)度的人們大多將十教授提出的“中國(guó)本位”等同于“堅(jiān)守中國(guó)固有文化”而大加批判,但仔細(xì)研究《宣言》,十教授強(qiáng)調(diào)的是“中國(guó)本位”,而并非“中國(guó)文化本位”。何為“中國(guó)本位”?《宣言》提出,即“此時(shí)此地的需要”[3]6。這里其實(shí)體現(xiàn)了一種不同以往的文化訴求,那就是建設(shè)符合中國(guó)當(dāng)前需要與民眾當(dāng)前需求的民族新文化。當(dāng)然,這種對(duì)“中國(guó)本位”的解釋不甚明確,為了回應(yīng)當(dāng)時(shí)的批評(píng)與質(zhì)疑,十教授不久后又聯(lián)合發(fā)表了一篇《我們的總答復(fù)》,此文將“中國(guó)本位”具體概括為,“充實(shí)人們的生活,發(fā)展國(guó)民的生計(jì),爭(zhēng)取民族的生存。”[5]183這一解釋仍稍顯泛泛而不夠具體。于是知識(shí)精英們紛紛提出自己對(duì)于“中國(guó)本位”這一概念的基本思考,不但豐富了“中國(guó)本位”的含義,同時(shí)也啟發(fā)了關(guān)于中國(guó)文化走向的新思路。吳忠亞認(rèn)為,我們要建設(shè)新的文化少不得要實(shí)行西化,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如何在西化中保持“中國(guó)本位”,他提出一個(gè)“民族自覺(jué)心”的問(wèn)題,就是在“歐化之先,我們必須要經(jīng)過(guò)理智的判斷,自主的選擇,真正是以滿足我們需要的態(tài)度去采取人家的長(zhǎng)處”,“有了這種民族自覺(jué)心,我們?cè)谀7氯思业奈幕臅r(shí)候,總不至忘卻我們是一個(gè)獨(dú)立的民族”[5]95。劉敖是系統(tǒng)分析了“本位” “中國(guó)本位” “中國(guó)本位意識(shí)” “中國(guó)本位文化”幾個(gè)概念,認(rèn)為做好“認(rèn)識(shí)自己的工作”(即檢討本民族固有文化的優(yōu)缺點(diǎn)及特質(zhì))、“認(rèn)識(shí)他人的工作”(即探索歐美各國(guó)實(shí)情及文化本質(zhì))、“比較認(rèn)識(shí)的工作”(即衡量各民族文化盛衰興亡的因果法則及中華民族文化的生存能力),樹(shù)立獨(dú)立自強(qiáng)的“中國(guó)本位文化意識(shí)”,并踏實(shí)做好教育、出版等文化工作,才能取得本位文化建設(shè)的實(shí)績(jī)。這些觀點(diǎn)表現(xiàn)出知識(shí)分子開(kāi)始跳出華夏中心論、西方中心論以及“中體西用”論的文化觀,以一種宏大的視野來(lái)審視中國(guó)文化在世界歷史文化長(zhǎng)河中的處境與地位,既強(qiáng)調(diào)文化發(fā)展的創(chuàng)新性與時(shí)代性,又兼顧文化發(fā)展的繼承性、民族性與獨(dú)立性,此時(shí)的認(rèn)識(shí)雖沒(méi)有科學(xué)理論支持,但已經(jīng)超越了之前的西化論、折中論、調(diào)和輪、化和輪。
“中國(guó)本位”的提出,實(shí)際上對(duì)于中國(guó)文化建設(shè)提出了一個(gè)新的命題,那就是對(duì)于古今東西文化判斷選擇的價(jià)值標(biāo)準(zhǔn)到底是什么?有人注意到中國(guó)與歐洲美洲國(guó)家不同,因而其他國(guó)家的文化未必適合中國(guó),同樣中國(guó)也不是16世紀(jì)、18世紀(jì)的中國(guó),因而我們過(guò)去優(yōu)美的文化也未必適合現(xiàn)代的中國(guó),建設(shè)中國(guó)文化要把握住‘時(shí)間和‘空間的重心,以此為根據(jù)來(lái)提出中國(guó)文化建設(shè)需要的內(nèi)容。這實(shí)際上體現(xiàn)了知識(shí)分子們對(duì)于文化選擇的一種新嘗試,不以過(guò)去的輝煌或現(xiàn)在的成就作為文化優(yōu)劣的標(biāo)準(zhǔn)和文化判斷選擇的依據(jù),而是根據(jù)中國(guó)現(xiàn)實(shí)國(guó)情與需要來(lái)繼承和揚(yáng)棄傳統(tǒng)文化、選擇和吸收外來(lái)文化。這種新型民族文化觀對(duì)于近代以來(lái)中國(guó)文化轉(zhuǎn)型的道路產(chǎn)生了深刻的影響。
三、開(kāi)拓近代文化轉(zhuǎn)型的新“視界”
20世紀(jì)30年代的中國(guó)本位文化討論中不乏具有學(xué)術(shù)價(jià)值的新觀點(diǎn)、新思考,體現(xiàn)知識(shí)分子對(duì)文化問(wèn)題的思考目光更遠(yuǎn)、眼界更寬,不僅開(kāi)拓了人們的文化“視界”,更為近代文化轉(zhuǎn)型提供了許多重要的思想資源。
其一,唯物史觀的運(yùn)用。作為馬克思主義代表的中國(guó)共產(chǎn)黨受制于緊迫的政治形勢(shì)并沒(méi)有直接參加30年代文化討論,但討論中仍可見(jiàn)到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與辯證法的身影。比如,李立中以經(jīng)濟(jì)基礎(chǔ)與上層建筑的關(guān)系為切入點(diǎn),對(duì)于文化的本質(zhì)、中國(guó)社會(huì)盛行的各種文化思潮、中國(guó)究竟需要什么樣的文化等問(wèn)題做了詳盡闡述,他指出,“某某歷史階段的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建立或滅亡,則與它適應(yīng)的文化,抑或速或緩隨之產(chǎn)生或消滅”,在分析批判中國(guó)社會(huì)流行的復(fù)古文化、基督教文化、啟蒙文化與資本主義文化思潮以后,他認(rèn)為本位文化宣言“正是辯證法認(rèn)識(shí)論的展開(kāi)”,因?yàn)椤爸袊?guó)是世界的一環(huán),所以應(yīng)該而且必須攝取現(xiàn)代文化,中國(guó)自有其特殊性,所以對(duì)于固有文化亦應(yīng)該予以批判的保存和揚(yáng)棄”,所以,中國(guó)的文化建設(shè)“必須要把握住文化與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的統(tǒng)一性。這是主要的條件。其次,文化的實(shí)踐性、空間性、連續(xù)性、民族性,這些次要的條件,亦不能忽略,必須予以嚴(yán)密的注意”[3]102-103。李建芳援引亞當(dāng)·斯密、馬克思、列寧等理論介紹資本主義產(chǎn)生發(fā)展過(guò)程對(duì)資本主義文化的影響,認(rèn)為歐洲文化的發(fā)展完全是按著辯證法和唯物史觀公式進(jìn)行,他認(rèn)為中國(guó)從唐宋以后就具備發(fā)展資本主義的條件,但是由于中國(guó)資本主義的發(fā)展缺乏強(qiáng)大的國(guó)際通商的刺激,而且發(fā)展過(guò)程極其緩慢,并不像英國(guó)法國(guó)那樣激烈迅速,因而“中國(guó)資本主義的發(fā)展沒(méi)有促成中產(chǎn)階級(jí)的文化革命和政治革命”,反而使“中產(chǎn)階級(jí)地主化”,導(dǎo)致“秦后中國(guó)思想文化發(fā)展走上保守和調(diào)和之道”[1]308-309。這里面關(guān)于中國(guó)資本主義發(fā)展的觀點(diǎn)雖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是從資本主義產(chǎn)生方式以及經(jīng)濟(jì)與社會(huì)結(jié)構(gòu)的角度觀察文化問(wèn)題,卻為人們提供了一種全新的理論角度。
其二,對(duì)于中國(guó)文化建設(shè)方向與性質(zhì)的分析。隨著討論的深入,人們開(kāi)始關(guān)注中國(guó)文化建設(shè)的方向是資本主義文化還是社會(huì)主義文化,并提出許多可資借鑒的觀點(diǎn)。李立中認(rèn)為中國(guó)與日本不同,中國(guó)不可能實(shí)現(xiàn)向資本主義社會(huì)的順利轉(zhuǎn)型。中國(guó)現(xiàn)在只是“變質(zhì)的初期資本主義社會(huì)”,而且“中國(guó)的資本主義關(guān)系……為金融資本主義所桎梏,不能更進(jìn)而得到絕對(duì)的發(fā)展……中國(guó)民族工業(yè)不能絕對(duì)發(fā)展,則中國(guó)即不能達(dá)到資本主義社會(huì)的可能……中國(guó)既然不能進(jìn)展到資本主義社會(huì),中國(guó)自亦不能有建設(shè)資本主義文化的可能”,那么中國(guó)文化建設(shè)的任務(wù)應(yīng)當(dāng)是“在高形態(tài)社會(huì)(社會(huì)主義社會(huì))的飛躍到來(lái)之前,做積極的準(zhǔn)備”[3]103。張岱年認(rèn)為,以中國(guó)的自身?xiàng)l件及所處的世界環(huán)境,中國(guó)不大可能完成西方先資本主義化再社會(huì)主義化的全過(guò)程,當(dāng)下的中國(guó)只能先盡量努力達(dá)到西方標(biāo)準(zhǔn)的“工業(yè)化”與“科學(xué)化”,從而為將來(lái)“轉(zhuǎn)入社會(huì)主義文化作準(zhǔn)備”,而不一定要執(zhí)著于資本主義[6]。同時(shí),張岱年還概括了未來(lái)中國(guó)新文化建設(shè)的三項(xiàng)主要工作,即文化整理及批判工作、學(xué)術(shù)創(chuàng)建工作、普及的文化革命工作[6]。可以說(shuō),這些思考也為后來(lái)中國(guó)共產(chǎn)黨形成科學(xué)的、民族的、大眾的新民主主義文化觀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啟發(fā)。
其三,關(guān)于文化創(chuàng)新與文化現(xiàn)代化的新思考。20世紀(jì)30年代的文化大討論中,如何看待西方文化與傳統(tǒng)文化,如何處理西方文化與傳統(tǒng)文化的交流、融合、改造等問(wèn)題,人們觀點(diǎn)不一、爭(zhēng)論激烈,雖然人們提出的文化自救的方式不盡相同,但是文化自救的最終目標(biāo)卻非常一致,那就是實(shí)現(xiàn)中華民族的文化創(chuàng)新與再生。人們將目光投向“現(xiàn)代化”以跳出“西化”的桎梏,不僅思考文化創(chuàng)新問(wèn)題,更討論中國(guó)現(xiàn)代化問(wèn)題,此時(shí)知識(shí)界的想法在廣度和深度上超越了之前的文化論爭(zhēng),而且,對(duì)于實(shí)現(xiàn)文化創(chuàng)新的手段與方法,也提出許多新的觀點(diǎn)與思路。西化派的嚴(yán)既澄就主張可以放棄“西化”的提法而代之以“現(xiàn)代化”,同時(shí)以“盡量”代替“全盤”的表述[5]200,“盡量現(xiàn)代化”的提出表明西化派更趨理性的認(rèn)識(shí),即從制度、方法等“現(xiàn)代化”因素入手,通過(guò)東西文化的交融匯通,實(shí)現(xiàn)中華民族固有文化的更新與再生。張熙若則更深入地闡述現(xiàn)代化與西化的區(qū)別,他認(rèn)為“西化”基本就是簡(jiǎn)單的抄襲模仿,而現(xiàn)代化則是將西方特有而中國(guó)沒(méi)有的東西,以及中國(guó)所獨(dú)有而西方所無(wú)的東西,利用我們現(xiàn)有的認(rèn)知、經(jīng)驗(yàn),加以融合創(chuàng)新,使之對(duì)于當(dāng)前的中國(guó)更“合理化”與“適用化”,總之,“現(xiàn)代化可以包括西化,西化不能包括現(xiàn)代化”[5]255-256。以上可以看出,30年代知識(shí)精英的文化觀念較之20年代進(jìn)步的地方就是形成了更為開(kāi)闊的文化視野,不僅強(qiáng)調(diào)文化的中西融合,更強(qiáng)調(diào)從中國(guó)政治、經(jīng)濟(jì)、社會(huì)條件出發(fā),以適應(yīng)中國(guó)社會(huì)發(fā)展需要為核心,強(qiáng)調(diào)通過(guò)文化的再生與創(chuàng)新,增強(qiáng)文化自信,完成文化自新,加速整個(gè)中華民族的現(xiàn)代化進(jìn)程,從而實(shí)現(xiàn)整個(gè)中華民族的復(fù)興與崛起。
參考文獻(xiàn):
[1]馬芳若.中國(guó)文化建設(shè)討論集:下編[M].上海:經(jīng)緯書局,1936.
[2]陳獨(dú)秀.今日中國(guó)之政治問(wèn)題[J].新青年,1918,5(1).
[4]鄭振鐸.中國(guó)本位文化建設(shè)宣言各方輿論之反響·鄭振鐸之意見(jiàn)[J].文化建設(shè),1935(5).
[5]馬芳若.中國(guó)文化建設(shè)討論集.中編[M].上海:經(jīng)緯書局,1936.
[6]張岱年.關(guān)于中國(guó)本位的文化建設(shè)[J].國(guó)聞周報(bào),1935:12(10).
[7]梁?jiǎn)⒊?梁?jiǎn)⒊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