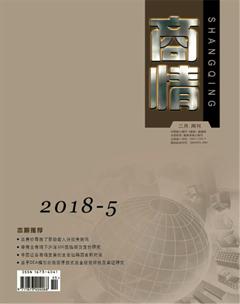建筑行業農民工社會排斥研究
朱潔瓊 李愛芹

[摘要]農民工社會排斥現象是個體排斥現象的整體社會表現,對個體而言,形成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而建筑行業農民工,由于數量大,流動性強,最具有代表性,他們在融入城市過程中受到的社會排斥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行業特殊性。研究發現建筑行業農民工主要受到勞動力市場、身份、消費和政治四個方面的社會排斥,這些社會排斥有些是環境被動施加的,有些是農民工主動施加的,文章引入“被動排斥”與“主動排斥”的概念,用以分析建筑行業農民工現有的社會排斥現象。在改善社會排斥的對策上,建筑行業農民工屬于社交弱勢群體,從短期可實施性的角度,應該更多的采取易于接受的軟手段。
[關鍵詞]建筑行業 農民工 社會排斥 被動排斥 主動排斥
一、前言
農民工是一個龐大的社會群體,他們一只腳踏入城市的大門,另一只腳還留在農村,特殊的身份使他們成為城市的“邊緣人”。他們在經濟、政治、文化、身份等方面受到城市方面的排斥,在形成社會排斥現象的眾多原因中,有一類原因,是農民工群體以外的客觀環境施加的,這類排斥主要受外部客觀環境影響,農民工單方面的作為很難起到扭轉作用,屬于“被動排斥”的范疇,具體指:由于政策法規、工作環境、城市風情等外部因素導致農民工被排斥在城市經濟、政治、文化等各項活動之外的社會現象。除了外部因素以外,農民工自身的自我排斥,例如自我認知、生活習慣等,也會成為阻礙農民工融入城市的重要原因,屬于“主動排斥”的范疇,具體指:由于身份特質、教育水平、心理活動等內部因素導致的農民工主動排斥融入城市經濟、政治、文化等各項活動的社會現象。農民工群體中存在著“被動排斥”與“主動排斥”并存的“雙重排斥”特征
二、建筑行業農民工面臨的多維社會排斥
(一)勞動力市場排斥
在勞動力市場方面,美國新功能主義社會學家皮奧里認為在勞動力市場中存在著兩種相互隔絕的勞動力市場,即第一勞動力市場和第二勞動力市場,其中,第一勞動力市場收入高、環境好,第二勞動力市場收入低、工作環境差。在建筑行業里,第一勞動力市場涉及的崗位主要為技術員及以上崗位,例如監理員、預算員等,這類崗位人員從事體力勞動較少,從業人員主要為受過高等教育的專業人員;第二勞動力市場涉及的崗位主要為施工員及以下崗位,例如砌筑工、鋼筋工等,這類崗位人員大多要從事體力勞動,農民工較為集中。而處在第二勞動市場的農民工要想進入第一勞動力市場是很難的,限于身份問題,即便農民工達到了第一勞動市場所需的技術水平,具備了勝任第一勞動力市場工作的能力,也未必能進入該市場工作。
(二)身份排斥
農民工群體普遍受到城市居民的偏見和歧視,“農村人”和“城里人”代表的不僅僅是地域上的差異,在現實中更多的表達一種層次上的差異。首先,建筑業農民的露天的工作環境要惡劣得多,往往給人一種臟、亂、差的感覺視覺反饋(如圖1),視覺反饋會誘發心理上的反饋,而這種心理上的反饋往往是消極和敵對的。
值得注意的是,外界給的身份排斥是一種“被動排斥”,短時間內很難改觀。而這種長期的“被動排斥”會引發農民工的“主動排斥”,當農民工長期處在周圍人有色眼鏡下的時候,其心理狀態也會產生變化,結果往往有兩個,一是消極社交,二是行為反抗(如圖1)。所謂消極社交,即農民工在社會排斥下形成的保守、被動、消極的社交行為。而行為反抗指的是,農民工在長期受到身份排斥的情況下,形成的逆反行為,輕者可能違反日常行為準則,重者可能引發偷竊、搶劫能違法行為。
(三)消費排斥
建筑行業農民工消費受限主要來自于兩方面,一是工資水平和城市的整體消費水平不協調,二是消費觀念,前者屬于“被動排斥”,后者屬于“主動排斥”。不同城市的發展水平不同,導致建筑行業農民工平均工資也存在較大差異,在發展水平不高的城市,建筑行業農民工收入偏低,限制了除生活必須品消費外的其他消費,在一些發展水平較高的城市,雖然平均工資可以達到5000元以上,但城市消費水平高,農民工為了節省開支,多數吃住在工地,消費水平和生活質量并沒有因為高收入而得到提高。此外,農村傳統消費觀念的影響也是根深蒂固的,多數建筑行業的農民工將自己的工作定位為“在城市干幾年體力活,多存點錢給孩子上學,以后回去也好養老”,傳統的農村消費觀念認為,在城市工作的目的是為了把錢存下來,即便是消費也是以后回到農村消費,而不是當下在城市消費。
(四)政治排斥
農民工群體長期游離于政治生活之外,實際上處于政治排斥狀態之中。對于建筑行業農民工首當其沖的是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得不到保障。一項2013年在哈爾濱、上海、珠海三地進行的調查顯示,76.7%的農民工未參加過村名委員會選舉,83.5%的農民工未參加過目前工作所在地的人大代表選舉活動,80.3%的農民工未參加過自己戶籍所在地的人大代表選舉活動。而在社區民主決策、管理和監督上,建筑行業農民工表現出了極度匱乏的狀態,尤其是底層的建筑工人,對“社區'這個詞缺乏基本的概念理念,更無從談起參與社區的政治活動,這種現象的產生與建筑工人的工作環境密切相關。首先,建筑工人流動性較強,工人要隨著工地的移動而移動,尤其在短周期工地,工人很難有足夠的時間融入社區生活;其次,建筑業農民工多數吃住在工地,限制了其日常活動范圍,農民工缺乏與外界溝通的渠道,相對封閉的工作環境使建筑工人沒有參與社區政治的意識。另外,即便是在工地內部,農民工的政治權利也無法得到保障,在工地的一些決策會議上,雖然我們也能看到農民工代表的身影,但形式上的一個兩個人根本代表不了農民工群體的政治訴求,事實也一次次證明,農民工的意見在政治決策和實施上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
三、緩解建筑行業農民工社會排斥的對策
建筑行業農民工受到的社會排斥有些屬于“被動排斥”,有些屬于“主動排斥”,相應的緩解對策有的可以立即投入實施,有的則需要相當長的時間,例如上述的城鄉二元分割制度,從1958實施至今,已經成為目前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一個嚴重障礙,這似乎已經成為一種共識,但我們必須認識到改革的長期性、艱巨性和復雜性。實施上,從農村進入城市的建筑工人屬于社交弱勢群體,在社會排斥的改善上,應該更多的采取易于接受的軟手段,從可實施性的角度,應該著力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一)引導社會輿論,傳遞正能量
社會輿論的力量是巨大的,尤其在新興媒體時代下,信息傳播速度快,覆蓋范圍廣,在輿論的引導上應該多管齊下,第一,增加建筑行業農民工的曝光量,全面展示一線建筑農民工的真實生活,引起全社會對建筑農民工的關注,尤其大力宣傳建筑農民工群體中的好人好事,樹立農民工踏實、吃苦、勤勞的形象,向社會傳遞正能量,改變市民對建筑農民工臟、亂、差的印象;第二,對在校學生感恩教育,正是由于廣大建筑農民工的辛苦勞動,才有了城市的繁榮,讓學生從小就對建筑業農民工及其他類似艱苦行業工人充滿敬意;第三,樹立平等的職業觀,一方面是引導市民,宣揚職業無貴賤,每一種職業都值得尊敬的思想,另一方面更要引導建筑業農民工,讓他們認識到自己工作的價值,摒棄低人一等的認知;第四,對消費場所員工宣傳顧客平等的理念,即便是對待穿著并不光鮮亮麗的客人,也要賓至如歸,減輕農民工的消極社交心理。
(二)加強建筑業農民工培訓
通過教育和培訓,提高建筑業農民城市的適應能力。首先,在培訓主體上,應該是多維度的,班組、建筑企業、社區、政府都應該發起定期和不定期的培訓活動,并通過措旖鼓勵農民工參加,例如培訓時間計算工時,甚至給予額外的工資獎勵等等;其次,在培訓對象上,越接近底層的建筑農民工越容易受到社會排斥,因此就減少社會排斥問題來說,培訓對象應該向底層工人傾斜;再次,在培訓內容上,應該以技能培訓和社交培訓為主,技能培訓重點在于基本文化知識、職業技術、市場經濟知識等,以提高農民工的教育水平,增強其市場競爭能力,社交培訓重點在于文化引導,增強農民工文化適應能力,幫助他們突破同質成員交往圈,打破“主動排斥”帶來的消極社交行為。
(三)繁榮建筑工地的文化生活
多數建筑行業農民工除了工作在工地外,吃住也在工地,建筑工地已經成為他們的主要活動范圍,在工地內開展文化活動,有利于提高活動的參與度,并能使農民工放下戒備,全身心地投入文化活動中。文化活動的投入應該從動態和靜態兩方面入手,對于動態文化建設,可以考慮建立文化驛站,增設健身房、工地影院、舞蹈室等。農民工在文化驛站學習的技能,又可以用于工地集會表演,例如充分利用舞蹈教室進行舞蹈隊排練,訓練成果用于文藝表演,促成良性循環,帶動建筑工地文化活動的大繁榮。而靜態文化建設,可以考慮建設工地文化宣傳墻、增設圖書室、電子閱覽室,提高建筑業農民工的文化水平,豐富文化生活。
(四)建立農民工基層組織,完善信息反饋機制
建筑業農民工受到社會排斥,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在整個社會中處于一種無權狀態,他們缺少表達和追求自身利益的制度化途徑。而單個農民工無法產生強有力的申訴力量,而工會有時難以兼顧到每個個體,因此除了工會外,鼓勵農民工在法律范圍內建立基層組織,代表農民工利益,依規反應農民的基本訴求,同時管理層應完善信息反饋機制,讓工人投訴“有門”,例如設立專門投訴受理辦公室和調解員,開通企業農民工勞動保障專線等。很多農民工事件,追其源頭,多由班組、隊伍乃至施工企業中個別責任人在處理勞資糾紛過程中,推卸責任,不敢擔當,不愿擔當,致使工人感到被欺瞞和壓制,產生敵對甚至仇視情緒。建立農民工基層組織,完善信息反饋機制對于提高農民工的話語權,改善社會排斥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