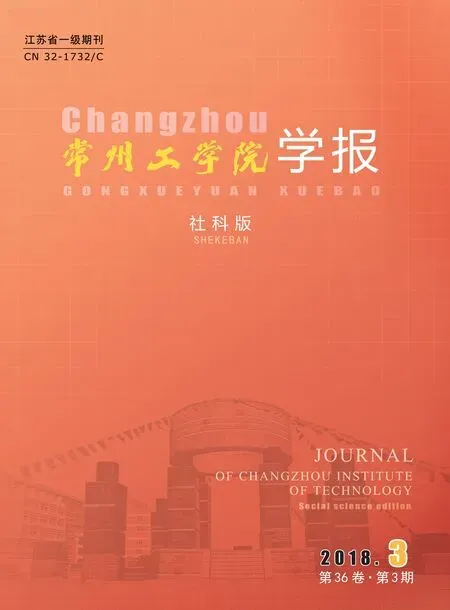大學(xué)生網(wǎng)絡(luò)社交的族群化探析
夏天靜
(1.常州工學(xué)院馬克思主義學(xué)院,江蘇 常州 213032;2.南京師范大學(xué)馬克思主義學(xué)院,江蘇 南京 210097)
在人類社會的發(fā)展演變過程中,個體的往來聯(lián)系交織出各種社會關(guān)系,在社會關(guān)系中密切互動的人們則在產(chǎn)生共同利益和集體意識的基礎(chǔ)上結(jié)成社會群體(social group)。社會群體不是任意的一個人群,而是處在社會關(guān)系中的一群人的集合體。與其他人群相比,社會群體具有以下特征:第一,有明確的成員關(guān)系;第二,有持續(xù)的相互交往;第三,有一致的群體意識和規(guī)范;第四,有一定的分工協(xié)作;第五,有一致行動的能力[1]。社會群體是研究社會發(fā)展現(xiàn)象的基本單元,依據(jù)不同的標(biāo)準(zhǔn)可以有不同的群體類別。西方學(xué)者在描述一國中具有自身文化特質(zhì)的小規(guī)模社會群體時,提出了“族群”(ethnic group)這一概念。隨著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shù)的發(fā)展,“族群”概念已經(jīng)被運用到網(wǎng)絡(luò)空間的社群研究中,而大學(xué)生的網(wǎng)絡(luò)社交也出現(xiàn)了族群化的特征。
一、社會學(xué)中的“族群”概念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族群”是人類社會學(xué)進行社會群體研究的一個重要概念,于20世紀(jì)60年代傳入我國。如果說階級是一種政治經(jīng)濟向度的分群方式,那么,族群則是傾向于文化向度的分群方式。
“族群”概念的提出,源于西方學(xué)者對近代國家移民群體的社會研究分析。1962年,美國學(xué)者內(nèi)森·格萊澤(Nathan Glazer)和丹尼爾·帕特里克·莫伊尼漢(Daniel Patrick Moynihan)在研究紐約移民集團的歸屬感時,使用“族群性”(ethni-
city)一詞來指稱這一新群體的“族裔集體的性質(zhì)與特點”[2],表現(xiàn)為具有種族意識,有同樣的血緣和文化傳統(tǒng),但卻沒有融入美國社會。在這之后,學(xué)者們使用“族群”來稱呼那些散居于一國,來自不同國家,具有不同文化、語言和宗教背景的移民人群。
隨著“族群”概念的廣泛使用,對于其理解,西方學(xué)術(shù)界存在著不同的理論傳統(tǒng),至今形成繁簡不一的20余種定義。“族群”定義的流變發(fā)展經(jīng)過了從注重群體的客觀特征到注重群體的主觀特征再到兩者特征的綜合的過程[3]9。
(一)客觀特征性定義
族群是指在一個較大的文化和社會體系中具有自身文化特質(zhì)的一種群體,其中最顯著的特質(zhì)就是這一群體的宗教的、語言的特征,以及其成員或祖先所具有的體質(zhì)的、民族的、地理的起源[4]14。客觀性定義是從群體的內(nèi)部共性出發(fā)的,既包括生物學(xué)意義上的特征,也包括社會學(xué)意義上的客觀特征,強調(diào)群體在語言、種族和文化等方面的不同。
(二)主觀特征性定義
美國社會學(xué)家韋伯(Max Weber)的“族群”定義對我國學(xué)術(shù)界影響較大,他用群體成員擁有的共同的“主觀信仰”界定了非血緣關(guān)系中的“族群”,強調(diào)族群不同于血緣親屬群體[4]14。韋伯之后的挪威社會學(xué)家巴斯(Frederick Barth),進一步從邊界的新視角說明了“族群”的主觀性。巴斯的邊界論從“群體的排他性和歸屬性”[3]9來界定族群,他認(rèn)為:“族群”是由其本身組成成員認(rèn)定的范疇,形成族群最主要是其“邊界”,而非語言、文化、血緣等“內(nèi)涵”;一個族群的邊界,不一定是地理的邊界,而主要是社會性的邊界[5]。
(三)綜合性定義
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礎(chǔ)上,《哈佛美國族群百科全書》中給出了綜合性的定義:族群是一個有一定規(guī)模的群體,意識到自己或被意識到其與周圍不同,并具有一定的特征以與其他族群相區(qū)別[4]14。這些特征超越親屬、鄰里和社區(qū)的聯(lián)系,既包括了共同的地域來源、遷移歷史和種族特征,也包括了共同的宗教信仰、語言、文字、音樂、習(xí)俗、飲食等文化傳統(tǒng)。在這一定義中,在族群的自身特征之外,同樣非常強調(diào)族群內(nèi)部成員以歸屬感構(gòu)成的自我認(rèn)同和以排他性形成的社會外部認(rèn)同。
二、網(wǎng)絡(luò)族群的形成機制
互聯(lián)網(wǎng)產(chǎn)生之前,個體的社會交往受制于諸多因素,或因居住于一個地區(qū)而形成一個群體,或因相同的社會身份而形成一個群體,人們的社會交往也往往受到地域性的空間限制和身份性的階層限定。網(wǎng)絡(luò)技術(shù)的發(fā)展,使網(wǎng)民個體突破了固有生活工作的空間和階層,互聯(lián)網(wǎng)的開放特性使得個體在網(wǎng)絡(luò)平臺上可以充分交流并分類聚集起來,極大地促進了網(wǎng)絡(luò)族群的形成。
對族群概念的解讀可以幫助人們了解網(wǎng)絡(luò)族群的形成機制。網(wǎng)絡(luò)族群將網(wǎng)民個體組織成為群體,核心機制就是認(rèn)同和辨異,即網(wǎng)民個體對這一網(wǎng)絡(luò)族群身份的自我認(rèn)同以及族群之外的社會他人對這一網(wǎng)絡(luò)族群的外在認(rèn)定。族群概念中的客觀文化特征以及巴斯邊界論強調(diào)的歸屬性和排他性,同樣可以用于解讀網(wǎng)絡(luò)族群的形成過程。
首先,現(xiàn)實社會生活中的族群(下稱“社會族群”,與“網(wǎng)絡(luò)族群”相區(qū)別)內(nèi)部的客觀特征,在網(wǎng)絡(luò)族群成員身上更多地凸顯為社會學(xué)意義上的不同。網(wǎng)絡(luò)世界的虛擬性模糊了網(wǎng)民個體在生物學(xué)意義上的特征,網(wǎng)民不受自身年齡、性別,甚至職業(yè)等限制,僅僅憑借自由的表達進行自我標(biāo)簽,相互識別,同好相吸,從而篩選出網(wǎng)絡(luò)空間中與自身興趣或價值觀趨同的個體,聚集成族。這一過程正如黃少華在其研究中總結(jié)的“發(fā)布信息、表達自我、尋求互動、凝聚認(rèn)同”[6]。
其次,由網(wǎng)民的自我認(rèn)同聚集起來的網(wǎng)絡(luò)族群,在網(wǎng)絡(luò)空間不可避免地與其他網(wǎng)絡(luò)族群有著交往和接觸,相互交往中更顯現(xiàn)兩個族群的差異,接觸聯(lián)系中更強化族群的邊界。在這一過程中,族群成員會自然生成并逐漸增強對所屬網(wǎng)絡(luò)族群的歸屬感和對其他網(wǎng)絡(luò)族群的排他感,即巴斯提出的群體歸屬性和排他性。歸屬感和排他性共同形成并構(gòu)建起每一個網(wǎng)絡(luò)族群的邊界,劃分出了族群內(nèi)部的同類成員和外部的不同游客。
由是觀之,從社會族群到網(wǎng)絡(luò)族群,從現(xiàn)實世界到虛擬世界,族群的形成機制是共通的,均是由內(nèi)部成員的認(rèn)同和族群外部的辨異構(gòu)建起族群(包括網(wǎng)絡(luò)族群)的邊界。
三、大學(xué)生網(wǎng)絡(luò)交往的族群化
隨著智慧校園的建設(shè)和智能手機的普及,大學(xué)生的校園學(xué)習(xí)和生活已經(jīng)與網(wǎng)絡(luò)密不可分,線上線下的人際交往互相交疊,共同構(gòu)成了大學(xué)生豐富多彩的校園生活,而族群化也成為大學(xué)生網(wǎng)絡(luò)交往中已有并不斷強化的特征,與其他學(xué)生和職業(yè)群體相比,大學(xué)生的網(wǎng)絡(luò)族群交往也有其自身的特點。
(一)大學(xué)生網(wǎng)絡(luò)族群的類型
大學(xué)階段,絕大多數(shù)學(xué)生離開熟悉的家鄉(xiāng)入住集體宿舍,開始獨立生活,作為與家人朋友聯(lián)系的最主要工具——手機則幾乎是其入校必備用品之一。智能手機的普及使得大學(xué)生有可能全天候地關(guān)注網(wǎng)絡(luò)信息,參與網(wǎng)絡(luò)社交。相對于上班族,大學(xué)生的主要任務(wù)就是上課學(xué)習(xí),日常接觸的對象主要就是同學(xué)和老師,因此社會人際交往對象相對單純。相對于高中生,大學(xué)生雖然有就業(yè)壓力,但學(xué)業(yè)壓力大大減輕,有大量的自主支配時間,因此人際交往需求大大提升。
象牙塔中的半社會化生活,使得大學(xué)生關(guān)注的網(wǎng)絡(luò)族群主要有兩類。一類與其現(xiàn)實生活圈高度重合,主要是基于學(xué)生生活構(gòu)建的同學(xué)群。大學(xué)生的同學(xué)群往往是新生活與舊生活的交疊,既有家鄉(xiāng)的老同學(xué)群,又有大學(xué)學(xué)習(xí)生活圈中新結(jié)識的師生好友群。這一類族群中的成員往往是現(xiàn)實社會生活中的熟人,相互認(rèn)識和了解,更多是以QQ群、微信群等形式建立的網(wǎng)絡(luò)族群,建群的目的主要是為了方便聯(lián)系、交流和分享信息。這一類網(wǎng)絡(luò)族群的認(rèn)同基礎(chǔ)是同窗情誼。
大學(xué)生熱衷加入的另一類網(wǎng)絡(luò)族群屬于趣緣型,其成員有同校、同城的熟人,更多的則是互聯(lián)網(wǎng)上未曾謀面的網(wǎng)友。熟人網(wǎng)絡(luò)族群往往是在大學(xué)生社團建立之后的衍生族群,主要目的是利用網(wǎng)絡(luò)進行超時空的信息交流和分享,網(wǎng)絡(luò)之外的線下社會族群活動更為豐富。陌生人為主的網(wǎng)絡(luò)族群,則完全是基于網(wǎng)絡(luò)的篩選和聚合作用結(jié)成的同道中人。大學(xué)階段的生活選擇更獨立自由,家人和師長也較少干預(yù)其課余生活,加上全覆蓋的校園網(wǎng)絡(luò)和普及的智能手機,大學(xué)生校園之外的網(wǎng)絡(luò)社交,主要是通過手機上網(wǎng)、基于各自興趣愛好結(jié)成的趣緣群體。在同城條件下,網(wǎng)絡(luò)族群的交往往往是線上交流、線下活動并行發(fā)展。
(二)大學(xué)生網(wǎng)絡(luò)交往的族群化特征
1.大學(xué)生是網(wǎng)絡(luò)族群化交往的“新移民”
“族群”最初的含義就是指稱外來居住于一國的移民群體,而來自中國各地的大學(xué)生與傳統(tǒng)的移民群體非常相似。一方面,大學(xué)生步入新校園、新班級和新宿舍,從初識到逐漸相互熟悉和適應(yīng),自然而然地結(jié)成大學(xué)新生活的班級群(既是現(xiàn)實的班集體,又是網(wǎng)絡(luò)族群),每一位大學(xué)新生都以院系為標(biāo)識找到在校園中的身份歸屬,自然劃定了以班級為基準(zhǔn)的族群邊界;另一方面,每一位大學(xué)生都有之前的學(xué)習(xí)生活經(jīng)歷,有著依然聯(lián)系甚至交流頻繁的初高中同學(xué)群,這類網(wǎng)絡(luò)族群因家鄉(xiāng)共同的語言(方言)、飲食習(xí)慣、生活習(xí)俗和學(xué)習(xí)經(jīng)歷等形成共識,劃定族群邊界。身處族群中的成員,每一個人在其中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獲得歸屬感。
與傳統(tǒng)移民與移民國家之間的關(guān)系相似,去異地求學(xué),仿佛是將大學(xué)生從出生、成長的地區(qū)遷出,移居大學(xué)所在城市。校園新移民對于陌生環(huán)境的緊張感、無依感促使他們迅速認(rèn)識新同學(xué),融入新班級,建立起新的班級族群(既包括現(xiàn)實的班集體,又包括網(wǎng)絡(luò)族群),從而找到新的歸屬感;他們同時也依然與中學(xué)同學(xué)保持著聯(lián)系,主要在以網(wǎng)絡(luò)聯(lián)系起來的老同學(xué)群里尋找熟悉感,以緩解新生活的不適,進而分享新生活的點滴。
2.大學(xué)生的趣緣型網(wǎng)絡(luò)族群交往
與其他學(xué)生群體、職業(yè)群體相比,趣緣型網(wǎng)絡(luò)族群對大學(xué)生的吸引力更大,同時,大學(xué)生投入在趣緣型網(wǎng)絡(luò)族群中的熱情度也更高。相對充裕的時間、自由使用的手機、開放包容的校園、門類繁多的社團、豐富的網(wǎng)絡(luò)世界、年輕好奇的心……這一切都成為大學(xué)生一頭扎進趣緣型網(wǎng)絡(luò)族群的理由和條件。中學(xué)時代想玩而無暇玩的樂器、運動、舞蹈、游戲、技藝等,均成為大學(xué)生想嘗試的領(lǐng)域,太多大學(xué)生想?yún)⑴c其中。
對大學(xué)生有巨大吸引力的趣緣型網(wǎng)絡(luò)族群,同樣給大學(xué)生的校園生活帶來諸多變化。首先是大學(xué)生對趣緣型網(wǎng)絡(luò)族群交往投入的時間較多。大學(xué)生對手機即時信息大都會第一時間瀏覽和回應(yīng),其中當(dāng)然也包括大量的趣緣型網(wǎng)絡(luò)族群的信息。對于正沉迷其中的興趣,大學(xué)生的時間投入更是驚人,有的甚至?xí)奚邥r間和上課時間,這也正是某些興趣如手游給大學(xué)生活帶來的負面效應(yīng)。其次是趣緣型網(wǎng)絡(luò)族群中交流的信息對大學(xué)生知識體系和價值觀影響很大。興趣是最好的老師,基于興趣,趣緣型網(wǎng)絡(luò)族群中交流的信息會為大學(xué)生迅速領(lǐng)會,牢牢記住,舉一反三,并身體力行,這類族群中的信息影響力是遠遠超過老師、家長等傳統(tǒng)權(quán)威的,其作用也是一把雙刃劍。最后是趣緣型網(wǎng)絡(luò)族群中的交往給大學(xué)生帶來的歸屬感,使得校園社團活動對大學(xué)生的吸引力受到挑戰(zhàn)。網(wǎng)絡(luò)族群的交往,因為有了網(wǎng)絡(luò)而無時不在、無處不在,幾乎所有的社會交往功能在虛擬的網(wǎng)絡(luò)世界通過技術(shù)性的手段和語言均能實現(xiàn),網(wǎng)絡(luò)媒介匿名隱身的特性更是現(xiàn)實社會族群無法比擬的。網(wǎng)絡(luò)族群的存在擠壓了校園社團對大學(xué)生的影響力,有些大學(xué)生沉溺于網(wǎng)絡(luò)族群而忽視現(xiàn)實社團,這相應(yīng)地影響了他們的社會交往。
(三)網(wǎng)絡(luò)族群交往對大學(xué)生社會化的影響
不可否認(rèn),網(wǎng)絡(luò)族群的交往占用了大學(xué)生相當(dāng)一部分傳統(tǒng)社交的時間和空間。網(wǎng)絡(luò)族群中的交往與社會群體中的交往一樣,給大學(xué)生的社會化帶來雙重影響,引導(dǎo)或誤導(dǎo)著大學(xué)生的社會化進程。
個體關(guān)于族群的意識和觀念并不是生物遺傳的結(jié)果,而是在后天生活環(huán)境中逐漸萌生、明晰、強化和發(fā)展起來的。網(wǎng)絡(luò)時代的后天環(huán)境,既包括了傳統(tǒng)的社會環(huán)境,也包括了虛擬的網(wǎng)絡(luò)環(huán)境。社會的族群意識和網(wǎng)絡(luò)的族群意識在本質(zhì)上是一樣的,都是大學(xué)生認(rèn)識世界、進入社會的過程中必須建立起來的重要社會意識。在與校園內(nèi)外人群的社會交往中,大學(xué)生會自然而然地根據(jù)具體環(huán)境、特定場景和感情利益關(guān)系的親疏遠近,在群內(nèi)親近成員的指導(dǎo)下,學(xué)習(xí)并接受“把生活周圍的社會成員劃分入不同性質(zhì)、不同層次的群組”這一觀念。同樣,在網(wǎng)絡(luò)族群的交流和交往中,族群成員也會自然而然地根據(jù)族群邊界確定社會關(guān)系親近的范圍:在這個族群邊界之內(nèi),熟人道德規(guī)范以及互惠關(guān)系得以通行;超出這個范圍,通行的則是另一套原則。大學(xué)生逐漸學(xué)會運用親近互惠的原則與同一族群成員進行親密無間的交流和交往,同時也會心有戒備地與族群之外的普通網(wǎng)友保持社會安全距離,從而形成族群內(nèi)外的網(wǎng)絡(luò)交往在交流語言、頻度、時長、關(guān)注程度上的差序格局。
網(wǎng)絡(luò)族群交往除能促進大學(xué)生正常社會性成長外,也會阻礙大學(xué)生的健康成長。網(wǎng)絡(luò)族群交往的負面影響在客觀方面,主要由網(wǎng)絡(luò)技術(shù)的匿名性、網(wǎng)絡(luò)族群中的不良信息傳播等導(dǎo)致;在主觀方面則是大學(xué)生個體對網(wǎng)絡(luò)交往虛擬特性的辨識、對網(wǎng)絡(luò)族群交往的控制能力等不足所致。在大學(xué)生社會族群和網(wǎng)絡(luò)族群的雙重交往中,既能看到網(wǎng)絡(luò)族群交往對其校園生活的良性促進,也常常能看到沉溺于網(wǎng)絡(luò)的負面事例出現(xiàn)。相較于現(xiàn)實生活中看得見摸得著的實體社交,網(wǎng)絡(luò)平臺上展開的虛擬社交對大學(xué)生網(wǎng)民提出了更高的自律要求,自律精神較差的大學(xué)生往往終日混跡于網(wǎng)群世界,生長出回避現(xiàn)實社會的“宅”性,以抗拒正常的社會化過程。大學(xué)生只有正確處理好網(wǎng)絡(luò)和現(xiàn)實群體交往的關(guān)系,學(xué)習(xí)并適應(yīng)社會交往的規(guī)范與原則,才能順利完成網(wǎng)絡(luò)時代的社會化成長。
綜上所述,網(wǎng)絡(luò)時代的發(fā)展,在現(xiàn)實的社會族群交往之外,也給大學(xué)生帶來了網(wǎng)絡(luò)族群的超時空交往機會。網(wǎng)絡(luò)族群的交往既是對現(xiàn)實社會交往的有益補充,提升了現(xiàn)實交往的密切度,共同推進了大學(xué)生的社會化過程,也因其交往的超時空性會帶來一定的負面效應(yīng),這需要大學(xué)生對網(wǎng)絡(luò)族群建立起恰當(dāng)?shù)慕煌^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