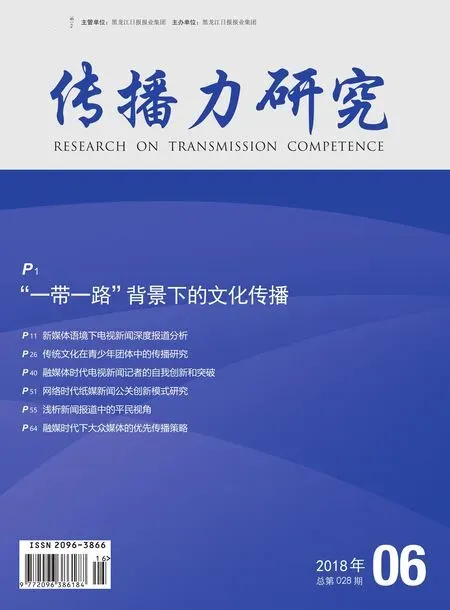后真相時代如何引導網絡輿論
趙彩雯 陜西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后真相”是英國《牛津詞典》選出的2016年度英文詞匯。其含義是:“訴諸情感及個人信念,較陳述客觀事實更能影響輿論的情況”[1],也就是說,對大眾意見的形成,客觀事實反而不及情緒感覺來的更有影響力。早在1992年,美籍塞爾維亞劇作家史蒂夫·特西奇在美國《國家》雜志上發表的一篇關于海灣戰爭的文章就曾使用過“后真相”一詞,并賦予其“情緒的影響力超過事實”的語義,在誕生20多年后才被《牛津詞典》評為年度詞匯,足以說明該詞所指的現象在今天的嚴重性[2]。過去“后真相”一詞不常出現,但2016年發生的英國脫歐、美國總統特朗普大選等一系列事件后,“后真相”又頻繁出現在我們的視野中,并影響著網絡輿論的發展走向。2017年9月在英國卡迪夫大學新聞媒體和文化學院舉行了第六屆“新聞業的未來”大會,這次大會的主題“新聞業的未來:后真相時代的新聞業”也與“后真相”有關,可見“后真相”一詞在近兩年來的影響力。
輿論引導工作是指新聞工作者通過選擇新聞事實,發揮傾向性的報道功能,對社會輿論進行導向和梳理,使其朝著健康有利的方向發展[4]。這是我國新聞媒介的一大重要職責,也是維護社會穩定的一大利器。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上也強調了輿論引導的重要性。以網絡為載體,及時、交互、關系賦權的新媒體環境下,社會傳播體系和傳播生態都發生了變革。受眾在傳統媒體公信力日趨消解的狀況下,難以以個人能力辨別觀點真假,往往順從于自身或社交媒體“小圈子”中的情緒、立場或刻板印象,從而做出輕率的情緒化判斷[3]。“情緒的影響力超過事實”的“后真相”時代,網絡輿論更是以“先入為主”的方式,在事實未清,真相未明的情況下,推動著事件的發展進程。可以說,新媒體為網絡輿論插上了翅膀,極大的滿足了公民的表達權和媒介接近權,信息也呈現出滾動化、裂變式的傳播。“后真相時代”,受情緒效應的驅使,網民更愿意選擇自己相信的“真相”,并以此來強化固有的觀點。由于我國網民數量多,媒介素養總體水平不高,網絡輿論形成中含有大多非理性因素,呈現出混雜、匿名、眾聲喧嘩的特點,再加之一些不良分子利用網絡輿論實現個人利益,使得網絡輿論引導工作迫在眉睫,而“后真相”時代的網絡輿論的群聚性、易爆性、情緒性等新特點也使傳統的輿論引導工作必須盡快變革,適應新環境。
一、新舊媒體聯動引導,及時占領輿論高地
新媒介技術的發展使得任何一個社會熱點事件都能腳踏移動智能設備的風火輪,借助4G網絡東風,得到及時快速的傳播,經過網民的轉發互動,意見和觀點的碰撞,快速形成輿論在網絡和現實生活中擴散傳播。新聞事件中的任何一個轉折點都可能成為網絡輿論爆發的導火索,引發一場輿論熱潮。互聯網語境下,輿論的復雜性和廣泛性需要新媒體和傳統媒體優勢互補,共同構建輿論溝通平臺。傳統媒體發揮其公信力、深度報道能力和平臺的聲譽傳播力,及時發聲,做好“首因效果”,占領輿論高地,同時提供對事件客觀全面的深度解讀,主動設置議程,避免網民被非理性的聲音引導,使網絡輿論走向偏激。新媒體也應發揮自身海量、廣泛、及時、互動等優勢,利用累積、共鳴、遍在等手段擴散主流聲音,形成輿論的良性互動機制。任何一個新聞事件在引爆網絡輿論之前,主流媒體就應該重視輿論的發展,及時發聲,若經過新媒體的滾動式、裂變式傳播,網絡輿論達到了最高點,質疑的聲音越來越多,會使輿論引導變得困難。在一些涉及法律的新聞事件中,媒體在報道中應多普及法律知識,用“專家+法律+事件”的報道模式,也要利用好官方微信、微博的傳播力,擴散官方的聲音,引導輿論發展。當下的互聯網時代,盡管人人都有發表觀點的權利和機會,但傳統媒體依舊占據主流媒體的主導地位,主流媒體不僅承擔著傳遞真實信息的職責,也肩負著引導輿論、教育公眾的責任,主流媒體有力的輿論引導必須是事實的呈現,保證信息的真實性,增強信息可信度。與此同時,要及時對事件進行正確的輿論引導,防止輿論撕裂。
二、創新輿論引導方式,涵化受眾主流價值觀
新媒體的發展使公民的表達權和媒介接近權得到了最大化的使用,用戶不再是“魔彈論”下的被動的信息接受者,選擇性接觸理解成為一大特點,要使網絡輿論朝著積極的方向發展,主流媒體應該改變過去傳統的教導式、說教式的輿論引導方式,配合互聯網思維,創新輿論引導的話語體系和變革呈現方式,利用網絡元素配以數據、算法、圖表、直播等新型手段,涵化受眾主流價值觀,讓公眾的認識、判斷和行為有共同的基準,為公眾的問題討論提供統一的價值框架。涵化受眾的主流價值觀,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不能只看當下事件的報道效果和輿論引導程度。新媒體環境下,信息的生產和傳播機制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受眾也從原來的被動接受信息學會了主動拉取信息。傳受角色的變化以及“后真相”時代“真相”和“謊言”之間的界限越來越模糊,使得受眾更能在重大事件中發揮輿論的助推器作用。輿論一旦出現,被推上風口浪尖扥話語攸關方,要及時澄清輿論中的不真實言論,更要放低姿態,利用社交媒體等新興渠道的便捷性,使用受眾喜聞樂見的形式、語言,有針對性地引導輿論。在與受眾的互動過程中不能使用情緒化、極端化的回應方式,以免導致“后真相”的再次傳播,應動之以理,用有說服力的證據和分析來說服公眾。
三、包容輿論自身發展,發揮對沖自凈機制
輿論有其自身的發展規律,過分的壓制會導致其惡性發展,刪帖、水軍等不當做法均會惡化網絡輿論。普通網民對熱點事件的圍觀,能形成群體壓力和輿論壓力,使得更多的人群聚圍觀,信息在傳播與交換中,會使公眾更加堅定自己已有的看法,任何有某種傾向的群體都不可避免地向著這個方面轉移。互聯網的匿名性使大家敢于表達自己的意見,敢于說出不同的聲音,借助網絡虛擬平臺,贊成和反對的觀點都能得到表達,針對同一社會事件,網民生活環境和個人經歷的不同,觀點各不相同,各種意見在相互交流和碰撞中,真相會逐漸清晰。2017年發生的“羅一笑事件”,也印證了這一點。從一開始的萬眾同情到新聞反轉后的千夫指責,微信朋友圈的大量轉發和微博熱搜上群體的參與,在事件爆發幾小時后,便被網友扒出事實真相,稱此事為生病女孩的父親羅爾的營銷炒作。“后真相”時代,自媒體中輿論的相互碰撞會使事件的真相逐漸清晰,因而也要給網絡輿論一定的自由發展空間,讓其發揮自身的自凈機制,不能過分壓制和管控,否則會產生“寒蟬效應”。
四、把握輿論引導時效度,建立廣泛的社會認同
我國主流媒體和政府組織在重大社會事件發生、發展的階段,有時會出現“缺位”和“失聲”現象,沒有起到對輿論的監測和預告作用。不要等到社會矛盾尖銳才去報道和管制,應第一時間利用互聯網強大的發聲和互動反饋功能,利用政務微博、智慧城市、在線答疑等手段,傳統媒體和新媒體共同建立話語平臺,直接對話減少中間信息損耗。同時對于事關民生的重大事件,第一時間公開已經不夠,必須把握輿論引導的時機,掌握分寸,增強透明度,設置指導性框架,把握主動話語權。能否把握好“度”,輕則影響輿論引導的社會效果,重則關系到的所控制社會的系統穩定。當前,從新聞輿論引導的許多案例中,我們可以發現輿論引導的社會效果并不總是按照傳播者所預想的那樣發展。
五、利用自媒體優勢,扶植已有意見領袖
自媒體不僅給公眾提供了自由參與的平臺,激活了個人機制,也打破了以往單一的線性傳播渠道,主流媒體應當充分利用自媒體大眾傳播加人際傳播的特點,在不同的傳播平臺上采取不同的傳播策略,全方位引導輿論,為受眾提供信息服務。設立公眾號,建立網絡答疑機制,同時采用新媒體技術,比如短視頻,交互式直播等方式加深用戶黏度,更進一步提高自身傳播力。網絡賦予每個人自由表達觀點的權利,但并非每個人表達的觀點都具有同樣的影響力,意見領袖往往依據巨大的粉絲量以及長期經營得到的公信力和傳播力,能形成強大的影響力,不僅能夠引發輿論,也能引導輿論走向。主流媒體不僅可以通過扶植已有的意見領袖,也可以利用已有的意見領袖傳遞自身觀點引導輿論。在網絡輿論的傳播中,自媒體人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一是這些人往往都有某一領域的專業知識,能夠從專業的視角對特定的現象和話題進行解讀;二是這些解讀往往都聚焦于社會上的一些熱點話題和熱門事件;三是自媒體人或自媒體中發布的信息均有很強的影響力,成為重要的輿論引導力量;四是這些自媒體人持續的信息發布行為不僅有助于自身品牌的塑造,而且信息的發布者也會獲得不俗的收入,同時也給這些平臺運營者提供大量的內容[5]。所以在網絡輿論的引導中學會利用自媒體的優勢和已有意見領袖的影響力是很重要的一環。
網絡輿論往往是官方的導盲犬,可以充分了解一定時間的民眾情緒,引導的好可以促進社會穩定和政府形象威信的建立,引導不好便會激化矛盾,對社會造成極大的消極影響。新媒體環境既給予了機會也給予了挑戰,如何利用好新技術適應新環境是當下輿論引導的重中之重,同時也要抓住“后真相”時代,受眾的心理特點,轉變引導方式。自黨的十八大以來,國家就十分重視網絡輿論引導工作,這不僅關乎國家意識形態的傳遞與維護,更是關乎網絡空間的建設和治理,只有正確的網絡輿論引導才能帶動網絡環境走向理性化和法制化。主流媒體在新的網絡空間背景下,必須積極轉型,做好網絡輿論的引導者、社會事件的闡釋者、公眾情緒的安撫者和社會爭議的平息者。同時也要把握網絡輿論引導工作的時效度,給予網絡輿論一定的自由發展空間是必不可少的。相信未來的網絡社會能走向哈貝馬斯筆下的“公共領域”。
[1]易艷剛.“后真相時代”新聞價值的標準之變——以“羅爾事件”為例[J].青年記者,2017(04).
[2]王悠然.警惕“后真相”時代的假消息[N].中國社會科學報,2017-01-06(03).
[3]胡泳.后真相與政治的未來[J].新聞與傳播研究,2017(04).
[4]傅雪琴.自媒體環境下傳統媒體如何做好輿論引導[J].中國廣播,2012(04).
[5]孫祥飛.新聞傳播學熱點專題80講[M].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16:2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