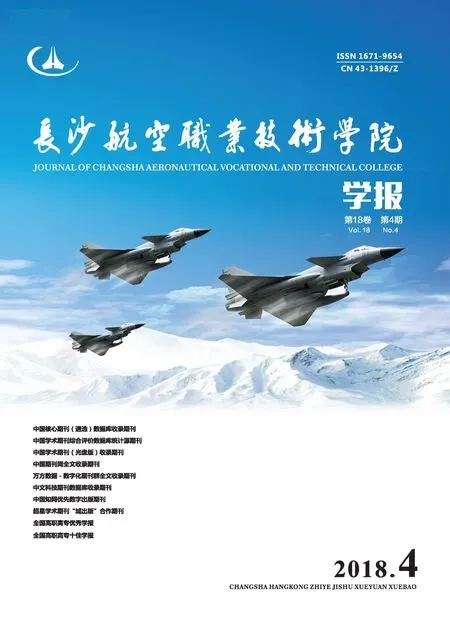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視閾下亞里士多德友愛觀審視
于阿專
(中共泰州市委黨校政法教研室,江蘇 泰州 225300)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當代中國精神的集中體現,凝結著全體人民共同的價值追求,不僅點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實質所在,更是對黨的十八大以來實踐經驗的高度總結。今年,中央印發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法治建設立法修法規劃》,要求在今后的法律法規體系建設中以鮮明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導向為引領,社會主義友善觀也由此煥發出了新時代特色。因此,我們重新審視亞里士多德的友愛觀,就意味著在對西方傳統文化揚棄的基礎上,用新理念塑造當前的友善核心價值觀,賦予其新的時代內容。
一、亞里士多德友愛觀的背景分析
我們在新時代重讀亞里士多德的友愛觀并加以探討,粗略地考察當時古希臘的時代環境以及亞氏友愛觀的理論淵源顯得尤為必要。
(一)時代背景
城邦制的政治模式、家庭制的辯護立場以及遺囑制的進化演變都促使友愛成為城邦生活不可回避的課題。公民熱衷于參加各種公開性的活動,這都得益于城邦為其提供了充分廣闊的空間,長此以往,公民對于城邦這個共同體的認同感和歸屬感日漸加深,由此家族、部落和城邦緊緊相連、密不可分。彼時希臘人友愛所包含的所有感情因其具有兩個人共同生活及存在感情的特性,都可以在家庭關系(夫妻關系、父子關系和主奴關系)中找到原型[1]。可以發現,友愛關系濫觴于家庭關系。此外,人類有關遺囑的相關理論也可追溯至此,反馬其頓黨以“不敬神祗”的名義陷亞里士多德于水深火熱之中,后者被迫逃亡至優卑亞。臨走之時,亞里士多德立好遺囑并委托其最信任的好友安提帕特為遺囑執行人,好友的所有活動都等同于自己在做這些事情。可見友愛關系已然成為當時古希臘人生活中的重要因素,這也為后期亞里士多德的友愛研究埋下了伏筆。
(二)理論淵源
古希臘時期,關于友愛話題的討論,最早可以追溯到荷馬史詩中關于英雄友愛事跡的歌頌。伴隨著后來歐里庇德斯、恩培多克勒、赫拉克利特等都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及友愛,這一話題逐漸受到人們推崇。而對亞里士多德友愛話題影響最為深遠的當屬柏拉圖談及友愛的多篇對話。柏拉圖在《李思》中首先對友愛進行了較為簡易的提問,試圖將愛產生的原因歸結于欲望的匱乏,但是最終并沒有得到理想的答案。《會飲》中,柏拉圖進一步將友愛局限于男女之愛的范疇,并借助第俄提瑪的精彩說教得出結論:友愛因彼此之間的欲望而產生,實質是一種因其自身既不美也不善從而展開一種對美善事物的追求。而這種追求在《斐德諾》中,被柏拉圖升華為一種欲求的迷狂。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思想根植于他所生活的時代,根本上超越了柏拉圖把友愛等同于愛欲的片面觀點,批判性汲取經典哲學家尤其是柏拉圖關于友愛理論的精髓,在此基礎上梳理歸納出其獨具特色的友愛論思想。
二、亞里士多德友愛觀的理論內涵
在亞里士多德筆下,希臘文Phileo不僅涵蓋了現代漢語意義中的友愛或者友誼,其他所有的人際關系以及社會關系,“如城邦公民之間、家庭成員之間的相互關系都在其考慮的友愛范疇內”[2]。
(一)友愛之特性
《尼各馬科倫理學》第八卷開篇就點明友愛“就是某種德性,或者是賦有德性的事情;或者說是生活所必需的東西,誰也不會愿意去過那種應有盡有而獨缺朋友的生活”[3]。由此可以推斷,德性并非偶然,我們稱個體間存在友愛,意味著一種行動的、活動的關系橫亙于雙方之間,它要求友愛雙方根源于共同的生活。“所應做的德性”最為重要,與感情層面的特殊意義以及潛能而在的東西有所不同,友愛雙方以相似的生活背景為依托,共同建立相似的價值認同,從而在實踐中因共同的德性而共處。同時,友愛在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沒有個體能脫離社會而作為“人”而存在,這是社會運行規則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二)友愛之類型
《尼各馬科倫理學》梳理歸納了友愛的三類形成原因:有用、快樂和善,在此基礎上,關于友愛三種類型的劃分順理成章。
一類是基于有用和基于快樂的友愛,可以統稱為偶性友愛,在亞里士多德看來,友愛的本質內涵在于雙方是因對方的原因而希望他好并由此成為朋友,這是一種毫不掩飾的給予對方的感情。但因為有用或者快樂而和對方成為朋友的人,并不是基于對方的視角,所以我們把這兩類統稱為偶性友愛,它們的共同點在于難以長久維持,因為有用和快樂“來也匆匆去也匆匆”,當繁華不再,友愛雙方極易散伙。
還有一類是德性友愛。“以德交則大異于斯二者,不為利誘,不以樂縻……其所重者,彼此之德”[4]。與偶性友愛根本不同,德性友愛是具備德性的個體因為對方的原因而產生,能夠勸人向善,指出朋友的果過失,而不是因為相互尋求利益進行交往,這種君子之交才是真正長久的友愛。“那些為了朋友自身而希望朋友為善才最是朋友……只有德性才是恒常如一的”[5],由此實現靈魂的合德性的共同活動,這種友愛這也是亞里士多德筆下描繪的最完美的友愛。
三、亞里士多德友愛觀在中國新時代的適宜性解讀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作為建構當代中國意識形態大廈的重要基石之一,無疑是匯集人民共識,凝聚中國力量的燈塔,指明了新時代構建和諧社會的新航向,是文化自信的集中體現,在實現民族復興新征程中起著無可替代的作用。友善作為社交關系中的基本道德規范之一,在探索實踐過程中往往被視作化解沖突矛盾、推動社會和諧的潤滑劑。由此,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視閾下重新研讀亞里士多德的友愛觀顯得極為必要而有意義。
(一)友愛:友善價值觀的理論原點
進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面臨著新的時代課題,要解決和應對發展中新出現的問題和挑戰,必須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出發,提出的重大戰略思想”[6]。友善作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話語體系在個人層面的語言模因之一,在深入解讀和廣泛傳播過程中,挖掘其科學內涵顯然繞不開對亞里士多德友愛觀的重讀,二者之間兼備共同性和差異性。
亞里士多德所研究的友愛范圍廣泛,有別于現代漢語定義上的朋友,其研究范疇包含了城邦公民、商業伙伴乃至家庭成員之間的關系,重新關注亞里士多德友愛觀也為我們當前研討友善核心價值觀提供了理論基點和研究借鑒,兩者對于所處時代的助推作用可謂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從核心價值來看,二者都強調的是公民因對方益處而懷揣善良動機并由此而產生內心的仁愛;從實踐價值來看,二者都不是一種靜止的內在修養,而是一種外在的積極行動;從社會價值來看,無論是亞氏友愛還是與人為善都存在于實際的交往過程中,是兼顧理性自我與他人的善,是高尚利己主義和社會道德要求的統一。
而友善價值觀作為亞里士多德友愛觀的外化和拓展,其科學內涵又有所突破和創新。亞氏友愛觀基于所處城邦道德理念的規范,目的是為了達成“城邦之善”,這從本質上順應了統治者的要求。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話語權的時代大潮中,友愛被賦予了更豐富的內涵,啟航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提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進一步豐富與深化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之友善的理論內涵,人際友善不斷推廣并被放大到國際友善,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外交思想的集中體現,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時俱進的最新理論成果。從古人“天下大同”的理想世界到今天提出的打造新型國際關系,新時代的國際友善觀對于“逆全球化”思潮抬頭而前路不定的當今世界提供了無可替代的中國方案。
(二)友愛:社會和諧的普適情懷
和諧社會的思想精髓因社會發展而薪火相傳,以和諧為特質的文化氣息源遠流長。黨的十六大報告中首次將“社會更加和諧”納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十六屆四中全會將其納入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重要內容,引起學界高度重視;黨的十七大、十八大報告中對構建和諧社會進一步補充強調,指引我們在實踐中不斷推動理論創新;十九大報告明確了“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奮斗目標,強調“和諧”始終是實現偉大夢想必須達成的重要目標之一。
當前,我國已處于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擴大開放的關鍵時期,面臨多重挑戰和不利因素,多種深層次的矛盾交織疊加,一些敏感問題稍有處理不慎就會引發社會跌宕,因而重視和諧問題不可避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作為引領人們思想、引導社會精神風尚的指向標,事關社會發展方方面面,只有深度融入社會生活,才能從本質上筑牢構建和諧社會的社會意識形態基石。作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品德內涵之一,友愛在社會風尚中不僅影響著個體之間的社交往來,更關系到社會秩序的穩定運行,因而和諧社會的構建需要充滿友愛的合格公民去共同發揮推動作用。而新時代面對新形勢新問題,如何發揮友愛在應對各項挑戰中的關鍵作用,也成為了亟需解決的時代話題。
(三)友愛:人際和諧的德性訴求
馬克思曾將人的本質概括為: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只有在與他人交往的關系中才會得以充分體現。中國傳統的“和諧”理念也極為重視人際關系和諧的構建,尤以有子所秉持的“和為貴”理念為典型,這也為儒家所秉持的中庸之道在處理社交關系上的基本準則奠定了思想基礎。經典作家和傳統文化為“和諧”理念在現代社會中的價值取向進一步深化提供了思想淵源,在新時代體現為社會個體之間的心靈有序溝通,其倫理學內涵就是彼此之間按照有序、協調、友愛的完善規則有序交往。據此,“關系”升華為和諧社會的核心意蘊與價值取向。
個體的價值取向具有差異性,現代社會生活節奏加快和各類競爭不斷加劇,使得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極易變得緊張、脆弱,因而,構建和諧的社會人際關系,也是筑牢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每一個友愛個體都是在社會公共生活中打破孤立自閉的封鎖狀態,彼此之間共同維護情感。這也與遠古人類最初互幫互助的原始本能不謀而合,當自然風險來襲,人類只有團結起來才能抵御災害以維持生存,盡管帶有私利性質的自我拯救不可避免,但在一定程度上卻成全了雙方之間的互助合作。作為一種關系性德性,友愛本身作為一個有效溝通渠道存在,激發社會成員在社交中相互磨合進而構筑良好社會秩序的內生性,通過外部介入來培育個體間向心與和諧的原始動能,以聚合雙方心靈達到有序交融,社會整體也因友愛的原力彌合而凸顯和諧魅力。
(四)友愛:自我和諧的理論歸宿
亞里士多德有關友愛觀的解讀占據了整整兩卷的內容,正如他所言,友愛作為社會成員之間的一種精神往來,它“似乎是取決于人們如何對待自身”[7]。但這種將友愛源于自身的觀點在過往通常被解讀為自私自利的一種表現。事實上,亞里士多德的自愛觀根本別于現代漢語語境中所定義的“自私”,自愛更偏重于在理性自我和他人之間兼顧的善,這種高尚的利己主義本質上并未違背社會道德要求,“自愛論”無疑為我們在構建和諧社會的語境中重視個體自由發展提供了新的思考與啟示。
我們所追求的道德理想始終是在有序和諧的友愛社會中實現自我身心和諧,這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社會進步的宏偉目標和個體自由的展示、個體的全面發展并行不悖。馬克思認為,“正像社會本身生產作為人的人一樣,社會也是由人生產的”[8]。自我反映社會個體對自身存在狀態的認知,從根本上影響個體的情感體驗,對個體所扮演的社會角色在人際關系中能否架構和諧的社交網絡起著重要作用。和諧社會的本質在于人與人之間的和諧,而個體的自我和諧可以說是這層含義的深層次延伸與終極體現。作為道德理想的“友愛”觀念,在塑造新時代團結友愛的人際關系和成熟穩定的社會心態之歷史進程中發揮著不可或缺作用,有利于個體的自我解放和全面發展,達成自我和諧。友愛乃至自愛在現實中完全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科學內涵高度吻合,而其又最終上升到更高層次的道德理想追求,融理想與情感、長遠與當前、社會與個體為一爐,在培育新時代合格公民的目標下,實現個體的全面發展甚而臻至道德完善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