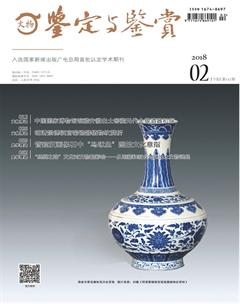臨汾地區金元時期佛教寺院經濟生活探析
王一君
摘 要:臨汾地區金元時期的寺院財產來源以民眾布施、寺僧捐贈及統治階層的捐助為主,房舍、土地、樹木園林是寺院的主要財產。當時臨汾地區寺院經濟的發展雖有一定規模,但與山西乃至全國相比還有較大差距,這與臨汾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有直接關系。
關鍵詞:金代;元代;寺院經濟
寺院經濟是伴隨著佛教的興起、發展,寺廟的新建、擴建,僧人的增多,佛事活動的頻繁逐步形成的。為了供應僧侶衣食、維修和擴建寺廟、開展正常佛事活動,寺院必須有一定的經濟收入方能維持。實際上,寺院經濟也是金元社會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研究寺院經濟利于我們更深入全面地了解金元時期的佛教生活。因此,筆者對臨汾地區金元時期的寺院經濟有若干愚見,懇請各位方家指正。
1 寺院資產的主要來源
1.1 民眾布施
按照佛教觀點,向寺院布施以供養三寶是獲得來生福報的重要方式,受此影響,佛教信眾不斷向寺院施舍,從而為寺院贏得大量資產。信眾施舍的方式多種多樣,有的僅僅是一對石柱,如元大德十一年(1307),“北楊村眾人等興功管飯置造石腳柱一對,伏愿風調雨順,國泰民安”。有些信眾則施予土地,如金皇統二年(1142),《大金國碑文之圖》:“謹發虔誠于天會年中,韓智、韓德、韓越等施寺地六分,修佛堂一所。”上述普通信眾雖有強烈的向佛之心,但畢竟經濟能力有限,因此捐獻數量也是有限的。元元統二年(1334),《重修寶峰院碑記》載:“昔者衹陁施樹,長者買園,共成寶剎……忽直天兵入界,劫火焚毀。口兵革已后,本村人巖公和尚,于本村觀音院住持剃度門人,同時置買田地,膳濟眾僧。門人了意發起重修寶峰院。當年秋旱薄收,漸轉物斛增價,每一碩米麥價直百貫,時世饑饉,人民口口游食忍苦,餓殍甚廣。祖言慰諭眾僧曰:‘稍有菲薄之膳,且安然而住。漸至豐年,行緣修葺,創建西廊五檫四椽,更修口口口座,又磚砌地面基堦,及塑繪関王一堂。”本次重修歷經六年,共花費一百三十七兩,在秋旱薄收、餓殍甚廣的年代,靠廣大村民募捐支撐了這一工程,其中不乏年紀90歲以上的老人,其艱難程度可想而知,足以證明侯馬上馬鄉民眾對于佛寺活動的支持和佛教文化的崇拜。
1.2 寺院僧眾捐贈
寺院維修擴建時,會向周圍信徒或社會上樂善好施的人募化,待完工后立碑石流傳后世。平時也有僧人募化四方,為寺廟募集“香火”資源,用以維持僧眾的生活。此外,僧眾也會為修建寺院而竭盡全力,甚至窮其一生都在做這一件事情,可見其心之虔誠。
元代一些寺僧會將身后家產贈與寺院。泰云寺就有一份地產來自于寬公及其先祖:“初,師之父張三十與師之房叔張實,共有水磨一區……仍將己身磨分施與本院,以為終焉之計。”“然則師之四分之一也,師將己分所得之資,遂為衣盂之費。其本院三門外,師麻地一畝二分,遂施與本院,以廣三門基址之路。師修本院鐘樓,又將□泉水白地七畝準工資與梓匠,作典價土布三十疋,許令徒弟贖收為生……”寺僧施舍家產是出于佛教信仰。從形式上說,這些捐贈都應該是無條件的,但從石刻史料記載來看,捐贈者卻是有著明確的目的,如要求寺院在捐贈本人去世后為其追薦冥符,代祭先祖。“今□將逝,永絕奉祀,心實惻然,為之奈何!適有吾祖遺業,地土已歸用于本院外,有水磨四分中一分,又地基二間,計地四分有余,請付本院常住,每遇歲時,寄附祭祀先祖眾靈。”此次布施就是囑托寺僧按節祭祀其俗家先祖,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佛教的中國化,也可以看作是寺院社會公益功能的延伸和擴展。無論這種捐贈是否設定了前提,它的結果是相同的,即寺僧的捐贈最終化為寺院財產。
1.3 統治階層對寺院的捐助
統治階層對寺院的捐助從側面說明了對佛教的態度,從現有史料來看,除積極修繕寺院外,統治階層有時還會拿出自己的俸祿“捐資助力”。元至正十六年(1356),《重修坤柔廟記》載:“至正八年,前吉州吏曹巨卿等輸材鳩工,為正五楹,香亭二楹,余則未加修葺。”碑文中提到了統治階層在看到摧殘殆盡的寺廟后積極修繕的行為,足以證明對佛教的重視和支持。此外,京兆監察御史之子修己于“十五年夏事緩,乃首捐俸金,率諸僚友暨士民樂輸材力,重飾正殿、香亭”。
寺院是佛教傳播的主要場所,統治階層和社會大眾積極參與寺院的創建和修復是佛教得以恢復和發展的重要因素。而很多時候,統治者和善男信女們為修建寺院竭盡所能,往往一人振臂,群起響應。
2 寺院資產的類型
佛教雖是出塵之學,但畢竟生長在俗世之中,離不開最基本的物質需求。《大般涅槃經》云:“若諸弟子無有檀越供給所須,時世饑饉,飲食難得,為欲建立護持正法,我聽弟子受畜奴婢、金銀車乘、田宅谷米、賣易所須。”[1]釋迦允許弟子從事商業活動的本意也是為了使其能夠安身立命,但魏晉之后,寺院財產較多,大至名寺廣剎,小至山野寺庵,佛教寺院或多或少都有些財產,由此構成了寺院經濟。寺院經濟的種類因其規模的不同而不同。
2.1 房舍
房舍是僧人賴以棲身之所,也是寺院重要的不動產。僧寺房舍的多少也因寺院的規模而有所不同。金代懷州明月山大明禪院有“大小屋舍一百余間”,金末長清靈巖寺“有屋三百余間”。曲沃大悲院,宋、金皆重修,為該地重要寺廟。宋治平四年(1067)重修時賜額,“□從治平四年□月□□□□院已蒙朝廷取會,屋宇至三十間以上者,并賜敕額,以壽圣為名,其余皆不許存留,伏望與免根治□從殿正本部□符福建運司相度……寺舍共計三千六百四十二所,并不曾經賜敕額數內三千二百四十五所,系治平四年正月一日已前建造”,可知當時寺廟規模較大。金正隆四年(1159),宗瑩住持廣勝寺期間,“展修官客位一所,四十余間”[2]。元代裕公和尚住勝因寺時,“創建法堂廊廡三十余間”[3]。而一些小規模的山野庵院,可能只有幾間。
2.2 土地
在封建社會土地是財富的象征,也是寺院的一項重要資產。寺院所占有的土地在一定程度上鞏固了佛教在社會經濟中的地位。金貞元元年(1153)《董村重修太上佛神廟志》中記載了該廟寺產的四方范圍:“今具殿基四至:東至王純,西至渠,東西闊南頭二十二步,北頭一十九步三尺;南至渠,北至殿后檐滴水澗痕外五尺為界。北至官河,南北長東邊三十二步二尺,西邊四十八步。”土地范圍的嚴格劃分利于僧人的管理,碑文中詳列了每段土地的四至,竭力做到“各段四至,各各分明”,免生訴訟。碑文在這里起到了鄉約的作用,以保障土地的合理利用,不至于受到侵害或者私自出售。
土地的買進是臨汾地區金元時期發展寺院經濟的一種重要途徑。山野寺院和一些小規模的寺院由于沒有國家和統治階層的全力扶持,所以在寺產方面較名寺大剎懸殊,也可以看作是佛教僧團貧富分化的一個縮影。
2.3 樹木園林
金元時期,一些寺院所擁有的樹木園林也是寺院的重要財產。明姜鎮東董村的太上佛神廟有“繞殿白楊樹六株,畜官馬仙生殿東一株,殿內五株,載植弗記□矣,皇統元年三月七日王顯太栽。槐樹二株,王長、官莊王伸施;柏樹一株,劉文施。皇統七年三月二十六日,王四哥接為矮槐。住長生堂道人王顯太、孔晏大,常得閏歷代久遠為記”的記載,碑文中信眾對于寺廟樹木的捐贈和種植轉化為該廟的資產。元至元五年(1268)《靈光寺祖師德業碑銘并序》:“此寺水陸產業四頃之盛,明德水白地土、棗木園林僅于百畝。”碑文中詳細記錄了靈光寺光棗木園林就有百畝,說明其寺產以林木為主。除此,還有水陸產業四頃,這樣既可以做到自給自足,也可以成為寺院和僧人收入的一個重要來源,由此林木產業對靈光寺的重要不問而知。
金元時期臨汾地區的寺院財產以民眾布施和寺僧捐助為多,房舍、土地、樹木園林是寺院的主要財產。從目前資料所載,臨汾地區寺院經濟雖有一定規模,但與山西乃至全國相比還有較大差距,這與臨汾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有直接關系。盡管如此,寺院經濟仍為臨汾地區的佛教發展奠定了重要物質基礎。
參考文獻
[1](北涼)曇無讖譯.大般涅槃經·卷6//大正藏·第12冊.
[2]汪學文.平陽府趙城縣霍山廣勝寺瑩山主塔銘[M]//三晉石刻大全·洪洞卷[M].太原:三晉出版社,2008.
[3]趙孟頫.裕公和尚道行碑[M]//翼城縣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