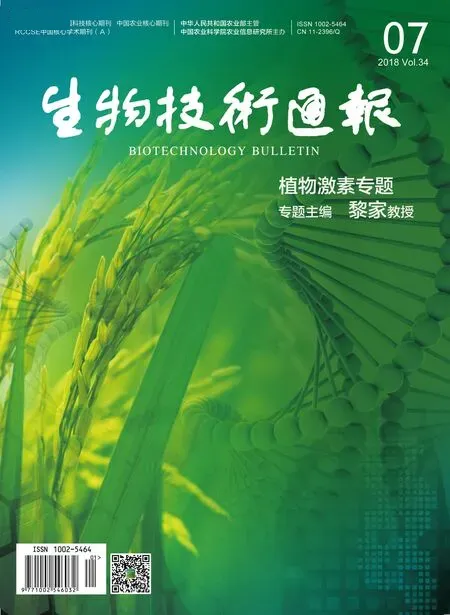植物細胞內膜運輸對植物發育的調控機制
龐磊 朱穎 金中財 夏曦華 李瑞熙
(南方科技大學生物系 植物與食品研究所,深圳 518055)
真核細胞的內膜系統由一系列連續的內膜結構組成,包括核膜、內質網、高爾基體、液泡/溶酶體、轉運囊泡和細胞膜。不同內膜結構之間存在網絡式的內膜運輸,這對細胞內蛋白質和酯類的運輸和交換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植物細胞內膜體系與別的真核生物體系相似,但也有植物細胞特有的結構和運輸方式[1]。其中最典型的結構是位于高爾基體反式表面上由一系列互相連接且具有動態性的細管和囊泡組成的反式高爾基體(Trans-Golgi network,TGN)。反式高爾基體作為植物細胞內的分選中心,引導蛋白轉運至不同內膜細胞器及分泌到胞外空間。最近研究結果表明,反式高爾基體也可作為植物細胞的早期內吞體(Early endosome,EE),接受來自于細胞膜內吞形成的囊泡。利用超高分辨率顯微鏡技術,研究者觀察到植物細胞反式高爾基體可以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高爾基體連接的反式高爾基體(Golgi-associated TGN),位于高爾基體反式一側;另一種是不依附高爾基體的相對獨立的反式高爾基體(Golgi-released independent TGN)[2-3]。
另一個植物細胞特有的細胞器是液泡。植物液泡作為成熟細胞中最大的細胞器是植物體內維持細胞膨壓和促進細胞體積擴張的主要細胞器,也是次生代謝物儲存、蛋白質和細胞器降解、氨基酸循環利用、毒害物質去除和病蟲害抵御的重要場所。液泡運輸根據膜來源和途經細胞器差異可以大致分為兩大類途徑。一類是不依賴高爾基體直接從內質網向液泡運輸的途徑,包括玉米糊粉層蛋白和南瓜子葉儲藏蛋白等。這一途徑是植物特有的液泡運輸途徑,對種子萌發,單子葉植物胚乳形成以及次生代謝物和激素儲藏具有重要作用[4-8]。另一大類是經過高爾基體的運輸途徑,又可細分為三種相對獨立的液泡運輸途徑,包括由AP3復合體介導的直接從高爾基體向液泡運輸的途徑[9-10]、受小G蛋白Rab5 GTPase直接調控的液泡運輸途徑,以及依賴于Rab5向Rab7 GTPase轉化的液泡運輸途徑等[11-14]。
植物細胞內膜結構的特異性不僅介導了一系列植物特有的內膜運輸方式,也對植物發育起著重要作用。本文將從幾個方面綜述植物細胞內膜運輸對發育的調控作用,包括內膜運輸與生長素極性運輸和穩態平衡之間的關系,內膜運輸對根毛極性生長的作用機理,以及液泡運輸在花粉管極性生長和種子萌發過程中的重要作用。
1 植物細胞內膜運輸對長素極性運輸的調控機制
生長素主要以離子態(IAA-)的形式存在于植物體內,在不同細胞和組織間的移動需依賴質膜(Plasma membrane,PM)上的運輸載體蛋白[15]。在已被證實具有生長素運輸功能的載體蛋白中,PINFORMED(PIN)蛋白的研究最為深入。PIN蛋白家族在擬南芥中有8個成員,分別命名為PIN1-PIN8。PIN蛋白均為膜蛋白,具有兩個疏水跨膜區和中央胞內親水環。根據親水環長度,將PIN蛋白分成兩個亞家族:具有長親水環的PIN1、PIN2、PIN3、PIN4和PIN7,定位在細胞膜上呈不對稱極性分布,負責向細胞外運輸生長素;具有較短親水結構域的PIN5、PIN6和PIN8,定位于內質網上,介導內質網和細胞質間的生長素平衡[16-17]。在很多組織中,PIN蛋白具有極性定位的特征并且介導了生長素的極性運輸。例如,在植物根尖中柱細胞表達的PIN1蛋白和內皮層表達的PIN2蛋白為基底極性(basal polarity)定位,而位于莖尖分生組織的PIN1蛋白和根尖表皮細胞的PIN2蛋白為頂端極性(apical polarity)分布,分別介導生長素向根尖和向莖尖方向極性運輸[18]。因此,PIN蛋白極性缺失會阻礙生長素的極性運輸,進而導致胚胎發育出現缺陷、細胞極性及植株形態建成異常[19]。
在亞細胞水平上,PIN蛋白均只在質膜上被檢測到,但事實上,PIN蛋白的質膜極性受內膜系統中的多條囊泡運輸(Vesicular trafficking)途徑共同協調控制[20]。質膜蛋白在內質網(Endoplastic reticulum,ER)被合成后,通常依靠囊泡運輸參與的胞外分泌途徑,經由高爾基體(Golgi)或反式高爾基體/早期內涵體(Trans-Golgi networks/early endosomes,TGN/EE)分選后出芽形成包被小泡(Coated vesicle),在小G蛋白的介導下被運輸到質膜上[21]。后期的胞吞(Endocytosis)將質膜蛋白運輸到TGN/EE,其中一部分通過再循環(Recycling)從TGN/EE被運回到質膜上;另一部分則隨囊泡成熟和融合過程進入晚期內吞體/液泡前體(Late endosome/pre-vacuolar compartment,LE/PVC)到達液泡被降解。因此,植物細胞能夠根據外環境通過胞吞和再循環途徑精準調節膜蛋白在質膜上的豐度。
胞吞過程在真核生物中具有高度的保守型,在動物細胞中,Rab5 GTPase是調控胞吞作用的關鍵因子[22]。在擬南芥中,ARA7是Rab5 GTPase的同源蛋白。PIN蛋白在ARA7/Rab5 GTPase的GEF因子VPS9A功能缺失突變體或持續表達組成型失活狀態(Dominantly negative,DN)下的 ARA7(DN-ARA7)的背景下失去質膜上的極性分布,并且胚胎出現嚴重的發育缺陷[23],說明胞吞作用參與PIN蛋白質膜極性定位的調控機制。PIN蛋白與接頭蛋白(Adaptor proteins)AP2復合體在質膜上結合后能夠招募網格蛋白(Clatherin),形成包被小泡啟動PIN蛋白的胞吞過程[24],而AP2復合體亞基和構成網格蛋白的輕鏈或重鏈基因的功能缺失均導致PIN蛋白完全失去基底或頂端極性定位[24-26],進一步說明胞吞在調控PIN蛋白質膜極性定位途徑中的重要功能。此外,GFP與網格蛋白CLC融合表達顯示GFP信號強度在側面質膜上明顯高于基底和頂端質膜,而化學抑制劑Tyrphostin A23處理后,PIN2蛋白在側面與頂端質膜上的信號比值明顯增加[27],表明側面質膜上網格蛋白介導的胞吞對PIN蛋白基底和頂端的極性定位具有決定性作用。
另一方面,為了維持PIN蛋白在質膜上的豐度,植物細胞內的小G蛋白介導的囊泡運輸能夠將部分PIN蛋白從TGN/EE通過再循環途徑運輸到質膜上。真菌霉素Brefidin A(BFA)能夠阻礙從TGN/EE到質膜上的囊泡運輸途徑。BFA處理能夠引起PIN1蛋白質在細胞質中的聚集形成所謂的“BFA聚合物”,導致PIN1蛋白失去基底極性分布;而BFA被洗脫后,抑制效應被解除,PIN1蛋白恢復其在基底質膜上極性分布[28]。ADP核糖基化鳥苷酸交換因子(ADP-ribosylation factor guaninenucleotide exchange factors,ARF-GEFs)GNOM 作 為ARF1 GTPase的GEF因子,能夠激活ARF1 GTPase酶的活性,介導PIN1蛋白的向底性再循環途徑,而PIN1蛋白在GNOM功能缺失突變體的背景下完全失去極性分布[29]。因此,PIN1蛋白的向底性再循環途徑受ARF-GEF GNOM所調控,且BFA能夠抑制該途徑。與之相反,BFA處理對PIN2蛋白的頂端極性分布影響不大[30],表明植物細胞內存在著不同的內膜運輸途徑分別介導PIN蛋白的向底性和向頂性運輸。最近研究表明,小分子化合物- Endosidin16(ES16)能夠特異性誘導頂端極性定位的 PIN2 蛋白形成類似于“BFA聚合體”的胞內聚合物并改變其頂端極性分布,但卻不影響胞吞過程和PIN1的向底性循環[31]。藥物親和反應靶點穩定性(Drug affinity responsive target stability,DARTS)分析進一步發現ES16 不直接作用于鳥苷酸交換因子ARF-GEF家族蛋白,包括GBF亞支和BIG亞支蛋白,但能特異性抑制一類小型GTP酶-RabA GTPases,并能特異性靶定于 RabA2A GTPase[31]。PIN2 蛋白在組成型失活狀態的RabA2A(DN-RabA2A)的背景下也在細胞內形成類似于ES16處理后的胞內聚合物,并且其頂端極性分布發生改變[31],表明RabA2A GTPase很可能參與了PIN2蛋白向頂性循環的調控途徑。除此之外,介導囊泡與質膜栓系的Exocyst復合體亞基功能缺失也會導致PIN蛋白基底和頂端極性定位發生缺陷[32-33]。以上結果表明PIN蛋白的極性定位由內膜運輸中的持續性胞吞和再循環途徑共同調控來實現的,且PIN蛋白的基底和頂端極性定位由不同的內膜運輸途徑所調控。
2 植物細胞內膜運輸對生長素穩態平衡的調控作用
Mravec等[17]在2009年首次報道了定位于內質網的PIN5參與調節細胞內生長素的平衡。該文首先證明了PIN5與經典的PIN一樣具有運輸生長素的能力。之后的亞細胞定位分析表明PIN5并不像經典的長PIN定位于質膜,而是定位于內質網。通過對擬南芥PIN家族8個成員進行氨基酸序列比對,作者發現PIN蛋白中存在一個推測的含酪氨酸的基序(NPNTY)。質膜定位的PIN蛋白在推測的酪氨酸基序附近含有一段高度保守的序列(MVWRKL),而這段序列在PIN5亞類的蛋白中并不是高度保守。作者將PIN1的含酪氨酸基序突變為NSLSL,失去酪氨酸基序的PIN1定位于內質網。但這一結果并不能很好的解釋兩個亞類的PIN蛋白存在不同亞細胞定位的原因[17]。Ganguly等[34]關注于兩個亞類的 PIN蛋白存在最大差異的親水性環,研究了親水性環對PIN蛋白亞細胞定位的作用。作者選取了兩個具有代表性的PIN蛋白PIN2和PIN5,將PIN2的長親水性環導入PIN5短親水性環的區域,并用PIN5自身啟動子驅動,改造后的PIN5和PIN2一樣定位于質膜,并且和其他質膜定位的PIN蛋白類似,在BFA處理后能形成BFA小體,而正常的PIN5則不能形成。說明PIN2的長親水性環確實能介導非質膜定位的PIN5向質膜運輸,但并不足以令PIN5像PIN2一樣在細胞內存在極性定位。
短PIN家族的另一個成員PIN8特異性定位于花粉中,與PIN5一樣定位于內質網,參與調節細胞內生長素的平衡,對花粉的發育和花粉管的生長至關重要[35-36]。Dal Bosco等[37]通過構建 PIN8 過表達的轉基因擬南芥及異源表達PIN8的轉基因煙草分析了PIN8在調控細胞內生長素穩態方面的作用。PIN8的異位表達造成了強烈的生長素相關的表型,表型的嚴重程度依賴于PIN8的蛋白水平,并且與自由態生長素和束縛態生長素的上升水平呈正相關。當用NAA處理PIN8過表達的幼苗時,生長素響應基因被強烈的抑制。這些結果表明內質網定位的PIN8在控制生長素閾值,調控生長素相關的轉錄方面有重要作用[38]。Ding等[36]也做了類似關于PIN8的研究,并且揭示了PIN8和PIN5在調節細胞內生長素平衡方面起著拮抗作用。pin5突變體表現出與pin8突變體同樣比例的形態缺陷型花粉粒,但pin5pin8雙重突變體可以恢復花粉形態缺陷的表型。Dal Bosco等[37]隨后對這一結果提出了疑問。PIN5廣泛表達于各組織中,在花粉中并沒有很高的表達,相反PIN8只在花粉中表達。那么在花粉的發育過程中,缺少PIN5如何能恢復花粉特異性的表型? 結合pin5、pin8 單突變體、pin5pin8雙突變體,以及PIN5和PIN8單過表達和雙過表達株系的分析。Ding等[36]認為PIN5和PIN8在功能上相互拮抗可能是通過兩種方式。PIN5調節生長素從細胞質運輸到內質網腔,PIN8可能作為一個活性的生長素運輸載體介導生長素從內質網腔流向細胞質,也可能通過負調控PIN5的活性而起到拮抗作用。
PIN6是PIN蛋白家族中一個較特殊的成員,在結構上它更接近經典的長PIN蛋白[39],具有長親水性環。在進化上則與短PIN蛋白亞類(PIN5和 PIN8)距離更近[17]。Simon等[39]在 2016年對PIN6的亞細胞定位及功能進行了詳細分析。亞細胞定位的研究揭示PIN6在質膜和內質網均有定位。生長素運輸和代謝實驗表明PIN6可以介導生長素跨質膜運輸以及細胞內生長素的平衡,包括調節自由態生長素和束縛態生長素的水平。進一步的功能分析顯示側根和不定根發生過程中生長素的分配都需要PIN6的參與。Ditengou等[40]進一步分析了PIN6存在內質網與質膜雙重定位的機制。研究發現在PIN6表達水平較低的組織,如根中,PIN6定位于內質網,而在PIN6表達較高的花序莖中,PIN6則定位于質膜。而造成PIN6的雙重定位的原因是MPK4和MPK6對PIN6的磷酸化。PIN6的亞細胞定位是受到組織特異性的發育信號對其表達水平及磷酸化狀態的調控。
3 植物細胞內膜運輸對根毛極性生長的調控作用
植物的根毛是由單個表皮細胞通過極性生長發育而來的。通常我們把根毛的生長發育劃分為3個階段:命運決定、根毛起始和尖端生長。對擬南芥的根毛來說,命運決定階段是以GL2為核心的信號網絡決定表皮細胞是發育成根毛還是非根毛。根毛起始階段決定了根毛的平面極性,即根毛的起始位置是靠近根尖側(Basal)還是遠離根尖的一側(Apical)。尖端生長則是根毛起始后直到成熟前的快速伸長階段[41]。
根毛從起始開始便進入極性發育過程,這一過程的建立和維持受到一系列因素調控,包括植物激素、脂筏、磷脂酰肌醇、ROP GTPases、Ca2+、ROS、細胞骨架和囊泡運輸等。其中囊泡運輸的極性又受到其它各因素直接或間接的調控。根毛尖端的快速生長需要新的細胞膜和細胞壁成分的供應,伴隨著大量的脂質、蛋白質和多糖的轉運。這一過程主要由細胞內膜組成的囊泡運輸完成。
內膜運輸主要過程可以分為五步:第一步,從供體膜上出芽并裝載正確的貨物形成囊泡。ARF GTPases在此過程中起著重要作用。ARF GTPases是一類小G蛋白,參與調控內膜運輸和肌動蛋白的組裝過程[42]。擬南芥基因組總共編碼了21個ARF GTPases,其中有6個屬于ARF1家族。第二步,囊泡被傳送到他們的最終目的地。這依賴于作為運輸橋梁的細胞骨架朝著正確方向組裝。第三步,囊泡被靶標膜捕獲并栓系在一起,這一過程需要由栓系因子(Tethering factors)和Rab GTPases的參與。目前有報道的能作用于根毛形態發生過程中的栓系因子只有Exocyst。Exocyst 是一個巨大的多亞基的栓系復合體。GTP結合狀態下的Rab GTPases具有連接囊泡和靶標膜的功能。擬南芥基因組共編碼了57個Rab GTPases,其中RabA占有最大的比例,有26個成員[43]。它主要在反式高爾基體以及后高爾基體囊泡運輸的調控中發揮作用。其中RabA4b已經被證實能夠調控根毛的形態發生。RabA4b定位在根毛的尖端,在根毛成熟后消失。酵母雙雜實驗證實了RabA4b與磷脂酰肌醇激酶(PI-4Kβ1)能夠互作。而且PI-4Kβ1還能與一種鈣離子感受器互作[44]。因此,RabA4b被認為具有能夠整合膜運輸、磷脂酰肌醇信號和頂端鈣離子感知的功能。第四步,囊泡和靶標膜相互融合,從而成功卸載貨物。SNAREs和其調控因子Sec1是介導這一過程的主要蛋白。擬南芥基因組編碼了大量的SNAREs。系統發育分析表明植物細胞膜上至少含有5種t-SNAREs的亞族syntaxins。Sec1蛋白結合syntaxin或者t-SNAREs并使其構象發生改變。在動物細胞里,Sec1結合到syntaxin上導致syntaxin形成閉合態構象,無法與v-SNARE互作。擬南芥基因組總共編碼了6個Sec1基因,其中的一個叫KEULE的已經被證實參與到根毛形態發生和細胞分裂過程中[45]。KEULE已經被證實具有Sec1的特征,包括與syntaxin的結合性能。根毛的正常發育需要Sec1的正常功能,因此這也間接的證明了SNAREs也參與到根毛的形態發生。第五步,參與膜運輸的工具分子被重新回收為下一輪運輸作準備。
囊泡在根毛內朝尖端極性運輸的建立和維持需要各調控因子由上到下的精密控制。生長素作為內源的位置信號,由IAA和H+的共轉運蛋白AUX1轉運進入細胞。在胞內,部分生長素結合其受體SCFTIR1/ARF復合體后導致Ca2+通道CNGC14被激活,進而造成胞內Ca2+濃度改變,進而通過調控細胞骨架組裝來控制內膜運輸,并能通過synaptotagmin進行信號轉換,減少膜融合需要的活化能,促進尖端的膜融合[46-47]。在植物體內的Rho GTPases被稱為ROPs,它們在根毛形態發生起重要的指揮作用,能直接或間接的調控胞內囊泡運輸極性。擬南芥總共有11個ROPs成員,其中ROP2、ROP4和ROP6在根毛起始和尖端的位置積累,而組成性活化(Constitutively active,CA)的ROP2、ROP4、ROP6和ROP11會導致球狀根毛的產生。過表達ROP2的植株根毛產生大量分支,說明ROP2在根毛分化過程中起作用。
最近的研究發現,ROP2除了受到GEF、GAP和GDI調控外,還受到MAP18的調控,MAP18通過與GDI/SCN1競爭性的結合ROP2-GDP促進活性ROP2的生成,從而調節細胞骨架,同時MAP18還能直接調控微觀組裝過程[48]。在酵母中的實驗證明,Exocyst復合體的某些亞基的正確定位依賴于RHO1。而在動物細胞中,Exo70可能主要介導了Rho和Exocyst的互作。有趣的是,擬南芥中至少有23個Exo70,目前發現EXO70A1參與到根毛尖端生長[49]。某些蛋白如ROPs和GPI(Glycosylphosphatidylinositol)錨定蛋白在細胞膜上的極性定位對其發揮信號指示作用極其重要。細胞膜上的脂筏可能提供了這樣一個特殊的錨定位點,并為囊泡的極性分泌提供了港口。Ovecka等[50-51]對根毛內富含甾醇的脂筏的分布和Zhao的觀測結果均支持了這一觀點。另外,一個有趣的突變體orc,也叫cephalopod或者smt1orc,是STEROL METHYLTRANSFERASE1基因的一個等位基因,參與到甾醇類合成的烷基化反應中。在smt1orc背景下,根毛的起始的平面極性遭到破壞,這也說明甾醇類參與了根毛起始位置的選擇[52]。
總而言之,囊泡在根毛發育過程中的極性運輸是一個受到多種因素嚴格調控又存在反饋調節的復雜過程,還有許多未知的機制需要進一步的研究。
4 植物細胞液泡運輸對花粉管極性生長和種子萌發的調控機理。
4.1 液泡運輸在花粉管極性生長過程中的作用
花粉管是一種高度極化的細胞,其生長的過程涉及復雜的細胞內活動。之前的研究結果表明,液泡對于花粉管的生長至關重要。植物細胞內液泡運輸主要有:(1)PVC/MVB介導的依賴于Rab5到Rab7轉化的途徑;(2)只依賴于Rab5的途徑;(3)只依賴于AP3的途徑;(4)直接由內質網到液泡的途徑[11]。Rab GTPase參與了蛋白運輸的全過程:囊泡的形成、運輸、與細胞膜的對接、黏附、錨定和融合等。Rab GTPase與GDP結合時處于失活狀態,與GTP結合時處于激活狀態,定位在膜上的Rab7能夠被特定的鳥嘌呤核苷酸置換因子MON1/CCZ1激活,介導PVC與液泡的融合[50]。在mon1的突變體中,由于Rab7介導的液泡運輸絲氨酸蛋白酶功能的缺失,花粉絨氈層細胞無法正常進行程序性死亡,產生異常的花粉包被影響花粉的萌發和花粉管的生長[53-55]。
介導液泡融合過程的栓留復合體HOPS(Homotypic fusion and vacuole protein sorting)由4個核心亞基 VPS11、VPS16、VPS18和 VPS33,以及 2個特異亞基VPS39和VPS41組成[56-58]。這些亞基在植物中都是單拷貝,對應的突變純合致死,通過對受精過程的研究發現,HOPS復合體中的亞基液泡分選蛋白VPS41參與了將胞外信號分子及其他物質從細胞膜上運進液泡或者其他亞細胞區間內進行降解的生物學過程,vps41突變體花粉管中早期從膜上到晚期內吞體的內膜運輸過程是正常的,但是從晚期內吞體到液泡的運輸過程受到嚴重影響,導致需要被運輸到液泡降解的信號分子無法及時的被降解,引發信號途徑的紊亂,從而影響花粉管的生長,使其無法穿入柱頭,有性生殖過程受到影響,導致不育[59]。而在vps11的突變體的花粉管中,液泡的形態并沒有發生顯著變化,但是其花粉管的伸長受到了顯著的抑制[60],以上結果說明,參與液泡運輸的HOPS復合體通過不同的方式影響花粉管的發育,任何亞基的缺失突變會導致嚴重發育表型的出現。此外,張彥課題組最新的研究發現在銜接蛋白ap3突變體中,AP3復合體靶向液泡膜的“貨物”棕櫚酰基轉移酶PAT10和其棕櫚酰化底物CBLs在花粉管內失去了原本的液泡膜定位,而呈現高爾基體定位,并且花粉管內鈣離子濃度顯著降低,液泡形態發生異常,影響了花粉管的生長[61-64]。
4.2 液泡運輸在種子萌發過程中的作用
大部分有花植物通過有性生殖和產生種子繁衍后代,因此種子活力的保持和順利萌發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65-66]。種子萌發的過程受到植物激素、光、一氧化氮和小RNA等復雜的調控網絡協調控制[67-72],并且細胞內發生一系列復雜的生理變化:細胞內膜系統內質網和高爾基體大量增殖,一方面高爾基體運輸物質到細胞壁作為合成的原料;另一方面內質網產生的小液泡吸水脹大并且相互融合,形成大液泡使細胞體積增大,促進種子萌發[66,72]。在種子萌發的過程中液泡運輸對于種子儲藏蛋白的轉運、pH的維持,以及特定蛋白如離子通道蛋白和轉運蛋白的定位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液泡運輸蛋白MAIGO2(MAG2)與定位在內質網上的t-SNARE組分SYP81/AtUfe1和SEC20互作,促進種子萌發過程中儲藏蛋白從合成部位內質網到翻譯后修飾部位高爾基體的運輸[73]。在mag2的突變體中,由于儲藏蛋白運輸功能的缺失導致細胞內質網中大量不正常MAG小體的形成,種子萌發受到嚴重影響[74-75]。銜接蛋白復合體AP3參與了從高爾基體到液泡的運輸,對于液泡形態的維持和功能的發揮起著關鍵作用。AP3復合體的亞基AP3β和AP3δ蛋白功能的缺失會導致大量原本定位在液泡膜上的蛋白在細胞質中積累,影響細胞內pH的穩態和種子的萌發,而其顯性負突變體在種子萌發的過程中表現出對弱酸條件抗性的增強[62-63]。
綜上所述,植物細胞內膜運輸對植物發育各個階段起著重要調控作用。內膜運輸突變體表現出組織特異性或發育時期特異性缺陷。然而,現階段研究主要集中在內膜運輸機制及表型的描述,發育信號與內膜系統的銜接以及內膜蛋白相應上游信號的機制尚未有深入探索。這方面空白有待于以后進一步研究發現來填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