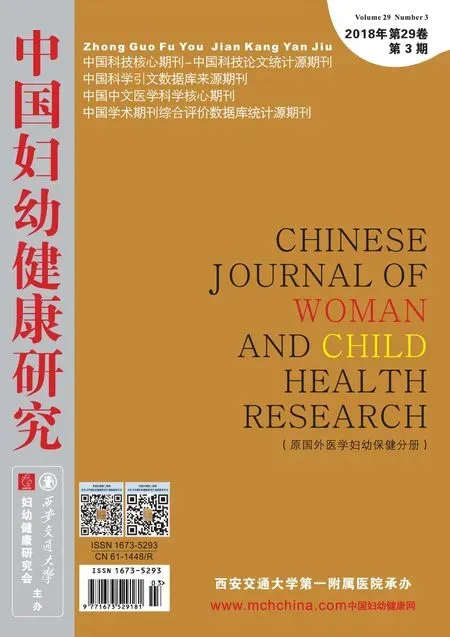疤痕子宮合并中央性前置胎盤的圍術期并發(fā)癥
蔡建云,顧新安,王 謹,張雪玲
(1.上海市同濟大學附屬楊浦醫(yī)院上海市楊浦區(qū)中心醫(yī)院婦產科,上海 200090;2.南通大學,江蘇 南通 226019; 3.上海伊萊美醫(yī)療美容醫(yī)院整形美容外科,上海 200070;4.上海市楊浦區(qū)精神衛(wèi)生中心, 上海 200090)
疤痕子宮合并中央性前置胎盤是一種兇險性前置胎盤,通常情況下其圍手術期會有無法控制的大出血發(fā)生,嚴重威脅著母兒生命安全,目前已經有很多相關醫(yī)學研究報道了在兇險性前置胎盤大出血的情況下孕產婦死亡風險增加[1]。本研究探討了疤痕子宮合并中央性前置胎盤的圍手術期并發(fā)癥及處理措施,現報道如下。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選取上海同濟大學附屬楊浦醫(yī)院2014年1月至2017年1月收治的90例產婦,納入標準:所有患者均知情同意;排除標準:將缺乏完整臨床資料等患者排除在外。依據胎盤與子宮附著情況將這些患者分為胎盤植入組(n=30)、胎盤粘連組(n=20)和正常剝離組(n=40)三組。胎盤植入組患者年齡27~37歲,平均(32.61±4.12)歲;孕次1~7次,平均(4.13±0.34)次。在妊娠類型方面,28例為單胎,2例為雙胎;在產次方面,20例為1次,5例為2次,5例為3次及以上;在剖宮產次數方面,26例為1次,4例為2次,0例為3次及以上。胎盤粘連組患者年齡27~38歲,平均(31.05±4.66)歲;孕次1~7次,平均(4.07±0.98)次。在妊娠類型方面,18例為單胎,2例為雙胎;在產次方面,13例為1次,4例為2次,3例為3次及以上;在剖宮產次數方面,17例為1次,2例為2次,1例為3次及以上。正常剝離組患者年齡26~38歲,平均(31.29±4.40)歲;孕次1~6次,平均(4.01±0.12)次。在妊娠類型方面,37例為單胎,3例為雙胎;在產次方面,27例為1次,8例為2次,5例為3次及以上;在剖宮產次數方面,34例為1次,5例為2次,1例為3次及以上。三組患者的一般資料比較差異均不顯著(均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如果胎盤絨毛向子宮內1/2肌層植入,將子宮切除或活檢組織標本病理確診,則評定為胎盤植入[2];如果疑似胎盤很難和子宮壁分離,疑似胎盤植入,但是沒有經病理確診,即術中胎盤緊密粘連子宮,很難剝離,但是胎盤植入病理證據缺乏,則評定為胎盤粘連[3];如果術中自行娩出胎盤,或徒手剝離,具有完整的胎盤,較易將其和子宮肌層分離開來,則評定為正常剝離[4]。給予胎盤植入組患者子宮動脈栓塞術治療,具體操作為:放置導尿管。以腹股溝區(qū)為中心,消毒鋪巾。采用Selding’s方法,經皮股動脈穿刺。放置4F或5F動脈導管,經髂外動脈,腹主動脈至對側髂內動脈,用60%泛影葡胺行子宮血管造影,確認子宮動脈所在部位。超選擇性子宮動脈插管,確認導管已經插入子宮動脈。超選擇困難時亦可使用同軸微導管技術。經導管子宮動脈栓塞(transcatheter uterine artery embolization,TUAE)所使用的栓塞劑一般為聚乙烯醇(polyvingl alcohol,PVA)顆粒。其直徑150~700μm,使用量為100~700mg,平均為350mg。部分作者除使用PVA外亦加用鋼圈或明膠海綿,因PVA栓塞費用高,國內學者以真絲線段行栓塞術。顆粒用量以完全阻斷子宮肌瘤血流為度。栓塞后重復血供造影,當子宮動脈血流停止或造影劑開始向髂內動脈前支反流時停止注射,必要時造影重復至栓塞滿意為止。拔除導管,局部加壓包扎,患者平臥位24h,穿刺局部加壓沙袋6h,防止出現血腫,總曝光時間和次數應盡量控制在最小范圍,以減少X線對卵巢的照射。
1.3觀察指標
統(tǒng)計三組患者的術中出血、輸血、子宮切除發(fā)生情況,同時隨訪三組患者的母嬰結局。
1.4統(tǒng)計學方法
采用軟件SPSS 20.0分析數據,數據以(均數±標準差)的形式表示,組間比較用t檢驗。計數資料用例數(百分比)的形式表示,組間比較采用卡方檢驗,以P<0.05為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
2結果
2.1三組患者的一般資料比較
三組患者的一般資料比較差異均不顯著(均P>0.05),見表1。

表1 三組患者的一般資料比較Table 1 Comparison of general data among
2.2三組患者的術中出血、輸血、子宮切除發(fā)生情況比較
胎盤植入組、胎盤粘連組患者的術中出血量、圍手術期出血量均顯著多于正常剝離組(t值分別為4.303、3.182、2.776、2.571,均P<0.05),而胎盤植入組患者的術中出血量、圍手術期出血量又均顯著多于胎盤粘連組(t值分別為2.447、2.365,均P<0.05);胎盤植入組、胎盤粘連組患者的輸血率均顯著高于正常剝離組(χ2值分別為5.021、7.383,均P<0.05),但胎盤植入組、胎盤粘連組患者的輸血率之間的差異不顯著(χ2=0.13,P>0.05);胎盤植入組患者的輸血量顯著高于胎盤粘連組、正常剝離組(t值分別為2.447、2.365,均P<0.05),子宮切除率顯著高于胎盤粘連組、正常剝離組(χ2值分別為11.142、12.831,均P<0.05),但胎盤粘連組、正常剝離組患者的輸血量、子宮切除率之間的差異均不顯著(t/χ2值分別為1.533、0.300,均P>0.05),見表2。

表2 三組患者的術中出血、輸血、子宮切除發(fā)生情況比較Table 2 Comparison of intraoperative bleeding, transfusion and hysterectomy among three groups n(%)]
注:與胎盤粘連組比較,#P<0.05;與正常剝離組比較,*P<0.05。
2.3三組患者的母嬰結局比較
三組患者的羊水栓塞、心臟驟停發(fā)生率及死胎、新生兒窒息發(fā)生率、新生兒死亡率比較均無顯著性差異(均P>0.05),見表3。

表3 三組患者的母嬰結局比較[n(%)]Table 3 Comparison of maternal and infant outcomes among three groups[n(%)]
3討論
3.1疤痕子宮合并中央性前置胎盤概述
近年來,在世界范圍內,疤痕子宮再次妊娠引發(fā)的問題在不斷提升的剖宮產率的作用下日益突出,我國長期以來均具有較高的剖宮產率[5]。相關醫(yī)學研究表明,1975年、2010年剖宮產率分別為4.1%、20.7%,疤痕子宮胎盤植入發(fā)生率分別為1.16/1 000、2.37/1 000,后者均顯著高于前者[6]。相關醫(yī)學研究表明,和住院分娩總體前置胎盤發(fā)生率相比,疤痕子宮再次妊娠前置胎盤發(fā)生率顯著較高,發(fā)生這一現象的原因可能是子宮內膜在剖宮產術的作用下受到損傷,同時妊娠晚期胎盤向上遷移受到前次剖宮產手術疤痕的阻礙,從而極易引發(fā)前置胎盤[7]。子宮疤痕處較薄的內膜能夠為絨毛向宮壁肌層侵入提供良好的前提條件,因此疤痕子宮合并前置胎盤極易有胎盤植入發(fā)生[8]。
3.2疤痕子宮合并中央性前置胎盤的圍手術期并發(fā)癥及處理措施效果分析
在對盆腔手術出血進行控制的過程中,外科領域通常采用子宮動脈栓塞術。近年來,相關醫(yī)學學者在產科兇險型前置胎盤剖宮產術中出血的治療中應用了子宮動脈栓塞術[9-10],結果表明,其能夠對術中出血進行切實有效的控制。本研究結果表明,胎盤植入組、胎盤粘連組患者的術中出血量、圍手術期出血量均顯著多于正常剝離組(P<0.05),而胎盤植入組患者的術中出血量、圍手術期出血量又均顯著多于胎盤粘連組(P<0.05);胎盤植入組、胎盤粘連組患者的輸血率均顯著高于正常剝離組(P<0.05);胎盤植入組患者的輸血量顯著高于胎盤粘連組、正常剝離組(P<0.05),子宮切除率顯著高于胎盤粘連組、正常剝離組(P<0.05),和上述相關醫(yī)學研究結果一致。
術前準備充分、搶救及時、充分保證輸血、采用新技術可能對兇險型前置胎盤剖宮產大出血進行有效控制或將其有效消除掉,從而將孕產婦的死亡率降低到最低限度。但是,本研究樣本量較少,結論不具有代表性,需要相關醫(yī)學學者加大樣本進行進一步深入研究,全面評估其安全性、對出血的控制效果及母嬰遠期預后等。
總之,疤痕子宮合并中央性前置胎盤患者圍手術期具有較高的胎盤植入發(fā)生率,子宮動脈栓塞術能夠對出血進行有效控制,值得在臨床推廣使用。
[1]張學美.瘢痕子宮合并前置胎盤的分娩結局探討[J].中國社區(qū)醫(yī)師,2015,31(4):63-64.
[2]范翠芳,孫艷梅,董蘭,等.前置胎盤伴疤痕子宮的母嬰結局——附253例臨床分析[J].重慶醫(yī)學,2015,44(7):946-948.
[3]陳艷雅.瘢痕子宮合并前置胎盤的高危因素與臨床危害[J].臨床醫(yī)學工程,2015,22(2):170-171.
[4]方有珍.疤痕子宮合并前置胎盤的分娩結局分析[J].西南軍醫(yī),2014,16(2):155-156.
[5]李靜文,楊曉紅.宮腔鏡下滾球電極去除子宮內膜治療月經過多合并嚴重內科疾病35 例臨床分析[J].醫(yī)學綜述,2014,20(9):1683-1685.
[6]Vervoort A J,Uittenbogaard L B,Hehenkamp W J,etal.Why do niches develop in Caesarean uterine scars? Hypotheses on the aetiology of niche development[J].Hum Reprod,2015,30(12):2695-2702.
[7]Schepker N,Garcia-Rocha G J,von Versen-H?ynck F,etal.Clinical diagnosis and therapy of uterine scar defects after caesarean section in non-pregnant women[J].Arch Gynecol Obstet,2015,291(6):1417-1423.
[8]Dash S,Panda S,Rout N,etal.Role of fine needle aspiration cytology and cell block in diagnosis of scar endometriosis: a case report[J].J Cytol,2015,32(1):71-73.
[9]Thomas A,Rebekah G,Vijayaselvi R,etal.Measurements of the lower uterine segment at term in women with previous cesarean delivery[J].Open J Obstet Gynecol,2015,5(11):646-653.
[10]Ryo E,Sakurai R,Kamata H,etal.Changes in uterine flexion caused by cesarean section: correlation between post-flexion and deficient cesarean section scars[J].J Med Ultrason (2001),2016,43(2):237-242.
[專業(yè)責任編輯:馬良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