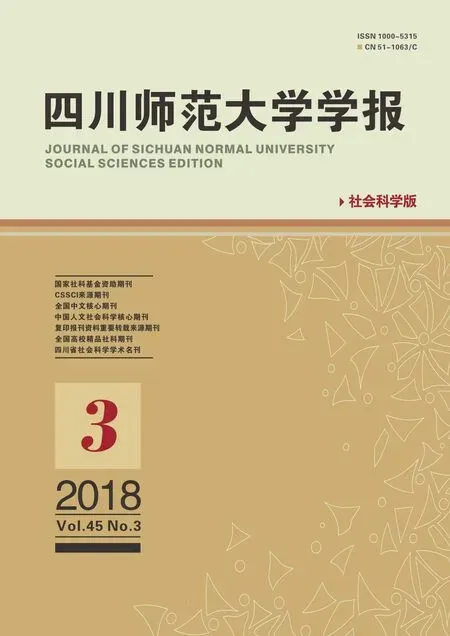“《芳華》暨青春記憶電影發展走向研討會”綜述
(四川師范大學 影視與傳媒學院,成都 610066)
今年是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導下,我國進入了一個新時代,中國電影的批評和創作也進入了一個新時代。2018年1月10日,由北京師范大學亞洲與華語電影研究中心、四川師范大學影視與傳媒學院聯合主辦的“《芳華》暨青春記憶電影發展走向研討會”在成都舉行。本次研討會是2018年全國范圍內第一場跨地域的電影學術研討會,10余位專家學者圍繞“《芳華》暨青春記憶電影發展走向”的論題,從如下幾個角度展開了熱烈討論。
一 平民視角與真實性凸顯
影視作品需要靠近生活、靠近現實,用微觀視角來講述故事。青春記憶電影只有真正做到“源于生活”,才能讓每一位觀眾能夠在影片中找到精神與情感的共鳴。電影《芳華》正是這樣一部用平民視角,折射和放大生活真實的影片。
北京師范大學周星教授指出,電影《芳華》中每一個人物命運交織到一起,沖突極具張力與感染力,導演馮小剛導出了社會性的真實。看電影《芳華》似乎覺得平淡而不緊張——其實是馮小剛前所未有的安寧收斂佳作,對于歷史、對于生活的回歸真實感知,對于青春、對于愛戀的浪漫優美的憂傷表現,對于男女際遇、對于成長遭遇的如真把握。偶爾的無法抑制的嫉惡如仇爆發卻即刻隱忍的張力,難免的善良遭嫉、有意無意的傷害都如常冷靜表現,歷史不幸也不動聲色地展示,一個動人卻不主觀煽情的電影,值得回味。
中央戲劇學院電影電視系主任路海波肯定了導演馮小剛的系列作品都體現了情懷與擔當。電影《芳華》以部隊文工團為背景,不回避人性的丑陋,體現出對現實的高度關注。《芳華》中各個人物的心路軌跡與命運走向,投射到今天現實生活中來,應該引起現實中你我他的自我解剖、質疑與思考。
四川師范大學影視與傳媒學院副院長陳佑松在發言稿《〈芳華〉與馮小剛的“新左”視角》中提到,《芳華》體現了馮小剛作品一貫的“新左”立場。所謂“新左”,既反對新自由主義放任市場經濟所帶來的階層分化加劇,也不贊同激進左派的階級斗爭理論。馮小剛的作品一直在尋求國家和個體之間的平衡與協商。馮小剛的電影都采用平民視角,塑造個體的小人物,呈現著日常生活的質感,同時并不把個體與國家相對立,而是承認社會主義的集體傳統對個體命運的型塑意義。《芳華》也是如此,他的主人公仍然是平民出身,有著日常的喜怒哀樂和人性欲望,但是他們最為直觀的生活世界卻是由中國當代的重大歷史階段——“文革”、越戰和改革開放塑造的。
二 思想情懷與人性描摹
近年來,國產青春片如《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同桌的你》等都講述關于特定年代的青春故事,但這些電影同質化現象較嚴重,缺乏對青春深層次的思考。電影《芳華》讓思想情懷不再缺席,而且有力地勾勒出人性的畫卷。
中國戲曲學院戲文系主任謝柏樑認為,《芳華》體現了美與丑、善與惡、人格的完美和天性的呈現,這些出身草莽但卻善良高貴的人們,與無數在戰爭中奉獻乃至犧牲的年輕戰友一樣,與那些一度在特定社會語境下不夠完美的文工團團員們一樣,同樣撐起了中國的脊梁。
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教授、四川省電影家協會副主席曹峻冰在《〈芳華〉:歷史文化與人性本真的抵牾與救贖》一文中用阿爾都塞意識形態理論的批評視閾審視影片《芳華》。他認為,基于影片的顯在表征和無意識“癥候”,指出影片《芳華》還有一個潛在的本文,即其是中國半個世紀歷史文化的縮影,也是由禁錮、保守到開放、自由的人的靈魂的進步史。
四川師范大學影視與傳媒學院院長駱平從自然主義、存在主義角度解析了國產青春電影女性形象。自然主義把人歸結到同一公式,為遺傳、環境和時代壓力所控制的生物。存在主義強調在敵對、冷漠的大千世界中個人經歷的獨特性和孤獨,視人類的生存為不可解釋的,強調選擇的自由和對自己行為的后果負責。《芳華》中女主人公何小萍,一個孤獨者,就是快要被環境、時代壓力控制的人物,卻明顯帶有存在主義的反叛色彩,這體現了國產青春電影中女性形象,是由自然主義向存在主義的轉變。
南京理工大學設計藝術與傳媒學院傳播與傳媒研究發展中心主任孫宜君認為,馮小剛用冷峻的筆觸與鏡頭表現人物,讓群體中的孤獨者透過偽善窺視人性之惡,也顯示了人性之美。
三 美學期待與人文溫度
電影《芳華》中,每一幀畫面色彩濃麗、鮮艷,給人以年代感和美的享受。眾所周知,中國電影美學的建設于20世紀80年代初正式起步,而中國電影美學不僅要借鑒西方電影美學的經典部分,也要融入中國元素,彰顯中國本土文化特色,同時要注重把握受眾觀影的期待審美心理,恰當提升影片人文性,讓人文溫度升溫,才能創作出真正吸引和打動受眾的優秀之作,造就經典。
北京電影學院教授王志敏認為,電影的理論界和創作界都有對于美學的期待。他提出了關于美的兩個特點:一是可接受性;二是美是具有召喚結構。他說,馮小剛可以說是審美召喚的大師,編劇嚴歌苓也是,而類型本身也具有召喚的力量。針對美國職業評論者用煽情和濫情來評論《芳華》的情況,他認為,中國電影不但能召喚中國觀眾而且能召喚國際觀眾,才能從電影大國走向電影強國。
西南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劉廣宇認為,時下對《芳華》的評價更多超越了影片本身,而成為了對穿越幾個時代的一代人的歷史記憶、社會切片和文化癥候的閱讀。他認為:(一)以《芳華》為代表的這樣一種回溯式的影像文本與以《楓》為代表的那樣一批剛剛從“文革”中過來的影像表述與反思,可以形成一種穿透歷史的互文性比較研究;(二)以《芳華》為代表的所謂“好人敘事”,其實正是當下社會對“好人”的集體無意識召喚;(三)但這種“召喚”還遠未達到某種程度的“自覺”,也正是由于缺乏更高的審美引領與價值標尺,使《芳華》難以成為一部經典作品。這無論從其人物塑造、戲劇橋段、細節展示等,均可見出其內涵的缺失。
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張燕認為,影片《芳華》之于2017年中國電影的意義,類似于《出租車司機》之于2017年的韓國電影,這是一部由個體見社會、由情懷現銳度的銀幕時代青春悲歌,具有深刻的現實主義批判色彩。借助文工團這一載體,影片悄然切入至今諱莫如深的特殊時代,貫穿起革命理想被肆意壓抑扭曲的國家時代、戰爭年代與個體生命情感飽經滄桑、被無情摧毀的芳華命運。該片盡管前后敘事存在一定的斷裂感和不圓潤、服飾設計與歷史還原也有不足,但瑕不掩瑜,仍算是一部有銳氣、有溫度、有思考力和穿透力的電影。
四川大學藝術學院副教授賈立強從影片《芳華》的細節處入手,在發言稿《〈芳華〉的劇作細節與人文內蘊》中提出應增加影片人文真摯度的觀點。他認為,文學影視藝術是人類藝術中最后的堡壘,那么,影視藝術作品應該具有更多的真摯度,才能體現有情懷有溫度的人文性。
四 構筑聚合力與發展空間
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楊俊蕾在《〈芳華〉民間立場分化的偽救贖》中提出,《芳華》的吸引力和它所激發的熱議如此高漲,首要緣由在兩方面:其一是電影行業內部“大導演定律”使然;其二則是《芳華》選取現實題材,深深觸動當代觀影者的共和國記憶。她所期盼的大導演進行共和國記憶表達,是像《一九四二》那樣堅定地回到民間立場,沉郁而滄桑地推進多視角歷史表達,使作品具有當代文化重構的作用,并在藝術感召中增加中國人的情感聚合力。
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裴亞莉在肯定電影《芳華》的同時,也期待導演馮小剛在未來的創作中能夠做到:(一)加強對人物形象及其精神成長過程的塑造,讓故事在發展中完成,讓人物在實際生活境遇中落腳;(二)應該有正確的歷史觀,讓人物行為有基本的歷史真實性的依據;(三)要努力升華作品的價值導向,讓電影確實成為為觀眾提供精神食糧的藝術產品。
浙江傳媒學院教授項仲平認為,《芳華》的拍攝和發行體現了時代的進步:一是導演對小說處理把握分寸巧妙和得當;二是對整個故事人物細節刻畫的用心;三是音樂的渲染和強化更是神來之筆。影片《芳華》值得我們電影評論者去探究,也值得留存于中國現代電影史上。
陜西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牛鴻英在發言稿《收編與抵抗之間:電影〈芳華〉的話語建構分析》中從文化研究角度認為:(一)面對電影《芳華》,以好萊塢商業類型片為適用對象的傳統敘事理論和經典電影理論已經失去了解釋的效力;(二)影片缺乏飽滿的人物形象和情感邏輯,敘事的緊密度也不夠,只給出了人物類型化的群像;(三)從文化研究的立場上看,影片凸顯了性別、階層、權力等深層話語邏輯,對女性身體的景觀消費,對不同社會階層的命運呈現,使得作品具有了大眾文化的抵抗性和批判性特征;(四)影片一方面繼續了馮小剛電影的小人物立場,另一面又挑戰了當代中國戰爭的敏感題材,具有很大的社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