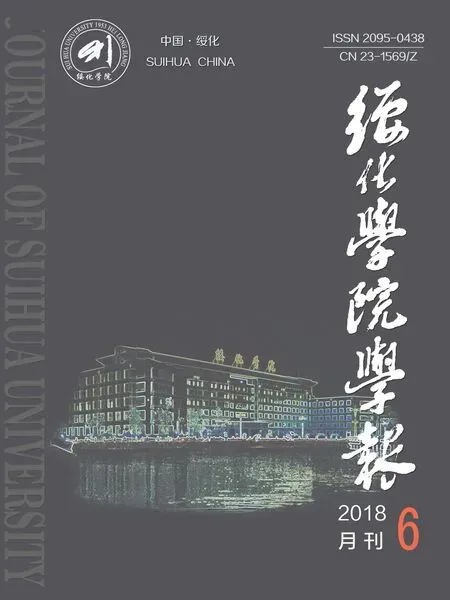鄉關何處:城市化語境下的鄉土文學創作走向
寇國慶 倪相群
(1.蚌埠學院;2.蚌埠第一中學 安徽蚌埠 233030)
最早給鄉土文學下定義的是魯迅。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導言》中他說:“蹇先艾敘述過貴州,裴文中關心著榆關,凡在北京用筆寫出他的胸臆來的人們,無論他自稱為用主觀或客觀,其實往往是鄉土文學,從北京這方面說,則是僑寓文學的作者。”[1]顯然,魯迅所指的這一類作家的創作多與故鄉的鄉土情感相關。
其實,從創作者來看,是從外圍俯視鄉土,以文人、知識分子帶著有色眼鏡來看鄉土,把鄉土作為批判亦或頌揚傳統文化;或是寄托人性的烏托邦,還是政治風向的試驗場,這些創作中的“鄉土”都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鄉土。早在20世紀30年代鄉土文學就已經暴露出的問題,茅盾就指出:“關于‘鄉土文學’,我以為單有了特殊的風土人情的描寫,只不過像看一幅異域圖畫,雖能引起我們的驚異,然而給我們的,只是好奇心的饜足。因此在特殊的風土人情而外,應當還有普遍性的與我們共同的對于運命的掙扎。一個只具有游歷家的眼光的作者,往往只能給我們以前者;必須是一個具有一定的世界觀與人生觀的作者方能把后者作為主要的一點而給與了我們。”[2]真正的鄉土創作不應該用旁觀者的視野,用獵奇、俯視的眼光來看待鄉土、鄉村、鄉民對鄉土文學創作來說,就顯得尤為重要。
一、時代巨變語境中的鄉土文學
整個20世紀的中國社會是一個古典社會、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現代社會的過渡,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造就了傳統鄉土社會加速瓦解,人與人之間,傳統的宗法的、血緣的、地緣的紐帶日益松散,就像馬克思所講的那樣,一切堅固的都煙消云散了。這一急劇的時代變遷給鄉土文學創作的影響是深遠的,考查他們精神、情感上的困惑、糾結、探索,無疑是這個時代的精神記錄與追問。
建國前后,趙樹理、柳青圍繞農村、農業、農民的生存發展而創作的一系列的作品生動鮮活地記錄了社會變遷,文革時期浩然的創作盡管多有詬病,也不失時代風云的折射。
20世紀80年代,陜西作家路遙的小說多以改革時代為背景,描繪時代巨大變遷中城鄉的社會生活和人們情感變化,代表作《人生》《平凡的世界》中既有時代陣痛下的黃土高原古樸的道德風尚、生活習俗的懷戀,也有作者對生活、對人生、對社會、對歷史的深刻思考。賈平凹早期圍繞底層鄉民的“商州系列”著力于宏大背景下描述社會轉型時期人性的變化,新時期以后的《秦腔》《帶燈》等長篇小說,關注當下時代巨變給傳統鄉土社會帶來的精神與情感方面的震撼。而另外一位陜西作家陳忠實則以他的史詩般的鴻篇巨制《白鹿原》探究民族秘史。當代河南作家多以中原大地為血緣紐帶,這其中劉震云、閻連科、李佩甫、李洱的創作有著濃重的“鄉土”情節,在表現內容與手法上也進行了創新與探索。劉震云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對對“故鄉”探索的系列作品《故鄉到處流傳》《故鄉面和花朵》《我叫劉躍進》《一句頂一萬句》《我不是潘金蓮》,既有對當下的鄉村社會時代巨變下的利益沖突與情感糾葛的展示,也有對鄉土社會孤獨個體生命體驗的洞察。被譽為“荒誕現實主義大師”閻連科在《受活》《丁莊夢》等一系列作品中,虛構各種超現實的荒誕故事強烈的黑色幽默往往令讀者哭笑不得,情節荒唐夸張,帶有滑稽劇色彩,折射了現實中鄉村農民的苦難與抗爭。李佩甫90年代以后的《羊的門》《李氏家族》描繪了厚重鄉土文化中的不同歷史階段的人性的幽暗與現實權謀。李洱的《石榴樹上結櫻桃》再現了的農村基層競選中基層干部的人性所遭受的扭曲與痛苦。河南的優秀作家還很多,厚重的中原文化給了他們源源不斷的精神滋養,也使他們的作品更能夠展現當下鄉土社會的真實。山東作家莫言用他的一系列關于高密鄉的歷史與現實的言說,描繪了一個神秘、野性的故鄉。張煒對九月大地的深情擁抱,在在展示大地的博大與多情。另外,曹乃謙《到黑夜想你沒辦法——溫家窯風景》、葛水平的《喊山》、張學東的《堅硬的夏麥》等等揭示了北方鄉民的面朝黃土背朝天的鄉民們生活的原始殘酷與堅韌執著。
二、現代語境下鄉土文學存在的問題
不容置疑,在新的世紀,城市化的速度日益加快,城鄉距離拉大,市民與農民在物質財富有著明顯的差距,因此,許多鄉土小說著重描繪了農民在物質財富落差下的心態失衡,以及進城脫離鄉土進城后一段適應期間的艱難。這些作品有:陳應松的《馬嘶嶺血案》、阿寧的《米粒兒的城市》、吳玄的《發廊》、林白的《去往銀角》、巴橋的《阿瑤》等等,但我們也應該看到,城市文明相對于鄉村文明來說,給了農民給多的回饋、更多的機會、更多的選擇自由。如果看不到這些進步的方向,一味地譴責城市文明,顯然缺乏歷史意識。
描繪鄉村權力的暴虐在很多作家作品中都可以找到,這對于鄉村的政治建設、民主建設都有著借鑒意義,然而,如果看不到鄉村政治建設、民主建設的進步,顯然不能夠真實地表現鄉村。畢飛宇的小說《玉米》系列、劉慶邦的《家園何處》、陳應松的《神鷲過境》、胡學文的《命案高懸》、杜光輝的《浪灘的男人和女人》都描寫了鄉村政治權力建設中出現的弊病。此外,這類作品還有葛水平的《涼哇哇的雪》、尚志的《海選村長》、梁曉聲的《民選》、曹征路的《豆選事件》、陳中華的《七月黃》、荊永鳴的《老家》等等,描述了剔除鄉村舊有的封建落后的思想與勢力的艱難。燕華君的《麥子長在田里》、向本貴的《泥濘的村路》、閻連科的《白豬毛黑豬毛》、秦人的《誰是誰的爺》艾偉的《田園童話》、張繼的《清白的紅生》等等描繪了鄉村中處于弱勢群體的女性所遭受道德傷害,從而揭示鄉土社會、鄉土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亟需改造的必要性。
當下的中國“城市化”造就了農村人口向城市聚集,城市文明對傳統鄉土文明的擠壓,作為一種文化現象業已影響和滲透到鄉土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特別是20世紀代以后,市場化、城市化加快,在這樣的化語境下,重新審視鄉土文學創作,批判對鄉土、鄉村、鄉民錯誤的情感認知,才能夠為鄉土文學的健康發展提供建議。
對于鄉土、鄉村的衰敗,深受傳統文化浸潤的人文知識分子顯然會有更多的懷戀,進而對現代文明持更為苛刻的情感態度,上個世紀30、40年的沈從文可以是個代表。沈從文心儀的是可供奉人性的“希臘小廟”的鄉土。在1942年他為《長河》所寫“題記”:“一九三四年的冬天,我因事從北平回湘西……去鄉已經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最明顯的事,即農村社會所保有的那點正直素樸人情美,幾幾乎快要消失無余,代替而來的卻是近二十年實際社會培養成功地一種唯實唯利庸俗人生觀。”接下來,他慨嘆:“‘現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可是具體的東西,不過是點綴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輸入……”[3]城市文明在發展過程中可能給人造成了很多不適應,有很多不足,如果一味地加以否定,顯然是帶上了有色眼鏡。
還有一些作家,犯了民粹主義的錯誤,把鄉土、鄉村、鄉民賦予過多的道德色彩,這也是要不得的。就有學者指出,張煒在《九月寓言》中將人與土地連接起來凸顯出來的民粹意識,這種意識源于舊俄時期的民粹主義的“土地性——人民性——道德性”[4]的思維方式在我國知識分子里同樣具有廣泛的市場,張煒的道德體系的建構在既通純潔“血緣”的同時,又接上了“人民”的“地氣”。《古船》中隋抱樸最后明白的道理就是“要緊的是和鎮上的人在一起。……老隋家人多少年來錯就錯在沒和鎮上的人在一起”。在張煒的審美理想中,“人民”成為一種理想的尺度。“說到獎賞就不能不想到‘人民’,不是抽象的想,而是具體地、真切實在地想。一個作家的勞動幫助了他所處那個時代的、或后來時代的人民,他應該由喜悅到興奮到忘情,獲得無邊的快樂。”[5]鄉土、鄉村、鄉民并不必然在道德方面具有天然的免疫力,鄉土文學作家如果看不到這一點,不利于鄉土文學的發展,也不利于社會文化的建設。其實我們更應該在現代都市中發現未來意義,“城市環境的最終產物表現為它所培養出的各種新型的人格。”[6]
三、鄉關何處——鄉土文學的追問
盡管鄉土社會可能已漸行漸遠,鄉土文學也逐漸失去土壤,在城市化、現代化的語境下,鄉土文學的未來必須是處理好鄉土、鄉村、鄉民與城市關系的問題。
確實,在城市化、市場化語境下,傳統的鄉土正在遭受現代城鄉文明的擠壓,在這一過程中,對傳統鄉土農業文明懷戀的人文知識分子作家來說,現實對情感的沖擊肯定是巨大的。當然,作家可用在這一歷史進程中,留下歷史發展的感性記憶,正如賈平凹所說:“社會發展到今日,巨大的變化,巨大的希望和空前的物質主義的罪孽并存,物質主義的致愚和腐蝕,嚴重地影響著人的靈魂,這是與藝術精神格格不入的,我們得要作出文學的反抗,得要發現人的弱點和罪行。”[7]作家們注定要把這急劇變化的時代變遷與情感激蕩記錄下來。由此,賈平凹在《秦腔》中寫道:“我以清風街的故事為碑了,行將過去的棣花街,故鄉啊,從此失去記憶。”[8]因此,《秦腔》被有些人稱為“鄉土敘事的終結”。賈平凹運用了“密實的流年式的敘寫”寫了“一堆雞零狗碎的潑煩日子”,[9]賈平凹以極大的激情記錄了作為最具代表性的秦川文化的秦腔面對市場經濟的發展所做的應對與抗爭。
對于作家來說,同樣重要的是,擺脫先入為主地對城市做出的單一的道德判斷,超越二元對立思維,緊緊地擁抱大地,追問生命的終極意義。新疆作家劉亮程在廣漠的西北土地上,感受到大自然、大地,體味大地與鄉土的恒久綿長,因此有學者曾經感嘆:“10年前我讀了他的《一個人的村莊》,認為在鄉土的廣度、深度和細部上都充溢著生命感,大地——鄉土上的人,牲畜和莊稼消失了一茬又一茬,甚至城市也可能消失,但大地鄉土仍在,這就是永恒的力量,就是永恒。”[10]余秋雨的文化鄉土創作同樣也是鄉土文學創作的有益探索,在散文《信客》《夜航船》《牌坊》《老屋窗口》《酒公墓》中有童年度過的青蔥回憶,鄉親們艱辛的謀生和對故鄉的眷戀,《鄉關何處》則挖掘故鄉淵源的文化價值。
費孝通《鄉土中國》中描繪了鄉土中國的“差序格局”“禮制秩序”“長老統治”,這些儒家文化最為核心的內容正在遠去,在高速城市化和現代化的中國,今天的鄉村無論從內容還是形式上早已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鄉村。鄉土文明作為文化記憶與審美理想可能仍然對中國人當下生活與未來愿景產生深層的重要影響,仍將是中國悠久文化的根基,但鄉土社會秩序與鄉土文明最終也許只是會成為我們不變的鄉愁。
[1]魯迅.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M].上海:文藝出版社,1953:78.
[2]茅盾.關于鄉土小說[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93.
[3]沈從文.長河題記[N].重慶《大公報》“戰線”副刊971期(1943-4-23).
[4]劉小楓.圣靈降臨的的敘事[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8:107.
[5]張煒.心上的痕跡,綠色的遙思[M].上海:文匯出版社,2006:122.
[6][美]R·E.帕克等、宋俊嶺等譯.城市社會學—芝加哥學派城市研究文集[M].北京:華夏出版社,1987:5.
[7]賴大仁.魂歸何處———賈平凹論[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0:128.
[8]賈平凹.《秦腔》后記[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9]周媛,賈平凹.我要為故鄉樹塊碑[N].西安晚報,2005-02-23.
[10]李伯勇.植根大地寫作的精神向度——關于“大地寫作”的話題[N].文藝報,2012-1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