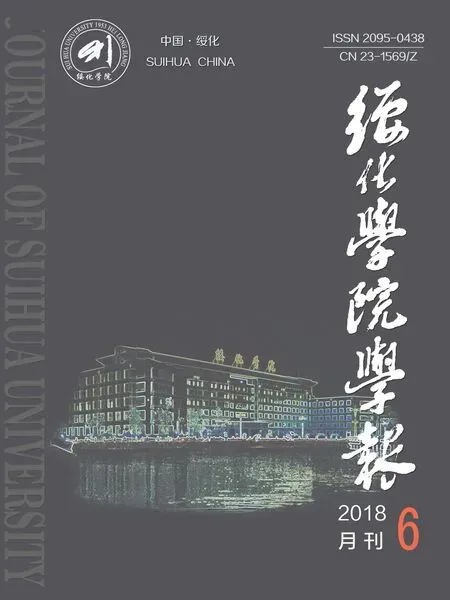《三個叛逆的女性》對《玩偶之家》的借鑒與超越
牟 艷
(重慶師范大學文學院 重慶 401331)
郭沫若的《三個叛逆的女性》與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可謂是戲劇史上以女性獨立解放為題材的雙璧。目前學界對于兩部作品的研究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類觀點以劉華東[1]和鐘翔[2]為代表,他們單純地關注到易卜生對郭沫若戲劇創作的影響,進而分析了兩部作品的關聯性與差異性。第二類觀點以陳鑒昌為代表,他寫作的兩篇論文《郭沫若易卜生筆下的“娜拉”比較》[3]和《郭沫若易卜生的娜拉形象意義比較》[4],立足于《三個叛逆的女性》和《玩偶之家》兩個作品,比較兩部作品中娜拉形象的異同。這類觀點單方面從形象角度進行對比分析。第三類觀點以張柏柯[5]為代表,他選取了《三個叛逆的女性》中的《王昭君》與《玩偶之家》進行對比,僅分析了兩部作品中主要人物的共性與個性。綜上可之,學術界都注意到了《玩偶之家》與《三個叛逆的女性》之間的關系,也看到了易卜生對郭沫若創作的影響。那么,郭沫若的《三個叛逆的女性》從易卜生《玩偶之家》的戲劇創作中具體借鑒了什么呢?他在借鑒易卜生戲劇創作時,是否顯示出了自己的創作風格呢?
20世紀初,日本和中國先后掀起易卜生熱。1909年文藝協會和自由劇場紛紛上演易卜生的戲劇。在國內,1908年魯迅在《摩羅詩力說》和《文化偏至論》中對易卜生大力推崇。1914年春柳社陸鏡若在《俳優雜志》第一期(1914年)上發表了《伊蒲生之劇》,將易卜生的戲劇引進中國。1918年,《新青年》上刊出了“易卜生專號”,“易卜生主義”開始成為中國追求社會變革的思想火炬。胡適在《易卜生主義》中,大力推崇易卜生的社會改革精神。20世紀初,無論是日本還是中國,對易卜生都燃起了一股熱潮,郭沫若的《三個叛逆的女性》(《卓文君》《王昭君》《聶嫈》)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相繼誕生。
郭沫若1926年結集出版的《三個叛逆的女性》深受易卜生《玩偶之家》的影響。1920年,郭沫若談到他在日本留學時“一天到晚踞在樓上只是讀文學和哲學一類書……還有好些易卜生的戲劇”[6](P85)。同一年,郭沫若在與摯友宗白華、田漢的通信中也積極地討論了易卜生的戲劇[7](P87)。郭沫若對易卜生戲劇的閱讀與思考,為創作《三個叛逆的女性》打下了堅實基礎。1942年,郭沫若談到《三個叛逆的女性》時認為:“很鮮明的又有易卜生和王爾德的模仿。”[8](P118)1956年,阿英提到:“郭沫若戲劇中滲透易卜生式的現實主義和王爾德式的唯美主義的雙重成分。”[9](P742)在《寫在〈三個叛逆的女性〉后面》一文中,郭沫若本來想將《蔡文姬》合在前兩個組成一個三部曲,并說道:“在我看來,我的蔡文姬完全是一個古代的‘諾拉’(通譯娜拉)。”[10](P143)也就是說,郭沫若本人是把他筆下的卓文君、王昭君和蔡文姬同易卜生筆下的娜拉相類比。可以說,郭沫若在創作《三個叛逆的女性》時確實受到了《玩偶之家》的影響。這種影響主要體現在《三個叛逆的女性》對《玩偶之家》的創作主題、人物形象及藝術特色的借鑒。在此基礎上,《三個叛逆的女性》也體現出郭沫若獨有的藝術氣派和風格特色。
一、對主題的借鑒與超越
(一)《玩偶之家》的創作主題。易卜生在創作《玩偶之家》時,歐洲正在進行社會關系改革。他看到婦女在家庭中依附于男性的現象,以朋友勞拉的真實故事為原型,創作了這部作品,希望以此揭露資產階級社會中擁有特權的男性自私虛偽的本質。在這樣的社會背景和創作意圖下,《玩偶之家》的主題也呈現出多元性。
首先,《玩偶之家》體現出資產階級社會中金錢至上的關系。作品中科洛斯泰責備林丹太太時就說道:“總之一句話——一切都是為了錢。”[11](P178)此外,當海爾茂知曉娜拉冒名借錢養病,而這件事會威脅到自己的身份榮譽時,他開始責備、辱罵娜拉,并認為“我這場大禍都是一個下賤女人惹出來的”[11](P192)。海爾茂對娜拉態度的急轉,體現了在資產階級社會中,金錢利益至上導致的人性扭曲。
其次,《玩偶之家》體現了易卜生對女性成為自由的“人”的追求。德國文學批評家路·莎樂美曾提到:“‘自由’的挪威,他(易卜生)認為里面住著不自由的女人和男人。”[12](P24)在整個《玩偶之家》中易卜生希望女性能夠真正實現自我價值,成為擁有自我權利的“人”。無論是林丹太太獨立自主的思想,還是娜拉的吶喊:“首先我是一個人,跟你一樣的一個人。”[11](P199)“你不受我拘束,我也不受你拘束,雙方都有絕對的自由”[11](P202),都是為了倡導女性成為自由的“人”。
最后,《玩偶之家》中可以看出易卜生對女性問題的關注。一方面,他發現了社會中女性權利缺失的問題。在戲劇中,娜拉身為一個成年人,想要借債卻沒有資格,只得模仿父親的簽名去借債,這反應了易卜生對當時社會中女性地位低下的控訴。另外一方面,易卜生也注意到了家庭關系中女性對男性的依附。娜拉自己也說道:“在這兒我是你的‘泥娃娃’老婆,正像我在家里是父親的‘泥娃娃’女兒一樣。”[11](P197)因此,易卜生塑造了一個出走的娜拉形象,進一步鼓勵婦女積極爭取獨立的人格,追求嶄新的生活。
(二)《三個叛逆的女性》的創作主題。在《寫在〈三個叛逆的女性〉后面》一文中郭沫若明確指出:“我在歷史上很想找個有為的女性作為具體的表現,我在這個作意之下便作成了我的《卓文君》和《王昭君》”[10](P138),郭沫若有意將這兩部戲劇作為“在家不必從父”“出嫁不必從夫”的典型。本來按照郭沫若原意是要將蔡文姬作為“夫死不必從子”的典型進行創作,此時卻發生了慘絕人寰的五卅慘案。親眼目睹這一慘案的郭沫若便創作了《聶嫈》,將聶嫈作為革命叛逆女性的典型與卓文君、王昭君共同結集合成“三個叛逆的女性”。因而,郭沫若塑造的三個叛逆的女性形象是“有意而為之”,其主題也呈現出鮮明性、深刻性。
《三個叛逆的女性》體現了黑暗的封建社會中,金錢利益對人的驅使。《卓文君》中卓王孫說道:“世間上除了金錢之外,那一樣事情辦得到?”[10](P36)為了使得自己的金錢地位得到鞏固,他極力阻礙司馬相如與卓文君的愛情,而把女兒嫁給程鄭之子。《王昭君》中毛延壽只看別人送給他的賄賂多少畫畫,他為了金錢丑化了王昭君的畫像。即使在王昭君母親瘋了的同時,毛延壽還在不斷派龔寬和女兒毛淑姬去壓迫王昭君給自己行賄。在《聶嫈》第二幕中,衛士和士長們更是為了拿到聶政的賞錢自相殘殺。
《三個叛逆的女性》最集中探討的主題就是張揚“三不從”原則,對封建制度和封建禮教進行抨擊。當卓文君吶喊出“我不相信男子可以重婚,女子變不能再嫁!我的行為我自己問心無愧”[10](P56)時;當王昭君對漢元帝控訴出“你為滿足你的淫欲,你可以強索天下的良家女子來恣你的奸淫!”[10](P56)時;當聶嫈用自己的性命使得使天下后世的暴君污吏能夠以此為警戒時,她們作為“人”的意識開始覺醒,看到自己所處的地位的不平等,并對這種現狀進行吶喊,想要以此提高婦女的社會地位。三個戲劇中最精彩的部分無疑是這些女性認識到自己的地位之后的反抗行為,她們雖身處不同環境的壓迫,仍均以自己的方式去進行反抗。卓文君以私奔的方式來回應封建父權,王昭君用遠赴窮荒極北的塞外地域來蔑視夫權,聶嫈以自己的生命去證明哥哥聶政的身份,進一步諷刺高高在上的封建王權。
(三)創作主題的同中之異。縱觀易卜生《玩偶之家》和郭沫若《三個叛逆的女性》,兩者都是以“對婦女地位探討,期望實現婦女解放”為其創作主旨。兩位戲劇家在創作戲劇時都對原有的事實做了更改,易卜生把勞拉進精神病院改成了娜拉大膽走出家庭,尋求自我獨立。郭沫若則大膽更改了王昭君在古典詩詞中“我本漢家子,將適單于庭。辭訣未及終,前驅已抗旌”[13](P90)的悲劇形象,將王昭君塑造成一個強烈的反抗意識和自我意識的女性,兩個戲劇家筆下的人物形象都有作為人的自我意識覺醒的描寫。而兩個戲劇家均以女性作為描寫對象,書寫出她們的覺醒與叛逆,更進一步強調了女性的主體意識覺醒。
但是,在他們近乎相似的創作意圖中又有著不盡相同的一面。易卜生在創作《玩偶之家》時表現了對婦女命運的關切,指出了婦女在家庭生活中只能像“玩偶”一樣處于依附地位的現實,易卜生對婦女的關切點主要著眼于家庭生活方面。郭沫若在吸收易卜生思想觀念的同時,把對婦女問題的關切進一步擴展:“在家不必從父,出嫁不必從夫,夫死不必從子”。這“三不從”對婦女問題的探討不僅擴展到了社會,還有國家,遠遠地從家庭范圍中延伸了出來。易卜生創作此劇時提出了促進婦女解放的問題,但是怎樣才能使婦女獲得解放易卜生并未給出答案。對于這個問題,郭沫若在《〈娜拉〉的答案》中寫道:“關于這個問題的答案,易卜生并沒有寫出什么,但我們的先烈秋瑾是用生命來替他寫出了。”[14](P307)郭沫若用秋瑾作為例子,認為答案就是逃離的娜拉不僅在精神上實現獨立,在行動上也實現了獨立。郭沫若把女性與社會革命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在《聶嫈》中,盡管郭沫若沒有實現第三個不從的意圖,卻為從家庭中逃離出來的娜拉給出了答案。在五四運動興起的時代,逃離家庭的無數個“娜拉”積極參加婦女解放運動,爭取革命的勝利,做一個像“聶嫈”一樣無畏的女戰士。對比《玩偶之家》與《三個叛逆的女性》可以知道,兩者創作意圖最大的不同之處在于其女性解放程度的差異。郭沫若在中國啟蒙運動環境下徹底揚起“女權主義”的旗幟,易卜生只是對資產階級家庭中不公平的婦女地位吶喊。相對于易卜生而言,郭沫若對中國幾千年封建制度的壓迫下的女性現狀提出更加強力的吶喊,召喚女權主義的到來!
二、對人物形象的借鑒與超越
(一)西方娜拉與中國娜拉。易卜生筆下的西方“娜拉”從一出場就以單純善良、樂于助人、熱愛丈夫的形象出現。這個形象在她和海爾茂的關系中得到了很好的體現:為了挽救丈夫的生命,偽造保人簽字去借債。她天真執著地愛著自己的丈夫,當柯爾斯泰要挾他準備詆毀海爾茂的名譽時,她甚至想要用生命來維護丈夫海爾茂。可當海爾茂知道事情真相后反而責備她,娜拉終于認清了自己在家庭中的“玩偶”地位。她開始覺醒并毅然選擇了走出家庭大門,以此來證明“是社會正確,還是我正確”[11](P200)。
郭沫若筆下的中國“娜拉”形象無疑借鑒了易卜生筆下的西方“娜拉”形象。各具特色。無論是西方的“娜拉”還是中國的“娜拉”,在她們身上都有著一種強烈的反叛意識,渴望去成為一個獨立自主的新女性,實現自我價值。《卓文君》取材于漢代卓文君私奔司馬相如的故事。卓文君和司馬相如相愛,遭到父親卓王孫的反對與阻攔。受紅蕭的啟發,不再屈服于“父權”的權威,她選擇像“娜拉”一般憤然離家。《王昭君》中郭沫若將歷史上王昭君的“命運悲劇”改成了“性格悲劇”。當漢元帝知道王昭君被毛延壽欺壓的事實,想要賜封王昭君為皇后時。王昭君對其投以不屑的態度,并對高高在上的皇權加以指責。為了反抗夫權皇權的壓迫,她請求遠嫁匈奴,去實現自我的解放。王昭君的反叛也體現出她思想中的獨立與反叛的精神。《聶嫈》中郭沫若將聶嫈塑造為女俠、女戰士的形象。哥哥聶政刺殺后選擇將面貌全部銷毀。當聶嫈聽說了哥哥聶政的事跡后,不僅沒有選擇茍活,還主動去哥哥聶政尸體旁邊證明身份,并以自殺來反抗,希望得到天下人的警示。
郭沫若和易卜生筆下的“娜拉”又有著很大的差異性,某些方面來說,前者對后者有所超越。易卜生筆下的“娜拉”經歷了由不自覺到自我覺醒的過程。郭沫若在《寫在〈三個叛逆的女性〉后面》一文中明確指出:“我自己對于勞動運動是贊成社會主義的人,而對于婦女運動是贊成女權主義的。”[10](P138)因而,他筆下的“娜拉”一出場就具有某種叛逆精神,這種精神促使她們不斷地與大環境斗爭。這種差異主要由易卜生和郭沫若不同的女性觀所決定。易卜生在與他朋友George Brandes的通信中曾說:“有時候我真覺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緊的還是救出自己。”[15](P54)在易卜生的觀念中,女性要想實現解放,關鍵是拯救自己。只要女性個體實現了自我解放,也就成功地走向了獨立,這種主張實際上也是一種利己主張。在郭沫若的女性觀中,女性要想實現解放,僅僅依靠自我意識的覺醒是不夠的,還要敢于和大環境作斗爭,女性的解放是反抗封建禮教結合在一起的。這不僅是他與易卜生女性觀主要的區別,也是他在形象塑造上超越易卜生的地方。
(二)配角塑造的繼承與超越。《玩偶之家》和《三個叛逆的女性》中配角的形象也是值得關注的。《玩偶之家》中的配角林丹太太是娜拉從小就認識的朋友,她從一開始就以一個久經世事、穩重的形象出現。在劇中,她既是娜拉的引導形象,又是一個補充的形象。在娜拉和軟克大夫的關系上,林丹太太在談話中巧妙地提醒娜拉恰當的處理。當娜拉借錢的事情即將暴露時,她安慰娜拉:“咱們一定得想法子叫柯洛克斯泰把信原封不動地要回去,叫他想個推托的主意。”[11](P172)而自己親自和柯洛克斯泰談判,成功說服他改變威脅海爾茂的計劃。林丹太太在劇中總是為娜拉積極地獻計獻策,不愧為一個優秀的引導者。同時,林丹太太在家庭中的頂梁柱作用,以及在社會上開小鋪、辦學校,熱愛工作的獨立形象無疑是易卜生對出走后娜拉形象的補充和期許。
郭沫若筆下的配角形象則呈現出了多元性。《卓文君》中的紅蕭是卓文君發現自我價值的引導者,她說:“我認為個人的運命,是該個人自己去開拓的,別人不能指導,也不從指導。”[10](P25)在她的鼓勵下,卓文君自我意識覺醒,認識到自己的處境并頑強地和父權抗爭。《王昭君》中毛淑姬沒有聽從父親毛延壽的吩咐去欺壓王昭君,反而積極地和龔寬一起為王昭君伸冤奔走。最終撕下了父親毛延壽虛偽的面具,使得正義得以伸張。當王昭君選擇遠赴沙漠去抵抗皇權時,她也毅然的選擇一起遠赴塞外。《聶嫈》中的春姑,拒絕聽從母親以美貌招攬生意的建議,她一開始就呈現出了反叛的精神。春姑還選擇了同聶嫈一起共赴死難,展現了一種豪邁的性情。當她面對聶嫈死亡的酬金答謝時,她毫不動容,反而選擇像盲叟一樣的傳頌者角色,希望把聶嫈兄妹的故事來儆戒世人。在《聶嫈》中還有一個頗富特色的配角——盲叟。郭沫若在《創造十年》中提到他自己:“尤其得意的是第一幕中的盲叟,那盲目的流浪藝人所吐露的情緒,是我的心理之最深奧處的表白。”[6](P234)郭沫若對盲叟的形象是頗具心力的,在《聶嫈》中塑造出不為世俗物質所動,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只為追求藝術和真理的盲叟形象。這個形象實際寄托了郭沫若希望做一個像盲叟一樣自由地追逐藝術和真理,并通過流浪將這種精神傳播下去,改變國民的靈魂。
郭沫若在配角形象塑造時也對易卜生有著繼承。郭沫若在配角形象塑造的時和易卜生一樣,沒有為了主角而降低配角的獨立性。也沒有因為期望呈現他們性格的豐富性而失掉主角的光環。他們都是獨立自主,有個人思想的人。林丹太太嘗試各種工作、紅蕭選擇用死亡鼓勵卓文君的出走、毛淑姬選擇和王昭君一起遠赴大漠、春姑選擇跟隨聶嫈去證明聶政的身份、盲叟選擇貧困但自適的流浪……配角的這些選擇,都是基于內心自由思想的主導,從而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同時,她們都有著相似的愛情態度:林丹太太與柯洛克斯泰、紅蕭與秦二、毛淑姬與龔寬、春姑與聶政,她們都在自由的選擇自己所愛的人。而且她們在劇中對主人公有著引導作用。林丹太太對娜拉的幫助、紅蕭對卓文君的鼓勵、毛淑姬對王昭君命運的推動、春姑對聶嫈行動的幫助、盲叟對聶嫈的推動。郭沫若在繼承易卜生配角的描寫方式時,又有所超越。紅蕭殺了走漏消息愛人秦二之后,果斷自殺的行為更加地決絕,她用生命去推動卓文君走向幸福。郭沫若筆下的配角形象相比之下更加具有反抗性和犧牲精神。此外,郭沫若用盲叟寄托了自己的藝術理想,也是一種超越。
三、藝術特色的借鑒與超越
易卜生被稱為“現代戲劇之父”,他“善于采用獨特的創作和技巧,反對西方流行的情節巧合而內容空洞貧乏的戲劇,以最簡潔的劇情把社會問題與舞臺藝術結合起來創作問題劇”[16](P44)。《玩偶之家》作為易卜生社會問題劇的主要代表,整個劇本的藝術特色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首先,易卜生在進行《玩偶之家》的創作時,突破了傳統的“巧湊劇”的影響,采用了“回溯法”將整個戲劇鋪展開來。戲劇開幕就以娜拉開心準備過圣誕節開始,繼而緩緩地追溯到八年前娜拉為了救海爾茂冒名簽字借債的事情,也因此將戲劇中的主要矛盾——“隱瞞借債和揭露借債”引上舞臺。其次,愛爾蘭劇作家蕭伯納曾評述道“這種嶄新的藝術手法(討論)……使得《玩偶之家》征服了整個歐洲,從而開創戲劇藝術的新流派”[17](P219),易卜生大膽的將傳統戲劇所懼怕的戲劇“討論”方式搬上舞臺,將劇中動作與其合為一體。無論是劇中對海爾茂性格的討論,還是結尾處對在娜拉和海爾茂的對話中對于婦女自身問題的討論,都將劇中的討論的問題成為生動的焦點,容易引起人們的關注與共鳴。最后,《玩偶之家》中戲劇的節奏變化極大,從開幕時娜拉和海爾茂之間商量圣誕節的歡樂到談到借債時的緊張,到海爾茂給娜拉錢之后的緩和,到海爾茂懷疑娜拉偷嘴的緊湊。整個《玩偶之家》都是在這種緩和與緊張的急轉中構成的,在緊張中又給人情理之中的很多意外。
《三個叛逆的女性》的創作可以窺見郭沫若自身用“舊瓶裝新酒”的那種“失是求似”的原則,他在歷史劇創作中巧妙地借用歷史題材以求達到“借古喻今”的效果。在這樣的戲劇原則下,郭沫若仍舊借鑒了易卜生的戲劇創作原則,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郭沫若的《三個叛逆的女性》對易卜生的“追溯法”有所繼承,《聶嫈》是由聶政刺殺并自毀容貌后開始追溯,《王昭君》是由毛延壽故意丑化王昭君的基礎上追溯;另一方面,《三個叛逆的女性》中借鑒了《玩偶之家》中常用的問題討論。《卓文君》中紅蕭和卓文君的對話是討論女性自身的命運問題、《王昭君》中漢元帝和王昭君的對話討論出君權、夫權對于女性的壓迫問題、《聶嫈》中春姑和士長的對話討論出社會環境的惡劣以及平等自由權利的問題。這些討論也揭示出戲劇的主旨。
在借鑒易卜生戲劇藝術手法的同時,郭沫若骨子里的傳統文化依舊在戲劇的書寫中被不經意的彰顯出來,這也造就了郭沫若對易卜生戲劇藝術特色的超越。一方面,郭沫若將浪漫主義和戲劇結合起來。陳瘦竹曾評:“郭沫若以革命浪漫主義詩人進行創作,成為杰出的戲劇詩人。”[18]在《三個叛逆的女性》中,最大藝術特色就是在進行戲劇創作時融入自我情感,使得三個戲劇成為了浪漫主義歷史劇。在戲劇中郭沫若時常借主人公之口敘述出自己的情感,在《卓文君》中他借卓文君說:“我不相信男子可以重婚,女子便不能再嫁!”[10](P56)這是郭沫若自己“三不從”思想的表現,也是他自己對于女性地位憤慨的體現。
另外一方面,作為詩人的郭沫若將詩歌和戲劇完美結合:一則含蓄的在語言中傳達出詩意。如《卓文君》中紅蕭與卓文君之間的對話:“你聽,不是琴音嗎?”“……不是,是風在竹林里吹”“……是水在把月亮搖動。”[10](P22)《王昭君》中毛淑姬形容王昭君的美貌時說道:“她那天生的美質,真好象雨落過后的明月一輪。”[10](P67)戲劇語言在傳達故事的同時,呈現一種詩意的美感。再則,郭沫若將古典詩詞引入戲劇。無論是卓文君在月光下念出的“鳳兮鳳兮歸故鄉”,還是《聶嫈》中的“春桃一片花如海”,均可看到戲劇中隨處灑落的古典詩詞。
結語
通過以上論述可知,《玩偶之家》和《三個叛逆的女性》都是中西戲劇史上爭取女性解放的優秀劇作,郭沫若的《三個叛逆的女性》不論在創作主題,人物形象塑造,還是藝術特色上都深受易卜生《玩偶之家》的影響。但作為深受中外文化沖擊的文化巨人,郭沫若在學習經驗的同時又表現出超凡的創造力:創造主題上的同中之異、人物形象塑造上融入自己的藝術理想、藝術特色上作為詩人郭沫若將詩歌和戲劇的結合,都可以看出郭沫若在借鑒《玩偶之家》的基礎上,又有著超越和發展,表現出極具色彩的戲劇魅力。
[1]劉華東.談易卜生對郭沫若的影響[J].新余高專學報,2005(1).
[2]鐘祥.郭沫若對易卜生的接受——重讀《娜拉》的答案[J].外國文學研究,1998(3).
[3]陳鑒昌.郭沫若易卜生筆下的“娜拉”比較[J].樂山師范學院學報,2001(1).
[4]陳鑒昌.郭沫若易卜生的娜拉形象意義比較[J].郭沫若學刊,2000(4).
[5]張柏柯.中外戲劇史上的一對奇葩——《玩偶之家》與《卓文君》之比較[J].延安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1(2).
[6]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 12 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
[7]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 15 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
[8]王錦厚等編.郭沫若佚文集(下冊)[C].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88.
[9]阿英.阿英全集(第2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10]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
[11][挪威]易卜生.玩偶之家.[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78.
[12][德]路·莎樂美.閣樓里的女人:莎樂美論易卜生筆下的女性.[M].馬振馳,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
[13]徐陵編.玉臺新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14]郭延禮.解讀秋瑾[M].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13.
[15]轉引自:胡適.讀書與做人[M].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16.
[16]王忠祥編選.易卜生精選集[C].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
[17]Shaw Bernard.The Quintessence of Ibsenism[M].New York:Brentano’sMcmxvll,1913.
[18]陳瘦竹.論郭沫若的歷史劇[J].戲劇論叢,195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