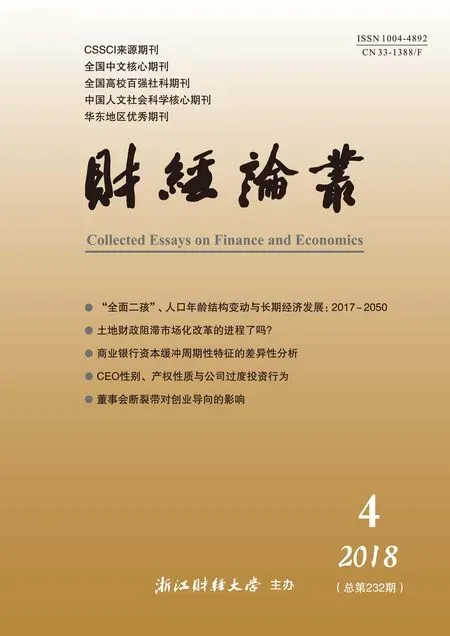規劃項目預算制度
——中國預算管理改革的新途徑
張 韜
(貴州財經大學經濟學院,貴州 貴陽 550004)
《國務院關于實行中期財政規劃管理的意見》(國發〔2015〕3號,以下簡稱“國發3號文件”)與《國家發展改革委關于加強政府投資項目儲備 編制三年滾動投資計劃的通知》(發改投資〔2015〕2463號,以下簡稱“發改投資2463號文件”)的出臺,為中國在未來實施真正意義的中期預算進行了積極的探索。截至2017年12月,中國內地除天津、重慶、山西外,其余省級政府部門甚至個別市級政府部門已先后出臺編制中期財政規劃的文件。中期財政規劃的實施,也為中國目前推進預算績效管理改革,深化預算管理改革奠定了制度基礎。2014年修訂的《預算法》明確規定要對預算支出實施績效評價。黨的十九大報告進一步明確提出了“建立全面規范透明、標準科學、約束有力的預算制度,全面實施績效管理”的要求。推動預算績效管理,實施績效預算制度,成為中國預算管理改革新的主要方向。
然而,中國出臺編制中期財政規劃文件的大部分地方政府,普遍存在缺乏財政項目庫支持的情況。“國發3號文件”出臺三年以來,財政部對中期財政規劃編制工作尚未確定改革時間表,地方政府即使出臺了本級政府實行中期財政規劃的政府文件,卻仍然繼續采用傳統的“基數法”對未來三年的財政收支進行預測,甚至部分地方政府以轉發“國發3號文件”回應國務院。中期財政規劃遲遲未能落實,導致國內對中期財政規劃的關注度正逐漸趨冷。無論是中期財政規劃,還是預算績效管理,都有賴于財政項目庫進行支撐。中國中期財政規劃改革實施并不順利,導致預算績效管理改革存在較大變數。全面實施績效管理要想取得預期效果,必須深入分析中國預算管理改革面臨的障礙和原因,借鑒世界部分國家預算管理改革成功的經驗,尋求預算管理改革的新途徑。
一、中國中期財政規劃改革現狀分析
(一)預算的準確性亟待提高
只有提高預算的準確性,中期財政規劃的編制才具有實際意義。威爾達夫斯基認為,如果預算缺乏預測性價值,而且實際支出也未包括在預算中,那么該預算就不能作為一個指南,也沒有人會接受這樣的預算[1]。部分地方政府雖然已經出臺編制中期財政規劃的政府文件,但其作出的對未來三年財政收支的預測數與實際執行數常存在較大的偏差。尤其對于層級較低或財力較為困難的基層政府,中期財政規劃的預測數與實際執行數往往偏差更大。這種偏差迫使絕大部分地方政府只能繼續采用傳統的“基數法”對未來三年的財政收支進行預測,而“基數法”的預測方法又偏離了中期財政規劃改革傳統預測方法的初衷。
(二)預算編制和規劃(計劃)編制之間相互脫節
由財政部主導的預算編制和由國家發展改革委主導的規劃(計劃)編制,一直缺乏有效的制衡和銜接機制。尤其在涉及到中期財政規劃改革的進程上,財政部門與發改部門仍在不同的軌道上運行。一方面,中期財政規劃和三年滾動投資計劃、甚至年度預算和年度計劃之間聯動性較弱*根據“發改投資2463號文件”的要求,財政部負責為政府投資需求提供財政預算保障,且負責將三年滾動預算(即中期財政規劃)和三年滾動投資計劃統籌銜接。但如何統籌銜接中期財政規劃和三年滾動投資計劃,財政部和國家發改委尚未出臺詳細的操作指南。,影響了資源配置的針對性和有效性;另一方面,預算編制與規劃(計劃)編制存在錯位[2]190,預算與規劃(計劃)未能實現同步編制。*財政部門在啟動編制年度預算的工作時,發改部門尚未啟動編制年度計劃的工作。由于部分項目支出在編制年度預算時無法確定,加之其它外部因素的干擾,使每年年度預算的執行數常偏離于預算數,財政部門一般在每年第三季度必須進行預算調整。預算編制與規劃編制之間相互脫節,使財政部門所編制的中期財政總規劃,在實際中難以約束各部門編制的部門中期財政規劃。各部門只需根據自身需求編制部門預算草案,而將預算平衡的任務推卸給財政部門[3]。
(三)對中期財政規劃的重視程度呈現逐漸弱化的趨勢
中期財政規劃預測數與實際執行數的偏差,以及預算與規劃(計劃)之間相互脫節,中期財政規劃存在淪為財政部門“獨角戲”的風險,甚至已經導致財政部對中期財政規劃的重視程度正逐漸弱化*在2014~2016年,財政部連續三年在向全國人大提交的預算報告中提到“中期財政規劃管理”。然而2017年財政部在向全國人大提交的預算報告中,已經刪除了“中期財政規劃管理”的字樣,取而代之的是“深化預算績效管理改革,逐步將績效管理范圍覆蓋所有預算資金”。,尤其國務院和財政部迄今尚未對各部門與各省區的中期財政規劃改革安排時間任務表。而財政部對中期財政規劃重視程度的變化,又進一步加劇各級地方政府、各行政部門對中期財政規劃改革采取了觀望的態度。一方面,政府部門已很少再提及“國發3號文件”,甚至曾經轉發“國發3號文件”或已經出臺實行中期財政規劃文件的地方政府,也沒有針對中期財政規劃出臺詳細可操作的指南,對中期財政規劃的關注也逐漸趨冷。另一方面,中期財政規劃改革在各部門與各省區間進展也不平衡,尤其各省區出于各自利益考慮,對貫徹實施中期財政規劃的政策力度也存在著較大的差異。
二、中國中期財政規劃障礙原因分析
(一)實行中期財政規劃對未來財政收入的可靠性和穩定性有著嚴格的要求
根據國際慣例,中期財政規劃的時間跨度一般為3~5年。延長的時間跨度使其相較年度預算將面臨更多的不確定因素。因此,中期財政規劃對未來財政收入的可靠性、穩定性有著極為苛刻的要求。一方面,中國目前編制的中期財政規劃尚未考慮物價因素的影響,而物價水平的波動將對中期財政規劃的準確性產生干擾。“當價格發生重大和非預期變動時,以資金表示的預算的規模將發生很大的波動”[4]。另一方面,非稅收入容易受到經濟波動及其它外生變量的影響,因此如果一個地區的非稅收入比重較高,在一定程度上會成為中期財政規劃改革的障礙。*尚未編制中期財政規劃的天津、重慶、山西,2016年的非稅收入占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比重分別達到40.4%、35.4%、33.4%。
(二)目前的項目庫難以支撐中期財政規劃的運行
發改部門與財政部門各自主導的項目庫,對支撐中期財政規劃的運行仍存在較大障礙。一方面,財政部門主導編制的預算項目庫,在實際操作中難以支撐中期財政規劃的運行。雖然中央部門和部分地方政府已相繼啟動了預算項目庫的編制工作*《財政部關于進一步做實中央部門預算項目庫的意見》(財預〔2016〕54號)提出:“2016年各部門開展預算評審的項目支出數額占項目庫中應評審項目支出總額的比例要達到30%以上,2017年達到50%以上,2018年達到80%,2019年實現百分之百覆蓋。”,但是均需要預算資金投入的發改部門項目庫與財政部門預算項目庫,在編制與評估工作中仍然相互獨立,使財政部門編制跨年度的項目支出預算仍將面臨較大的變數。另一方面,由發改部門主導編制與評估的項目庫,在實際操作中難以與財政部門的期望相兼容。發改部門的項目庫涉及大量市場化投融資項目,而這些項目不可能由財政部門全額“埋單”。即使發改部門的項目庫專門列出了需要公共預算資金投資的內容,但由于財政部門一般很少介入發改部門項目庫編制與評估工作,很難完全認同由發改部門主導編制的項目庫。
(三)中國的中期財政規劃缺乏法律約束力與實施細則
一方面,中國的中期財政規劃缺乏法律約束力。中期財政規劃管理在中國的《憲法》《預算法》等法律文件均未被提及,其實施的主要依據來自“國發3號文件”。然而,“國發3號文件”實質上只是財政部以國務院的名義出臺的一個政府文件,僅供政府部門在編制年度預算時進行參考,并沒有法律約束力。另一方面,財政部迄今尚未出臺《中期財政規劃實施實則(或實施方案)》。由于中期財政規劃缺乏具有可操作性的實施細則或實施方案,部分部門對編制中期財政規劃缺乏足夠的認同。目前僅靠“國發3號文件”一紙文件,難以支撐中國中期財政規劃機制的運行。更為嚴重的是,“國發3號文件”出臺時間已經超過3年,其實施效力將隨時間推移與相關部門領導更迭而逐步衰減。
三、美國規劃項目預算制度改革及其評價
中期財政規劃管理和預算績效管理,均要求重視對跨年度的項目進行績效評價。但中期財政規劃和預算績效管理的核心內容,均來源于“以規劃導向進行理性決策”的“規劃項目預算制度”(Planning Programming Budgeting System,PPBS)。
(一)美國規劃項目預算制度簡介
規劃項目預算發端于美國企業界。在20世紀60年代以前,美國國防預算只是一個在三軍之間瓜分資金的賬本。國防部長既難以從國家安全戰略出發設計預算分配方案,也缺乏對各軍種成績評價的工具,只能根據各軍種每年的要求分配預算。
曾擔任福特汽車公司總裁的麥克納馬拉(McNamara)在1961年接任國防部長后,希望引入一種“跨年度且以項目為導向的”國防預算。利用系統分析和運籌學所取得的進展,麥克納馬拉決定將規劃項目預算制度引入國防部。引入規劃項目預算制度,為國防部對各軍種的效益和成本進行評估提供了有效的政策工具,擴大了政府執行計劃的選擇性。*關于麥克納馬拉引入規劃項目預算制度的詳細內容,可登陸美國國防部網站進行查詢。http://history.defense.gov/Multimedia/Biographies/Article-View/Article/571271/robert-s-mcnamara/。麥克納馬拉還在此基礎上開始編制五年國防規劃(the Five-Year Defense Plan,FYDP)。
美國國防部的改革引起了約翰遜總統的關注。雖然白宮的行政權力整體上有所加強,但聯邦預算與約翰遜總統“偉大社會”的施政目標之間相互脫節的問題,使聯邦政府在限制私人壟斷、開礦,反對販毒、搶劫或推廣家庭規劃方面工作效率低下[5]80。為了提高政府工作效率,約翰遜總統于1965年要求總統預算局(The Bureau of the Budget,BOB)在聯邦政府各部門開始執行規劃項目預算。在規劃項目預算制度的基礎上,聯邦政府又引入了總統備忘錄草案(the Draft Presidential Memorandum,DPM),確保聯邦部門執行程序與總統行政命令的一致性。Schick(1966)認為,規劃項目預算是第一個被設計為同時適應控制導向、管理導向、規劃導向的預算制度,既預示著一次激進的預算革命,又根植于歷史傳統與演化[6]。
但是,美國聯邦政府的規劃項目預算制度在設計中存在缺陷。一方面,規劃項目預算制度需要對每個項目進行量化分析,但部分項目實際中難以進行量化,尤其數據收集工作分散在各部門且各部門間協作不充分[5]82。漸進預算理論奠基者Wildavsky(1969)甚至認為,規劃項目預算是一種非理性的分析方式,給美國聯邦政府預算帶來的是壓制而非對錯誤的修正[7]。另一方面,規劃項目預算制度的改革步伐超出了預期的方案。原先總統預算局只是考慮在少數部門進行試點,但過于樂觀的約翰遜總統將原方案改為在聯邦政府21個部門同時實行。結果規劃項目預算制度在執行過程中,遭到了聯邦預算最終決策者——美國國會的反對,眾議院撥款委員會仍然要求聯邦政府繼續采納傳統的分項排列預算制度(Line-Item Budgeting System)[8]。
(二)對美國規劃項目預算制度的評價
規劃項目預算是美國政府汲取了20世紀50年代實施的績效預算因缺乏項目支持遭遇挫折后,所作出的一次積極的預算管理改革探索。由于代表民主黨利益的約翰遜總統推行的規劃項目預算,并未得到當時由共和黨操縱的美國國會的支持,同時規劃項目預算在理論設計上偏重于規劃導向和管理導向,過于理想化的設計未能有效化解聯邦政府日益嚴重的財政赤字和債務問題。因此,當代表共和黨利益的尼克松總統上臺后,便于1971年宣布停止規劃項目預算。而美國的規劃項目預算成為黨派斗爭的犧牲品,導致部分政界和學界對規劃項目預算制度持悲觀或消極態度。
事實上,規劃項目預算為美國的中期財政規劃和結果導向預算改革成功留下了豐富的遺產。雖然聯邦政府全面推行的規劃項目預算制度于1971年被尼克松總統廢止,但尼克松總統上臺后實施的目標管理(Management by Objectives,MBO),事實上只是規劃項目預算的“翻版”。*信奉保守主義的美國共和黨一般較為反感“Planning Programming Budgeting System”中的“Planning”,認為政府制定過多的“Planning”會損害公民的自由。然而,代表共和黨利益的尼克松總統在上臺后卻進一步強化了白宮的行政權力,其中包括了將總統預算局升級為總統管理與預算局(The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OMB)、將項目優先決定權劃歸總統等。Gremillion等(1980)、馬國賢(2008)的研究發現,部分聯邦機構仍保留了規劃項目預算制度。美國農業部林業司在綜合了零基預算、目標管理預算制度后,在其國家森林系統(National Forest System,NFS)中將規劃項目預算改良為項目計劃制度(Program Planning System)[9][10]。Klucers(2001)、馬駿等(2011)通過對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州地方政府預算的研究,認為規劃項目預算的信息對預算決策非常重要[11][12]。茍燕楠(2011)認為,雖然規劃項目預算改革因超越政府的能力而失敗,但改革也為現代預算制度的發展留下了寶貴的遺產,包括實現中長期規劃與年度預算的整合、強調項目績效評價,對新績效預算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2]11。1993年克林頓總統簽署的《政府績效和結果預算法案》(Government Performance and Results Act,GPRA)以及2004年小布什總統簽署的《項目評估與結果法案》(Program Assessment and Result Act,PRA),繼承并發展了規劃項目預算制度的核心內容。尤其美國總統管理與預算局在2002年引入的項目評級工具(Program Assessment Rating Tool,PART),推動了預算與績效相銜接[2]15。
四、引入規劃項目預算是預算管理改革一個新的途徑
項目支出是中期財政規劃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項目庫管理可以有效地支撐項目支出以及中期財政規劃的運行。通過對中期財政規劃改革障礙的原因分析,說明缺乏發改部門的支持,片面依靠財政部門推動中期財政規劃改革是不現實的。尤其財政部門與發改部門之間關于項目庫編制的矛盾尚未解決,增加了財政部在推進中期財政規劃改革的障礙,也導致預算績效管理改革也將面臨相似的困境。
與此同時,各部門的專項規劃和區域的發展規劃在編制過程中,存在權力與責任不匹配的問題,在一定程度上也導致提出編制三年滾動投資計劃的“發改投資2463號文件”,在全國各省級發改部門也同樣存在“以文件落實文件”的現象。發改部門可以通過項目審批來體現自身的政績,卻可以輕易將項目責任推卸給具體的執行部門。而財政部門在項目審批中,常扮演類似負責“埋單”這種被動參與的角色。*《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對中期財政規劃和年度預算的要求是:“中期財政規劃和年度預算要結合本規劃提出的目標任務和財力可能,合理安排支出規模和結構。”這種情況加劇了財政部門與發改部門之間的矛盾。一旦發展規劃的編制缺乏財政部門積極主動的配合,其在具體執行過程中將難以得到充分且可持續的預算資金保障。加之目前中國的中期財政規劃與土地資源規劃、城鄉建設規劃、生態文明規劃之間呈現出“各自為政”的格局,甚至在時間上都不能與作為“總體規劃”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五年規劃保持同步,無疑增加了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五年規劃所確定的目標落實的難度。
為有效解決由財政部領銜編制的中期財政規劃和預算績效管理,以及由國家發改委領銜編制的五年規劃和三年滾動投資計劃之間的有機銜接問題,尤其是解決各自主導編制的項目庫上存在的矛盾,將預算管理改革的離心力轉變為合力。引入規劃項目預算,可以為中國預算管理改革提供一種新的途徑,增強財政部門與發改部門在預算管理改革的動力。
由發改部門領銜編制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五年規劃,一直是黨和政府治理國家的主要方略,發改部門已經積累了豐富的“規劃治國”經驗。首先,由發改部門領銜、財政部門配合編制規劃項目預算。其次,以規劃項目預算為制度基礎,由財政部門領銜編制中期財政規劃,發改部門領銜編制三年滾動投資計劃,實現中期財政規劃和三年滾動投資計劃之間的銜接,并對中期財政規劃和三年滾動投資計劃涉及的重大任務和項目進行深度融合,逐步過渡到真正意義上的中期預算。最后,以規劃項目預算和中期預算為制度基礎,深化預算績效管理改革,啟動績效預算編制,從而實現中國預算管理改革的目標(見圖1)。

圖1 中國預算管理改革框架圖
五、實施規劃項目預算改革的主要路徑
(一)國家發改委領銜、財政部配合編制規劃項目預算
1.發改部門具備實施規劃項目預算的動機
如果發改部門在財政部門的配合下,領銜編制規劃項目預算,各部門編制部門規劃項目預算,財政項目庫的問題在制度上得以落實,不僅可以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五年規劃提供及時、可靠的公共預算資金支持,而且維護了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五年規劃的約束力及發改部門的公信力。
2.發改部門具有編制規劃項目預算的比較優勢
從“一五”計劃到“十三五”規劃,由中國發改部門主導編制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五年規劃,一直是黨和政府治理國家的主要方略。發改部門在評估項目的優先性方面,相較其他部門具有顯著的比較優勢,可根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五年規劃所確定的目標和任務,負責審核各部門規劃項目預算可否列入總規劃項目預算、以及各部門規劃項目預算執行的時間順序。財政部門負責維護規劃項目預算的財經紀律,控制預算規模并監督規劃項目預算的執行。
(二)財政部領銜編制中期財政規劃,國家發改委領銜編制三年滾動投資計劃
隨著國家發改委領銜、財政部配合編制的規劃項目預算開始啟動,無論是財政部領銜編制的中期財政規劃,還是國家發展改革委領銜編制的三年滾動投資計劃,都具備了可靠的制度基礎。
1.財政部領銜編制中期財政規劃
首先,各行政部門以發改部門跨年度的規劃項目預算為基礎,編制跨年度的項目支出預算;然后,各行政部門結合跨年度的基本支出預算編制完整的跨年度的部門預算(即部門中期財政規劃);最后,由財政部門審核匯總后形成完整的中期財政規劃。
2.銜接和整合中期財政規劃和三年滾動投資計劃,并過渡到中期預算
首先,銜接中期財政規劃和三年滾動投資計劃的目標和任務,尤其是中期財政規劃和三年滾動投資計劃的編制時間,實現中期財政規劃和三年滾動投資計劃同步進行。其次,在中期財政規劃和三年滾動投資計劃銜接機制運行成熟后,整合中期財政規劃和三年滾動投資計劃(涉及公共預算資金的部分),形成中期預算,與年度預算、年度計劃一并提交人民代表大會進行審批,賦予中期預算必要的法律約束力。
(三)由財政部領銜、國家發改委配合編制績效預算
規劃項目預算的編制賦予了績效預算基本元素,而中期預算的編制又賦予績效預算多年期的視角。在規劃項目預算制度和中期預算制度均運行成熟后,由財政部領銜、國家發改委配合,啟動績效預算編制。財政部門負責維護績效預算的財經紀律,控制預算規模并監督績效預算的執行。發改部門對績效預算的執行進行監督,確保績效預算的執行符合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五年規劃所確定的目標和任務。
無論是規劃項目預算,還是中期預算與績效預算,對中國而言都屬于“舶來品”。在政治制度、經濟管理制度、文化背景等方面,中國與美國都存在明顯的差異。在中國現行的政治和經濟管理體制下,要想達到通過實施規劃項目預算、中期預算和績效預算來實現國家預算管理改革目標,首先需要在部分地區與部門進行試點。在試點取得一定成效后,需要通過繼續修訂《預算法》,構建起與之配套的法律法規體系,同時通過體制機制創新和政策創新來創造制度基礎。這一系列改革尚需要專家學者通過更深入的研究后提供決策參考,更需要財政和發改等實務部門進行更深入的實踐探索。
參考文獻:
[1] [美]阿倫·威爾達夫斯基.預算:比較理論[M]. 茍燕楠,譯.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9.5.
[2] 茍燕楠.績效預算:模式與路徑[M]. 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11.11,15,190.
[3] [德]羅伯特·黑勒,趙陽譯.德國公共預算管理[M]. 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3.93.
[4] [美]阿倫·威爾達夫斯基.預算與治理[M]. 茍燕楠,譯.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10.6.
[5] 陳寶森.美國經濟與政府政策——從羅斯福到里根[M].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80,82.
[6] Schick A. The Road to PPB: The Stages of Budget Reform[J].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1966,26(4):243-258.
[7] Wildavsky A. Rescuing Policy Analysis from PPBS[J].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1969,29(2):189-202.
[8] [美]杰克·瑞賓,托馬斯·D.林奇.國家預算與財政管理[M]. 丁學東,居昊,王子林,吳俊培,王洪,羅華平,譯.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0.124.
[9] Gremillion L., McKenney J. and Pyburn P. Program Planning in the National Forest System[J].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1980,40(3):226-230.
[10] 馬國賢.政府預算理論與績效政策研究[M]. 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8.465-466.
[11] Klucers R.An Analysis of Introducing Program Budgeting in Local Government[J]. Public Budgeting & Finance,2001,21(2):29-45.
[12] 馬駿,趙早早.公共預算:比較研究[M]. 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3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