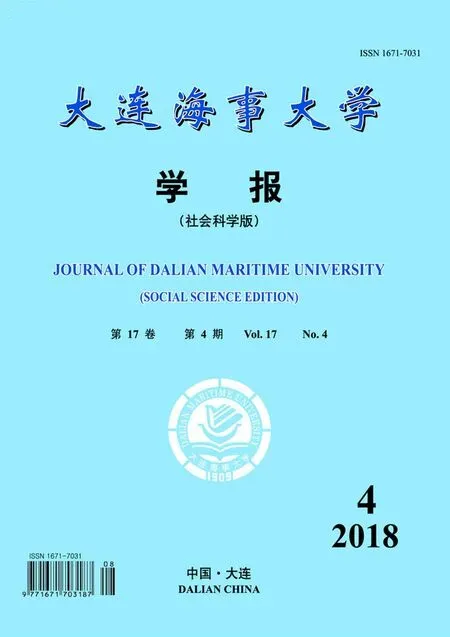中西方功利主義政治哲學理論辯證
徐慶利,劉盼盼
(大連海事大學 公共管理與人文藝術學院,遼寧 大連 116026)
雖然功利主義政治哲學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著極其重要的學術地位,并以其獨具特色的工具主義道德標準影響了人類兩千多年來的社會政治生活,但是在其理論的普世性問題上,學術界則莫衷一是。有大陸學者認為:中國沒有像西方那樣的完備的功利主義政治哲學,有的乃是一些不具理論連續性的功利思想。[1]然則事實確實如此嗎?未必然。
一、概念與范疇:理論研究的起點
從人類思維發展的特性來看,人們在理解和把握社會政治生活的過程中,首先是從賦予認識對象以一定的概念開始的,通過對這些概念的認知來形成對認知對象的理解和把握。從這一點來說,理解和把握這些概念,乃是一切政治哲學理念得以建構的理論前提與思想基礎。現在,對于功利主義政治哲學的研究起點也應在此。
(一)概念解析
1.功利
功利作為功利主義的核心概念,其英文“utility”原義為“有用,實用,效用”[2]。在人類的社會政治生活中,“功利”表現為某種事物對于人自身欲求的滿足程度。正是由于“功利”的存在,人們在對社會政治生活的選擇上,趨向于“趨樂避害”。古希臘的伊壁鳩魯對于何為倫理學意義上的善,就是從“趨樂避害”的效果論角度去解釋的。他闡釋道:“只有當我們痛苦而無快樂時,我們才需要快樂;當我們不痛苦時,我們就不需要快樂了。因為這個緣故,我們說快樂是幸福生活的開始和目的。因為我們認為幸福生活是我們天生的最高的善,我們的一切取舍都從快樂出發,我們的最終目的乃是得到快樂,而以感觸為標準來判斷一切的善。”[3]103
在政治學哲學的層面,“功利”作為一種內在的價值原則,維系著一個國家政治及法律原則的正常運轉。19世紀英國功利主義大師邊沁認為,“功利”的內在價值取向就是“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但是需要說明的是,“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并不一定是代表正義的善,判斷一種善是否合乎正義,并不是看其是否代表大多數人的利益。譬如,中國政治史上所謂的“夷夏觀”,雖然它符合廣大屬于“夏文化”民眾的政治觀,但是它并不代表一種合乎正義的善。
2.功利主義
功利主義,是“功利”的意義在理論上的系統化,它“可以被視作是一種根據對人們的幸福的影響來直接或間接地評價行為、政策、決定和選擇的正當性的倫理、政治傳統的名稱”[4]。另外,從理論的價值來講,功利主義是“自由主義的另外一個理論基礎”,其基本理論傾向“即是認為一切立法、政府政策和道德原則的最終判定標準是其實行之后可能達到的功利水平。……(它)以人的感覺所表現出來的快樂作為判定的基本出發點,而精神的安寧則是在此之上的更高的衡量指標”。[5]可見,對于功利主義來講,它是自由主義的一種,但是所強調的不是一種目的論,而是一種效果論,即所謂“成者為王,敗者為寇”。這種效果論內涵的價值很直接,但是其評判標準卻難以令人把握。它給人的不是一個統一的、可以直觀把握的標準,而是建立在“個人感覺”這個心理層次之上的一個個支離破碎的理念。此外,這種“精神的安寧”作為“更高的衡量指標”更是令人難以把持。
(二)范疇界定
1.快樂與痛苦
如果從“快樂”和“痛苦”的表現形式來看,可以從物質和精神的兩個層面去體分;但是如果從單一個體對二者的心理感觸來考察,則存在此消彼長、不可兼得的現象。因此對于快樂與痛苦的取舍,是在個體對二者做出對比之后才做出的選擇。
功利主義政治哲學的產生就是來源于人們對于快樂的體認。在功利主義者那里,他們認為:“自然把人類置于兩位主人公——快樂和痛苦——的主宰之下。只有它們才指示我們應當干什么,決定我們將要干什么。是非標準,因果關系,俱由其定奪。”[6]可見,在功利主義者意向中,快樂不只是人類的一種簡單感官行為,而且是一種“至善”。因為快樂是一種“至善”,所以追求快樂不再是某個人的單獨行為,而成為整個人類都在采取的集體行為。
2.善與惡
作為倫理學上的一個核心概念,“善”經常表現為某種被要求或被命令的特質;而“惡”,則是以“善”的對立面出現,并且常常顯現為某種被禁止的特質。[7]在倫理學層面,“善”之所以成為人類社會政治生活追求的生活目標,就在于它讓人們找到了一個可供選擇并遵循的道德原則。對于功利主義政治哲學而言,“善”之所以被作為其理論的基本范疇,其根本意義也正緣于此。
在功利主義思想家這里,他們認為,“但凡是任何人嗜欲或欲求的任何對象,自他一方面言,便名為善;而任何他所仇恨及憎避的對象,則名為惡”[3]656,“所謂善與惡,只是快樂或痛苦自身”[8]。因為“快樂”是每一個參與社會政治生活的人都想得到的價值訴求,“快樂”即是“善”,“善”即是“快樂”,所以一切追求“快樂”的行為,都符合“善”的原則。這樣,功利主義政治哲學找到了為自己功利行為進行辯護的有力武器。
3.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
人與社會的關系,是人類社會政治生活中不可回避的一對重要關系。與之相對應,“利益”也就相應有了兩方面的區分,即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對于功利主義政治哲學而言,由于中西方政治、經濟、文化環境的不同,在對“利益”的終極選擇上,出現了不同的路向選擇。
中國的功利主義政治哲學選擇的是一條如何從強調整體、忽略個體轉變到整體與個體并重的道路,即從“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張子語錄》),到“今日欲言獨立,當先言個人之獨立,乃能言全體之獨立”(《十種德性相反相成義》)。而西方的功利主義政治哲學選擇的則是一條如何從利己轉向利他,進而彌合個人利益與整體利益之間界限的道路,即從“凡是安寧地生活的人,就不應該擔負很多的事,不論是私事還是公事”[3]73,到“待人像你期望人待你一樣,愛你的鄰人像愛你自己”[9]。
二、歸屬:兩種語境下的功利主義政治哲學
西方功利主義政治哲學肇始于古希臘的德謨克利特與伊壁鳩魯的“幸福論”,后經中世紀的消沉,在文藝復興之后,特別是在19世紀以邊沁、密爾為代表的古典功利主義時期,達到了理論的頂峰。這一時期,西方功利主義政治哲學不僅完成了思想體系的整體架構,而且成為19世紀乃至20世紀世界各國社會政治發展的主要助推力之一,創造了不朽的輝煌。進入當代之后,西方功利主義政治哲學又呈現出新的發展態勢,政治哲學家們在為其理論進行辯護的同時,又提出了準則功利主義與行動功利主義兩大理論,進而為功利主義政治哲學在西方當代世界的發展帶來了新的契機。
如果說西方功利主義政治哲學的發展比較奔放,那么中國功利主義政治哲學的發展則比較含蓄,含蓄得甚至讓人產生懷疑,懷疑它是否曾經存在過,它的名字是否也可以稱之為功利主義政治哲學。
對于中國功利主義政治哲學是否存在,是否也可以稱之為功利主義政治哲學,是一個必須加以澄清的話題。從認知世界的途徑來分析,人類大致是沿著兩條路徑來認識我們身處的這個世界的。
其一,由概念到物的形而上途徑。這種認知路徑要求人們對世界的認知,首先從掌握具有“普遍意義”的概念入手,以一個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概念為出發點,進而形成對一個個具體事物的認識與把握。西方功利主義政治哲學走的就是這樣一條道路,如伊壁鳩魯的幸福論,就是從對“幸福”概念的界定開始的。他認為所謂幸福,就是“身體上無痛苦,靈魂上無紛擾”[3]104,由此他導引出具有功利主義性質的“幸福論”。后世的功利主義政治哲學家正是按照這種認知路徑,推演出功利主義政治哲學的重要命題——“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
其二,由物到概念的形而下途徑。這種認知路徑的出發點不再是一個個抽象的概念,而換之為一個個具體而鮮活的事物。這種認知途徑,不是來自于形而上學的概念界定,而是來自于對同類事物的不完全歸納,因為每個人的認知角度、理論水平,以及所考察事物的多寡是不同的。由于是不完全歸納,便會導致關于此類事物的概念各異。物與物之間的支離破碎,導致概念與概念之間無法統一。中國的功利主義政治哲學走的就是這樣一條認知的道路,它的每一步發展都緊緊依賴于當時的社會現實,因現實而產生,為現實而服務,現實改變了,理論也就跟著改變,因而始終沒有形成一個統一、完備的理論體系。從先秦墨家的“兼相愛,交相利”、法家的非道德政治論,到鼎盛時期南宋浙東陳亮、葉適的反道義論,再到理論中西交融時期的中國近代,無一不在驗證著這樣的認知路徑。
由于中國的功利主義政治哲學始終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的理論形態,因此國內大部分學者不愿、甚至不屑用“功利主義”來加以冠之。他們認為:“中國哲學沒有‘功利主義’。如果一定要給中國的‘功利’思想加一個名稱,則只可名曰‘大利主義’;如果一定要給出一個價值判斷,則只可以說以‘西式功利主義’解讀中國哲學,乃是貶低了而不是抬高了中國哲學。”[1]
既然中西方功利主義政治哲學存在著這樣大的差異,那么為何屬于同種理論歸屬呢?
首先,在于質的同一性。任何理論在其發展的過程中均不可能整齊劃一,不僅要重視共性問題,而且要給予個性理論存在與發展的空間。這就好比人類自身形體的發展,幾乎找不出完全一致的兩個個體。即使是形象再為一致的雙胞胎,細心的父母也能發現其存在于表象一致下的些微差別。另外,在社會政治生活中,人除了個體形象存在差別之外,最大的差別還有來自于每個人內心世界的不一致性。
既然人與人之間存在如此的不一致性,那么為何歸屬于同一種物種呢?這個問題其實很簡單。形形色色的個體之所以并稱為“人”,是因為都具有作為“人”的質。對于人的本質,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一書中指出,“人的本質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10]。
其實,中西方功利主義的發展歷程也是這樣,雖然它們表現出不同的理論形態,但是它們理論的本質特征卻是一致的,即它們均是以工具理性為出發點,強調結果、目的,并以此來判定行為的善與惡,進而指導人類社會政治生活的總體走向。中國的功利主義,雖然沒有發展成像西方那樣完備的理論形態,但是從理論的主旨來看,與西方功利主義則屬于同一種宗屬,只不過沒有完全成型罷了。
其次,在于研究對象的一致性。政治哲學作為政治學與哲學的交叉學科,是政治學的形而上學。從研究的內容來看,政治哲學所研究的不再是人們看得見、摸得著的政治科學,而是人類社會政治生活中的應然性問題,即“ought to be”問題;而政治科學則是研究人類政治生活的實然性問題,即“to be”的問題。
對于中國功利主義政治哲學而言,它的研究對象也是建立在對社會政治現實的批判基礎之上,也是對人類社會政治生活所做的應然性判斷。特別是近代康有為的《大同書》,認為人類社會政治生活應該生活在大同之世,只要生活在這樣的世界,后世便再也無任何痛苦可言了。
鑒于此,可以認為:功利主義政治哲學是存在于兩種語境之下,中西方功利主義政治哲學是同一種理論歸屬的兩條分支。
三、批判:來自道義論的詰難
由于功利主義政治哲學堅持的是一種目的論,目的論的偏執性必然要招致反對者的詰難。在功利主義政治哲學的反對者中,影響力最強的就要屬西方當代道德哲學家羅爾斯,以及我國南宋時期的大儒朱熹。
羅爾斯在其代表作《正義論》的篇首,便闡釋出其理論的主旨:“我的目標是要確立一種正義論,以作為一種可行的選擇對象,來替換那些長期支配著我們的哲學傳統(功利主義、直覺主義)的理論。”[11]1*括號內容為本文作者所加。他認為:“功利主義在某種意義上并不把人看作目的本身……如果各方接受功利標準,他們就缺少對他們的自尊的支持,這種支持是由他人的公開承諾——同意把不平等安排適合于每個人的利益并為所有人保證一種平等的自由——所提供的。在一個公共的功利主義社會里,人們將發現較難信任自己的價值。”[11]173羅爾斯對于功利主義政治哲學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
首先,羅爾斯批判了功利主義所堅持的“善”優先論,指出“正當應優先于善”而存在。羅爾斯認為功利主義政治哲學對“善”的體認,完全忽視了正當的價值。他指出,“正義原則(在更廣泛的意義上即是正當原則)是處于原初狀態的人們愿意選擇的原則,而合理選擇的原則和審慎的合理性的標準則完全不是被選擇的”[11]434;“各個個人是從不同的方面確定他們的善的,許多事物可能對一個人來說是善而對另一個人則不是善”,而“在一個組織良好的社會里,公民們持著相同的正當原則,他們在各個具體的例子中都試圖達到相同的判斷。這些原則將在人們相互之間的沖突的要求中建立一種最終的秩序”。[11]435
其次,羅爾斯批判了功利主義所堅持的“社會選擇來源于個體選擇擴大化”的觀點。羅爾斯認為:“假定一個人類社團的調節原則只是個人選擇原則的擴大是沒道理的。”[11]26他指出:“如果我們承認調節任何事物的正確原則都依賴于那一事物的性質,承認存在著目標互異的眾多個人是人類社會的一個基本特征,我們就不會期望社會選擇的原則會是功利主義的。……我們不能僅僅通過把合理慎思的原則擴大到用于由公平的觀察者建立的欲望體系來達到一種社會選擇原則。這樣做沒有嚴格地考慮個體的眾多和區別,沒有把人們將一致同意的東西看作正義的基礎。”[11]26
最后,羅爾斯批判了功利主義所倡導的犧牲論。羅爾斯認為功利主義政治哲學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它直接地涉及一個人怎樣在不同的時間里分配他的滿足,但除此之外,就不再關心(除了間接的)滿足的總量怎樣在個人之間進行分配”[11]23。他認為應確立“分配的正義”,使公民的平等自由權利對于福利總量的增長具有優先性。為此,他強烈反對“為了使很多人分享較大利益而剝奪少數人的自由”[11]23的功利主義犧牲原則。而如何實現這種“分配的正義”呢?羅爾斯把希望寄予了其著名的“正義兩原則”,即“平等的自由權原則”與“機會公平平等原則”。
與西方的羅爾斯相比,我國宋代大儒朱熹對功利主義的批判則是直接在與浙東功利主義學派的論辯中完成的。
在宋代,針對陳亮的功利主義政治哲學,朱熹就曾批評指出,“嘗謂天理、人欲二字,不必求之于古今王霸之跡,但反之于吾心義利邪正之間,察之愈密則其見之愈明,持之愈嚴則其發之愈勇”(《陳亮集·寄陳同甫書》)。朱熹認為,判斷政治的善、惡應以主觀動機,而不是以外在的事功作為評判標準。
對于何謂“天理”、何謂“人欲”,朱熹有自己獨特的見解。朱熹認為,“天理只是仁義禮智之總名,仁義禮智便是天理之件數”(《朱子語類》卷十三)。而對于“人欲”,朱熹認為,“人欲者,此心之疾疢,循之則其心私而且邪”,“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朱子文集》卷十二)。對于人欲,朱熹認為它有合理與不合理之分。他認為,“欲之好底如‘吾欲仁’之類”(《朱子語類》卷五),不好的則如“窮口腹之欲”,并且認為只有那種不好的或不合理的“私欲”、“嗜欲”才是人欲。
而對于天理與人欲的關系,朱熹認為,“圣人千言萬語,只是教人明天理,滅人欲”(《朱子語類》卷十二),“修德之實,在乎去人欲,存天理”(《朱子文集》卷三十七)。
正是從這樣的天理人欲觀出發,朱熹對浙東功利主義所堅持的王霸義利論進行了批判,并指出:“孟子所謂‘浩然之氣’者,蓋斂然于規矩準繩不敢走作之中,而其自任以天下之重者,雖賁育莫能奪也。是豈才能血氣之所為哉!老兄視漢高帝唐太宗之所為而察其心,果出于義耶,出于利耶?出于邪耶,正耶?……若以其能建立國家,傳世久遠,便謂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敗論是非。”(《陳亮集·附錄》)
對于陳亮的成人之道——“學成人而不必于儒,攪金銀銅鐵為一器而主適用”,朱熹也進行了批判,認為陳亮之論“其立心之本在于功利”。朱熹認為:“夫成人之道,以儒者之學求之,則夫子所謂成人也;不以儒者之學求之,則吾恐其畔棄繩墨,脫略規矩,進不得為君子,退不得為小人。正如攪金銀銅鐵為一器,不唯壞卻金銀,而銅鐵亦不得盡其銅鐵之用也。”(《陳亮集·附錄》)朱熹認為,成人之道應“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則利自在,明其道則功自在,專去計較利害,定未必有利,未必有功”(《朱子大全·送張仲隆序》)。
四、批判之批判:對道義論批判的反思
雖然以羅爾斯、朱熹為代表的道義論對功利主義政治哲學進行了深刻的理論批判,但是在批判他人的同時,對于這些問題道義論同樣也有著自己不解的困境。
首先,政治理念與社會現實的脫節。道義論雖然克服了功利主義效果論所帶來的“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簡單邏輯,在社會現實之上設立了一個為眾人普遍遵守的道德法則,認為在這種道德法則的維系下,人類政治生活會按正常的軌道發展,至少會成功地避免“人欲橫流”的社會出現,但是,在提出這種良善的道德原則之后,卻并沒有在理念與現實之間鋪架出一條筆直可見的橋梁。
對此,羅爾斯只設計出一道“無知之幕”,以此來去除人與人之間的利益偏見,從而實現其所謂的充滿正義的社會。相比羅爾斯,朱熹則仍堅持先賢們倡導的成圣之路,即“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是一條何等漫長之路,正是由于這一條路的漫長,才有了浙東陳亮“義利雙行、王霸并用”的事功之路。
其次,道義原則的普世性與現實理性多元性的矛盾。對于道義論而言,其最大的功績就是試圖找到一種終極道德,在這種道德法則所包含的園囿中,實現人類政治生活的有序化。然而,在現實生活中,這種終極道德又是不存在的,人類現實政治生活是以多元性的狀態而存在的。現實的多元性,造就了人類理性的多元性,正如墨子所言:“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其人茲眾,其所謂義者亦茲眾。”(《墨子·尚同上》)正是由于“義”的眾多,不具有統一性,“是以人是其義,以非人之義,故交相非也”(《墨子·尚同上》)。
可見,雖然道義論所倡導的初衷很好,但是現實理性的多元性又往往導致其道義原則的普世遭到阻礙,這也正是為道義論者所惆悵的,“江西之學只是禪,浙學卻專是功利。禪學,后來學者摸索,一上無可摸索,自會轉去。若功利,則學者習之便可見效,此意甚可憂”(《朱子語類》卷一二三)。
最后,道義原則的推行同樣不能避免犧牲的存在。雖然道義論一再反對功利主義“為了使很多人分享較大利益而剝奪少數人的自由”[11]23的做法,但是并沒有認識到:功利原則“在人們利益不發生沖突而可以兩全的情況下,表現為‘不損害一個人利益、增進每個人利益’原則;只有在人們利益發生沖突而不能兩全的情況下,才表現為‘最大利益凈余額’原則”,“‘最大利益凈余額’雖然在人們利益不相沖突領域必然導致非正義,卻是利益沖突領域的唯一正義的、正確的原則。因為在利益發生沖突的情況下,不損害任何人的利益是不可能的,而只能二者擇一”。[12]
道義論雖然對功利主義犧牲論提出批判,但是它并沒有解決當人們利益選擇出現二難選擇時會如何來處理。正如美國學者桑德爾在其《公正》所舉出的案例:一輛剎車失靈且在飛馳的有軌電車,突然發現前方軌道上有5名工人在作業,假設這時前方出現一條側軌,但其前方有1名工人在作業。在此情況下,司機直行會撞上5人,改道側行會撞上1人。這時,功利主義者會選擇側行,犧牲1人,而保全5人生命。而這時,道義論該怎樣選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