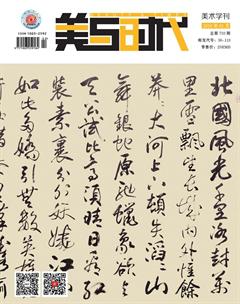《圣朝名畫評》的史料運用與寫作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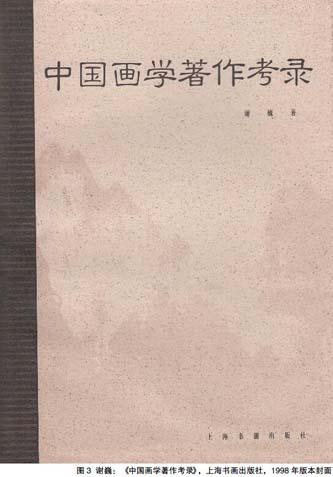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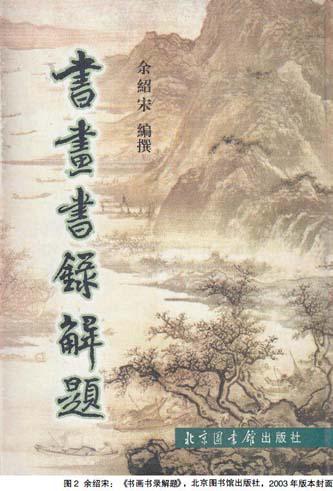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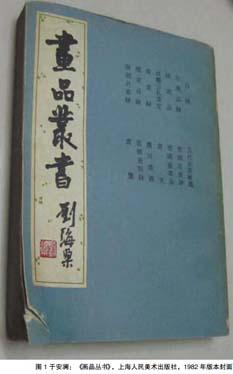
摘要:從史料運用與寫作特色上看,《圣朝名畫評》對畫家之生平、籍貫、心理性格、師承、文化教育背景、作品風格、歷史事件、繪畫史籍等基本史實均有明確記載,為我們了解和深入考察五代至北宋中后期的繪畫風格樣式與趣味的發展、繪畫史學發展、美術考古遺跡以及相關文化史等諸多問題提供了重要文獻依據。在體例上,此書采用將藝術家與作品進行分類列門、分品(神、妙、能)的記述手法,為后來的一些美術史著作如《宣和畫譜》奠定了新的撰寫格套。同時,它將畫家個人傳記的記述與畫評截然分開,也使其撰寫內容、結構較為清晰。而就歷史寫作意識與觀念而言,此書也透露出不盲目學習古人、不迷信古代畫家的特征。對一些重要畫家的風格趣味也進行了再認識,體現出本書撰寫時逐步形成的新品評趣味與觀念。總體來看,該書體例嚴謹,分科完備,史料剪裁運用得當。在嚴謹的歷史論述中又同時有理論建構。因此,不應當看作是宋代中后期單純的畫評著作,而是一部體例較為完備的兼具品評的繪畫史論著作。它客觀地反映出晚唐至宋代中國古代畫學著作出現史學化的某些傾向。在唐宋繪畫史學史上理應得到進一步重視、挖掘與研究。
關鍵詞:劉道醇;圣朝名畫評;史料運用;寫作特色;史學化傾向
一、問題的提出
自魏晉以來,中國就形成了以書畫評論鑒賞為中心的畫學著述模式。及至晚唐,伴隨著(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朱景玄《唐朝名畫錄》等著作的問世,嚴格意義上的中國美術史著作開始出現,其紀傳體的撰寫體例和史論結合的書寫格套也較為深刻地影響到了其后的中國美術史學的發展。延至宋代,則陸續又有了《益州名畫錄》《圣朝名畫評》《五代名畫補遺》《圖畫見聞志》《宣和畫譜》《畫繼》等一系列畫史著作的出現。在唐、宋社會轉型的思想文化變遷中具有重要意義。
《圣朝名畫評》由北宋中期的學者劉道醇撰寫,由宋至清曾陸續被《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宋史·藝文志》《絳云樓書目》《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等書多次著錄與考訂。[1] 對于此書的性質,按照近代一些學者的看法應該放入畫品、畫評領域中。如余紹宋在1932年出版的《書畫書錄解題》一書就將其放入品藻·品第類中。[2] 王世襄在1943年完成(當時未刊)的《中國畫論研究》中也曾指出:“《圣朝名畫評》自品評方面論,為比較成功之作品,大有詳細研究之價值。宋代品評之著作,可以劉道醇《圣朝名畫評》為代表,視唐代諸家,顯有改善。”[3] 其后,俞劍華在1957年出版的《中國畫論類編》中也明確將其放入品評類中。[4] 金維諾在1979年明確指出該書屬于評傳體斷代繪畫史。[5] 其后,于安瀾在1982年則將該書放入《畫品叢書》中,顯示出作者對此書性質的判定。[6] 盧輔圣在1993年主編的《中國書畫全書》第一冊中也對該著作進行了全文收錄,但也未指明該書的性質。[7] 謝巍在1998年出版的《中國畫學著作考錄》則并未明確判斷此書的性質,僅對其版本進行了考證。[8] 李一在2000年出版的《中國古代美術批評史綱》更是直接將其納入美術批評范疇。[9] 在2012年,任弈霏在《〈圣朝名畫評〉考》中倒是指出其書的性質為斷代體繪畫史,但可惜也并未再深入分析鉤沉。[10] 因此,在這些學者中也只有金維諾、任弈霏明確指出該書屬于評傳體斷代繪畫史,但并未作更深入討論,同時也似乎未引起學界足夠重視。
從以上的簡略回顧中,我們可看出該書自宋至清陸續被多次著錄考訂。民國以來的大部分學者則將此書的寫作性質定為繪畫品評、品藻性著作,而并未深入洞察它的史學價值與寫作特色,從而對該書的性質到底是繪畫品評,還是繪畫史著作莫衷一是。實際上,我認為如果從史料運用、寫作特色等方面去看,該書的撰寫顯示出較強的繪畫史學的性質,反映出晚唐五代至宋代,中國古代畫學著作出現的明顯史學化傾向。本文也將重點對該書顯現的史料運用和寫作特色展開必要分析梳理,以期進一步判定此書的寫作性質。
二、《圣朝名畫評》的史料運用與寫作特色
在仔細回顧學界對本書研究的基礎上,作者在下文中將對此書的史料運用和寫作特色進行分析。
第一,中國早期的繪畫品評著述一般來講不太重視對畫家的生平信息進行記錄,僅是對畫家的技藝、作品進行評價而已,這在《古畫品錄》《續畫品》中就非常明顯。但隨著唐代以后獨立的繪畫史著作出現,情況已經悄然發生了變化。無論是《歷代名畫記》還是《唐朝名畫錄》,一般均會對書中所錄畫家之生平、籍貫、字號、個人性格、佚事進行客觀記錄,并逐漸成為后世畫史著述的寫作格套。[11] 比前兩者撰寫時代較晚的《圣朝名畫評》也不例外。該書對所錄每一位畫家的生平、籍貫、字號、個人性格等最基本的歷史信息都有所如實記述,對于學界研究其生卒年與歷史軌跡有重要幫助。比如,對于王瓘,本書即記載他“字國器,河南洛陽人,美風表,有才辯”等基本的歷史事實。[12] 再比如,對于高益,本書記載“本契丹涿郡人,太祖時遁來中國。初于都市貨藥,有來贖者,輒畫鬼神犬馬籍藥與之,得者驚異。”寥寥數語,即將他的歷史軌跡和早期的藝術創作環境進行了大體的介紹。[13] 尤其是,作者還涉及到對一些畫家文化教育背景的記錄,如對于武宗元,曾有如下記述:“武宗元,世業儒,為鄉里所重。”而對于孫知微,也注意到他“知書,能論語,通老學”。對于趙元長,作者則記錄他“蜀中人,通天文。”[14] 以上這些材料都表明作者并沒有將所要選取的史料局限于單一的“藝術”領域,而是將畫家放入文化教育背景中去考察。這或許也表明自五代以后,學者在評鑒一位畫家的技藝優劣時,開始將文化修養水平列入考察的必要條件中,也表明唐代以后的學者在撰寫畫學著述時,對史料的剪裁、運用更為得體。
第二,此書對畫家進行繪畫創作時顯現的歷史事件、畫藝、心理性格特性等旁證性的文獻也多有記載。這種撰寫“格套”自南北朝時期的孫暢之撰寫《述畫》一文中即有出現,并在唐代以后的畫史著作中逐漸趨向于成熟。比如,其書曾經記述沙門元藹在一次作畫時被一宦官凌辱,后憑借其超人的繪畫功底找到其人,從而在畫壇上留下了一段佳話。[15] 又如,該書也同時記錄畫家高益、許道寧在北宋都城汴梁販賣藥品,同時將各類題材的畫作送給客戶。這些記載雖然簡略,但都為我們提供了一些寓居在汴梁的畫家早期的歷史佚事。[16] 而對于“攻寫貌、善佛像”的畫家尹質,該書則特別記述他在景祐中宣獻宋公去世后,其家人請他為宋公寫貌時,“嗜酒,無拘束,但草成儀像,逾時不往”的縱逸性格。[17] 而對于宋代著名畫家王拙之子王居正,《圣朝名畫記》則記載他“嘗于苑圃寺觀眾游之處,必據高隙以觀士女格態”。 [18] 寥寥數語,就將該畫家堅持細致觀察、對景寫真的樸實性格娓娓道來。其對畫家平時注重觀察、對景寫真的記述倒是頗與宋代初年黃休復在《益州名畫錄》中記錄晚唐畫家滕昌祐“常于所居樹竹石杞菊、種名花異草木,以資其畫”的寫作意識相合。[19] 總之,這些歷史記述雖然比較簡略,但對于我們細致研究該時期與畫家有關的歷史藝軌和北宋時代的士民生活、社會風俗還是較有幫助的。
第三,此書中對北宋時期大批畫家在各個地方的寺觀壁畫創作活動多有記述,對后世學者研究這一時期的美術考古遺跡具有較重要的文獻參考價值。
比如,該書曾記載王藹“于定力院寫宣祖及太后御容……又于大殿西壁畫水月觀音,反于景德寺九曜院殿西壁畫彌勒下生像。末年與東平孫夢卿畫開寶寺大殿后文殊閣下東西兩壁……”[20] 復如,此書也記述武宗元于北宋真宗景德末參與到玉清昭應宮、中岳天封觀、洛中南宮三圣宮、河南廣福院的壁畫創作活動。雖然相對而言,該書對他的壁畫創作并不詳盡。[21] 但是,此類記述卻可以和《圖畫見聞志》記述的他于“許昌龍興寺畫《帝釋梵王》、經藏院畫《旃檀瑞像》、嵩岳廟畫出隊壁”等壁畫創作活動形成一種有益的互補。[22] 一言以蔽之,這些資料的記錄都為我們還原那一時代的寺觀壁畫等美術創作活動提供了重要的文獻“標本”,值得特別注意。
第四,有意味的是,該書在記錄畫家的各種基本信息的同時也如實記載了一些在歷史上曾經出現但現在已經無存的繪畫史著作,體現出作者在歷史記述方面的寬廣視野。比如,本書“卷一·人物門”第一“王士元”條就記述了“唐有名畫斷,第其一百三人之姓名。(宋)太宗天縱多能,留神庶藝,訪其后來,復得一百三人,編次有倫,亦曰名畫斷。” [23] 由此,我們也可以獲知在北宋初年,宋太宗即仿照唐代《名畫斷》的體例,重新編撰過《名畫斷》一書。這一點尤其值得重視。
對此,謝巍曾經注意到:“唐代做《畫斷》者有三人,一為張懷瓘《畫斷》,其書非專門品評唐代名畫,而與南北朝、隋朝名畫為主,兼及唐開元以前諸名畫,而不合引文所述。二為朱景玄《唐朝畫斷》(一名《唐朝名畫錄》,《直齋書錄解題卷十四》《新唐書·藝文志》分別著錄為《唐畫斷》《唐朝畫斷》),據朱氏自序謂‘其余作者一百二十四人,即言國朝親王三人、吳道玄、周昉兩人未計在內,凡為一百二十九人。若外加序中評及非唐朝畫家陸探微計入,則為一百三十人。與引文所述人物相合。三為韋蘊《唐畫斷》,此書著錄有作一篇,或作一卷,系續朱氏之書,據篇幅多寡,斯篇人數當不及朱氏書作三卷之多,不過十多人,或數十人而已,因而不合引文所述人數。”[24] 由此,謝巍推測此書應該是繼續朱景玄之書,其續則始自唐大中,歷五代,而止宋開寶之前,其體例亦分為神、妙、能、逸四品,對于研究唐宋之際畫史體例的變遷也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第五,由寫作體例來看,此書主要按照人物門、山水林木門、畜獸門、花竹翎毛門、鬼神門、屋木門共六門分門別類式地記述藝術家及其作品,對同一位藝術家及其作品,也按照其繪畫技藝水平分別放入神、妙、能諸品中,而不盲目地迷信其社會地位與在畫壇上的影響力,比較客觀與公允。這與作者撰述的另一著作《五代名畫補遺》在結構體例上是較為相似的。[25] 比如,對于黃荃,本書第一卷“人物門”與第三卷“花木翎毛門”中,即按其繪畫技藝水平將其分別放入“妙品”與“神品”中,對他的繪畫技藝的討論尤其側重于花鳥畫方面。[26] 這也顯示出一方面,中國傳統繪畫在中、晚唐開始,繪畫門類分化越來越細致,藝術家的繪畫實踐也各有偏重。另一方面,在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完成以后,宋代學者在對同一位藝術家所從事不同藝術門類的評論上更加嚴謹與中肯一些。這或可反映出宋代學者的理性與客觀精神。
還需要指出的是,與作者撰述的另一著作《五代名畫補遺》有所不同,該書將畫家個人傳記的記述與畫評大體分開,這樣就使撰寫內容結構較為清晰,富有條理性,可謂分裁得體,也使得該書很好地將繪畫批評與繪畫史記述體例結合在一起。因而,我認為雖然該書的名稱為《圣朝名畫評》,但實際上卻兼具有繪畫批評與繪畫史的雙重特色。[27] 而反觀北宋晚期米芾《畫史》一書。雖然該書的書名被定名為《畫史》,粗看書名好像就是一般的繪畫史著述,在體例上該書也大體按照晉畫、六朝畫、隋畫、唐畫、五代畫、宋畫等年代序列來編排目次。但對于具體的每件作品,此書也只能做到僅列作者籍貫、名號(有些則不錄),并對作品進行鑒賞、評論,其體例與史料運用與剪裁比較凌亂,沒有什么章法,遠沒《圣朝名畫評》的寫作完備與細密,實際上米芾《畫史》反而更像是單純的繪畫品評類著作,與其書的名稱完全不合。[28]
第六,該書對各位畫家的風格評述顯然是建立在作者在序言中所提出的重要美術理論觀點——“六要”(氣韻兼力、去來自然、變異合理、彩繪有澤、格制俱老、師學舍短)與“六長”(粗鹵求筆、細巧求力、無墨求染、狂怪求理、僻澀求才、平畫求長)觀念之上的。從中也可看出理論與繪畫史寫作的密切關系。這也顯示出作者能夠在之前畫學理論上的基礎上提出較新的見解,而不盲目迷信經典。比如,作者在是書“人物門第一”對王瓘藝術風格的敘述與評論中,即注意到他的畫風“廢古人之短,成后世之長。不拘一守,奮筆皆妙”的特點。此種觀點,即與他提出的“六要”中的“師學舍短”一點不謀而合,其觀念也透露出不盲目學習古人、不迷信古代畫家的特征。 [29] 這種觀點,在作者綜合評論王瓘、王藹與孫夢卿的藝術風格中也有鮮明的呈現:“吾觀國器之筆,則不知有吳生矣。吳生畫天女頸領粗促,行步跛側。又樹石淺近,不能相稱。國器則舍而不取,故于事物盡工。復能設色清潤,古今無倫。恨不同時,親授其法。”“唐張懷瓘以吳生為僧繇后身,予謂夢卿亦吳生之后身。而列于瓘、靄之下,何哉?吳生畫天女及樹石有未到處,(語在王瓘事跡)。瓘、靄能變法取工,夢卿則拘于模范,雖得其法,往往襲其所短,不能自發新意,謂之脫壁者,豈誣哉?”[30] 這也表明作者在該節中選擇王瓘、王藹與孫夢卿這三人進行綜合比較也是有意為之。這段史料也體現出作者希望以當時衍生出的美術理論建構與參照畫史的觀念。
需要補充的是,同一時期成書的《圖畫見聞志》的相關論述也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相似的視角。如《圖畫見聞志》之“敘論:論古今優劣”中即認為“若論佛道、人物、士女、牛馬,則近不及古。若論山水、樹石、花竹、禽魚,則古不及近”也透露出這種觀念。[31] 英國歷史學家柯林武德曾經認為“一切歷史都是思想的歷史”,亦即,他較為強調客觀性歷史與主觀性歷史之間的緊密聯系。[32] 這一觀念在現在看雖然有所偏激,但它對于我們參照劉道醇、郭若虛在此處所呈現的畫史觀念還是有啟發性意義的。何兆武也曾經認為:“史料本身是不變的,但是歷史學家對史料的理解則不斷在變,因為他的思想認識不斷在變。歷史事實一旦如此則永遠如此,但是對于他的理解卻永遠都在變化。”[33] 因而,無論是歷史學家還是藝術史家都不可能超越他所處的那一時代。《圣朝名畫評》與《圖畫見聞志》里的這兩段史料似乎也能夠說明北宋中、晚期藝術史學者對那一時代藝術樣式、趣味變遷的敏感與思想上的回饋。
第七,此書對一些重要的美術家的風格進行了再認識,體現出本書撰寫時形成的新品評趣味。這對我們理解北宋中后期乃至南宋時代的繪畫趣味轉向是一個重要的參考。
比如,本書卷三,“花竹翎毛門”第四在對徐熙的藝術風格進行分析時曾經指出:“(黃)荃神而不妙,昌妙而不神,神妙俱完,舍熙無矣。”并進一步認為“江南絕筆,徐熙、唐希雅二人而已。極乎神而盡乎微,資于假而迫于真,象生意端,形造筆下。”寥寥數語,就將作者的推崇徐熙“落筆之際,未嘗以傅色暈淡細碎為功”的品評立場清晰地表述出來。[34] 相似的評判,在北宋晚期成書的《圖畫見聞志》與《宣和畫譜》中也有深刻顯現。如在郭若虛《圖畫見聞志》中,作者即認為徐熙畫法在當時“此真無愧于前賢之作,當時已為難得”。[35] 而在《宣和畫譜》中,對徐熙的褒獎也較為明顯。[36] 這似乎也預示著進入北宋晚期以后,受文人畫風尚與作者本人藝術趣味的影響,那一時代的美術史家開始致力于營建一種新視覺圖式與品評趣味的嘗試。
因此綜上所述,我認為《圣朝名畫評》的史料運用和寫作上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就史料運用而言,該書對畫家生平、籍貫、心理性格、師承、文化教育背景、作品風格、歷史事件、繪畫史籍等基本史料的記載,為我們了解和深入考察五代至北宋中后期的繪畫風格樣式與趣味的發展、繪畫史學發展、美術考古遺跡以及相關文化史等諸多問題提供了重要的文獻依據。它同時也展現出作者的這一兼具畫史與畫評的畫學著作,是以對畫家、作品為中心的“史料”進行較為扎實的史學梳理作為認知基礎的。這就與南北朝至隋唐時期出現的畫評著作《古畫品錄》《續畫品》《后畫錄》《續畫品錄》(《畫后品》)的寫作方式又有所不同。而與晚唐時期出現的《歷代名畫記》《唐朝名畫錄》等純粹的繪畫史著作在史料運用特色上高度相似,體現出《圣朝名畫評》在剪裁、運用史料方面的確更為嚴謹、細密與科學,也稱得上是明確的畫史著作。
第二,就該書的體例結構而言,與作者的另一部著作《五代名畫補遺》相似,此書采用將藝術家與作品進行分類列門、分品(神、妙、能)的記述手法,為后來的一些美術史著作如《宣和畫譜》奠定了新的撰寫格套。同時,它將畫家個人傳記的記述與畫評截然分開,也使其撰寫內容、結構較為清晰。其撰述手法屬于繪畫批評理論與繪畫史的綜合。在撰寫體例與敘述模式上應該或多或少地受《畫斷》《歷代名畫記》《唐朝名畫錄》的一些影響,并與同一時代出現的繪畫史著作如《圖畫見聞志》等書透露出的體例多有契合。從結構上來看也遠比同一時期前后撰寫的米芾《畫史》要嚴謹細致。
第三,就歷史寫作意識與觀念而言,此書也透露出不盲目學習古人、不迷信古代畫家的特征。比如,作者在是書“人物門第一”對王瓘的評述中,即注意到他的畫風“廢古人之短,成后世之長。不拘一守,奮筆皆妙”的特點。此種觀點,即與他提出的“六要”中的“師學舍短”一點不謀而合。此種觀念在一定程度上也透露出藝術技藝能夠不斷向前發展的進步性的歷史認知觀念。此外,該書對一些重要畫家的風格、趣味也進行了重新認識,體現出此書在撰寫時逐步形成的新品評趣味與藝術觀念。這對我們理解北宋中后期乃至南宋時代的繪畫趣味之重要轉向也是一個重要的參考。它同時也向我們顯示出作者在進行該著作的撰寫過程中,與那一時代的藝術趣味的變遷聯系極為緊密的特征。
三、結語
從本書的史料運用與寫作特色看,《圣朝名畫評》體例嚴謹,分科完備,史料剪裁運用得當,在嚴謹的歷史論述中又有理論建構。因此不應當看作是宋代中后期的畫評著作,而是一部體例較為完備的兼具品評、繪畫史事記述與分析的繪畫史著作。它客觀地反映出晚唐五代至宋代中國古代畫學著作出現嚴謹的史學化的一些傾向。王世襄曾指出:“郭若虛《圖畫見聞志》為續《歷代名畫記》者。《紀藝》中竟不論畫家之高下。可見品評之風,至宋而漸消沉。”[37] 這一敏銳觀察,也或許可作為我們理解《圣朝名畫評》《圖畫見聞志》等為代表的北宋時代畫史寫作觀念出現明顯變化的某種參照。此書在唐宋繪畫史學史上理應得到進一步重視與研究。在此僅將此文當做拋磚引玉之作,期待學界同仁批評指正。
(本文在撰寫過程中曾先后得到中央美術學院人文學院羅世平教授,河南大學藝術學院張自然副教授、董睿副教授等人的重要幫助,在此謹致謝忱!)
注釋:
[1]參閱(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宛委別藏版本),卷十五·藝術類,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443—444頁。(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十四·雜藝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12頁。(元)脫脫 等撰:《宋史·藝文志》,卷二百七,志第一百六:藝文六,中華書局,1977年,第5290頁。(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百二十九,經籍五十六,中華書局,1986年,第1831頁。(明)錢謙益:《絳云樓書目》,卷二,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第53頁。(清)紀昀 等撰:《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子部二二·藝術類,中華書局,1997年,第1485頁。
[2]余紹宋.書畫書錄解題·品藻·品第類[M].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317.
[3]王世襄.中國畫論研究[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225—232,231.
[4]俞劍華.中國畫論類編(上編)[M].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57:408—420.
[5]金維諾.北宋時期的繪畫史籍[J].美術研究,1979,(03):59—62.
[6]于安瀾.畫品叢書[M].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2:107—148.
[7]盧輔圣主編.中國書畫全書(第一冊)[M].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3:446—459.
[8]謝巍.中國畫學著作考錄[M].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8:132-133.
[9]李一.中國古代美術批評史綱[M].哈爾濱:黑龍江美術出版社,2000:220—223.
[10]任弈霏.《圣朝名畫評》考[J].藝術市場,2012,(19):74—75.
[11]張彥遠.歷代名畫記[M].范祥雍點校,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64.
[12][13][14][15][16][17][18][20][21][23][26][27][29][30][34]劉道醇.圣朝名畫評[M].于安瀾.畫品叢書.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2:116,118,119、122、125,127,118、133,127,128,
117,119,120,121、141,93—106,116,118,140.
[19]黃休復.益州名畫錄(卷下)[M].秦嶺云點校,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64:53.
[22][31][35]郭若虛.圖畫見聞志[M].黃苗子點校.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63:61-62,24-25,95.
[24]謝巍.中國畫學著作考錄[M].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8:108.
[25](宋)劉道醇.五代名畫補遺[M].于安瀾:《畫品叢書》版本,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2年,第93—106頁。但值得注意的是,《五代名畫補遺》的結構體例與《圣朝名畫評》又有些許不同。它主要由人物門、山水門、走獸門、花竹翎毛門、屋木門、塑作門、雕木門這七個門類構成。除鬼神門外,塑作門、雕木門這兩個門類被列入此書中也是值得特別注意的。
[28](宋)米芾.書畫史·畫史[M].北京:中國書店,2014:1—94.
[32][英]柯林武德.歷史的觀念[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15,115.
[33]劉北成,陳新.史學理論讀本[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60.
[36]于安瀾.畫史叢書(第二冊)[M].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63:203-204.
[37]王世襄.中國畫論研究[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231.
作者簡介:
劉曉達,廣東第二師范學院美術學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早期中國美術史與美術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