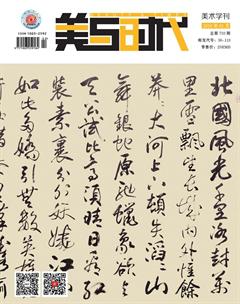王鐸《贈愚谷詩》與傅山《嗇廬妙翰》比較研究
呂田
摘 要:以王鐸、傅山的雜書卷冊為研究對象,對二者的書學宗法、漲墨、異體字的使用和章法等方面進行比較研究。通過對同一表現形式的分析,了解二者的書學追求與藝術特征的異同,得出其雜書卷冊書法內在及本質聯系。
關鍵詞:雜書卷冊;王鐸;傅山;《贈愚谷詩》;《嗇廬妙翰》;比較研究
王鐸、傅山的雜書卷冊是明末清初極具代表性的書法作品。兩人處于同一時代,相同的雜書表現形式,卻出現不同的藝術風格,在此選取二人創作時代相近的雜書卷冊進行對比研究。
一、時代背景
(一)晚明尚奇的時代風尚
晚明經濟的繁榮促使了教育事業的發展,使民眾的識字率上升,對讀物的大量需求使晚明的出版印刷業發達,各式出版物風格對先前經典的視覺風格頗具沖擊,晚明的書法藝術也受到了當時印刷文化的影響。
明代也是基督教和西方物質文化由天主教徒帶入中國的時代,擴展了國人對世界的認知,助推了明代尚奇風尚。
書法發展到晚明,傳統的帖學書法發展到了極致,一些書法家尋找變革和突破;明后期的社會變遷使得書法家以不同于傳統書法家的創作方式來排遣內心,這也是造成晚明奇異書風的一個重要方面。
17世紀的評論家使用的“奇”具有十分積極的含義,它是原創力的代稱,對藝術家和批評家而言,被稱為“奇”的作品正是代表這一時期審美理想的佳作。
(二)美學思想解放
明代市民階層的崛起,經濟領域以及意識形態都發生了巨大變化。思想文化領域出現了以解放個性為中心的王陽明心學。美學思想也不例外,在書法上主要是強調創作源于心靈,以師心代替師古,突破前人束縛,獨抒性靈。
(三)諸體兼備
明代刻帖盛行,較前幾個朝代的書家,此時的書家可以掌握多種字體。萬歷年間《曹全碑》出土,使書家耳目一新并加以學習;同時文學藝術領域開始關注古趣,遂有寫隸書的風氣。而篆書也因萬歷年間文人篆刻的興起受到重視。因此篆、隸兩種書體開始流行,書寫雜書卷冊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二、王鐸《贈愚谷詩》與傅山《嗇廬妙翰》的比較
(一)創作時代
王鐸(1592—1652),1645年于南明朝大學士任上降清,入清后任禮部尚書,7年后去世。他是明代草書最高成就的代表。四十歲左右時,作品由之前緊隨二王書風,逐漸開始形成了個人面目。《贈愚谷詩》是他在五十四歲(1647年)所作,已經展現出較為成熟的個人特點。
傅山(1607—1684),明末清初思想家、書畫家。明亡后,受道法,服道裝,法名真山等。康熙十八年(1679年)被舉應“博學鴻儒”科,固辭不準,至京師,疾甚,乃放還。真草篆隸無不精妙,尤長于草書。其書風從1640年代后期到1650年代初期開始發生變化。《嗇廬妙翰》作于1652年,此雜書卷冊中多種字體的展現,可作為多種字體書風變化的例證。
(二)作品概況
兩卷雜書冊均具有很大的隨意性,不是按照字體演變順序而作。
1.王鐸《贈愚谷詩》
現藏臺北何創時書法藝術基金會,分別用行書、章草、草書、楷書書寫了九首詩。此卷段落組成:(1)“盧嚴”段,大字楷書;(2)“拔劍”段,行書;(3)行書,宗法二王的“楷前行書”;(4)“繇東峰天池入支硎”段,楷書;(5)“洛山”段行書,于上一部分楷書結尾的下半段位置起首,行草書;(6)“云翼禹峰過”段,較大字行書;(7)“(文章)道不孤”段楷書大字,學顏真卿;(8)“至圣公相”段草書;(9)“東彭禹峰”段,于上一部分草書結尾的中上段位置起首,行書;(10)“愚谷”段,行書。
詩與詩之間字的大小差別較大。第一首詩的字比第二首詩的字約大一倍以上。第四首詩和第七首詩雖同為楷書,但第四首詩為中楷,第七首詩為大楷,段落感強。楷書行書學習顏真卿,中宮緊湊。筆畫硬直,按捺出挑,提按轉折明顯,運筆軌跡直且鋒利。
2.傅山《嗇廬妙翰》
由真、草、行、篆、隸及傅山自創的混合體寫出,由二十六個段落組成。[1]
整體字幅明顯小于王鐸,中宮較王鐸更放松,結體更顯敦厚。筆畫出鋒不似前期,運筆軌跡較王鐸彎,且平和含蓄。
(三)作品比較
1.相同點
(1)學書宗法相似
王傅二人皆由鐘繇、二王入手,均尊晉法,后取法顏真卿。
王鐸認為,學書未入晉則為野道。姜紹書在《無聲詩史》中評王鐸:“正書出自鐘無常。雖模范鐘王,亦能自放胸臆。”將王鐸在1646年作品《臨顏真卿八關齋會記》與《贈愚谷詩》的(7)段作對比,便可清晰地看出其繼承了顏氏衣缽。
傅山初從“二王”,曾遍臨晉唐法帖,對顏真卿在書品人品上都崇拜。白謙慎先生認為他的書法在17世紀50年代中期已轉向了顏真卿風格。傅山曾在約1650年作《臨顏真卿麻姑仙壇記》,在癸巳冬(1653年末或1654年初)的《小楷札記》,均可看出在其創作《嗇廬妙翰》前后對顏真卿書法的學習。
在行書方面,《嗇廬妙翰》中的第(7)段可與顏真卿《祭侄文稿》對比,風格接近且漲墨的使用相似。
《嗇廬妙翰》基本上是以鐘繇和王羲之的筆法寫小楷,以顏真卿的風格寫中楷,全篇書風均表現出顏氏風范。
(2)均使用了臨創的學習和創作方法
董其昌提出了臨摹應該神似重于形似[2],“臨創”風氣開始明顯出現在書法臨摹中。
王鐸作品中有不少是臨摹古代的法帖,但非嚴格的臨寫,而是隨意刪取法帖的片段或幾件拼合,結構、筆法只是以法帖為大致依憑,在前人作品的基礎上發揮。其中有許多成為他的代表作。
存世傅山的草書立軸中有相當數量是臨寫《淳化閣帖》和《絳帖》所收法書名跡,這些作品均受到“臨創”風氣的影響。
(3)異體字
書寫異體字是王鐸書法中的一個鮮明特色,《贈愚谷詩》中的異體字在楷書部分表現得最明顯。在第(4)段中開始便由一個大粗筆異體楷書與前段分格開來,此段中的楷書都運用增加筆畫的異體方法使視覺效果繁復,但整體筆畫又偏平直瘦硬,頗具建筑美感。第(7)段有異體字“鵬”“礙”“鎮”“有”“晚”“殘”“瑜”“曠”“走”“鳥”“趨”等,幾乎全段使用增減筆畫的異體字。由于此段學顏體,字幅碩大,筆畫粗壯,所以王鐸增加筆畫的程度少于第(3)段,既不讓觀者覺得臃腫,整段細讀來也妙趣橫生。
傅山在《嗇廬妙翰》中異體字使用量之大,讓人難以卒讀,但除去對內容的理解,我們依然承認異體字的使用增強了書法結構和用筆帶來的視覺美感。許多字使用了增加筆畫的異體方法,且多數字異體化的筆畫方向相似,使單字結構趨于方形,筆畫數差距變小,加之傅山在書寫不同字體時均敦厚用筆,造成了全篇疏密粗細分布均勻的渾然效果。
(4)章法
雜書卷冊中各段書法行數不同,所占全卷的寬窄比例不同;在高低上,每段語末尾位置不一,故章法錯落有致。書體多、書家書寫隨意,使全卷動靜互補,樸拙自然,綜合來看更能獲得多維的審美體驗,有1+1>2的作用,使審美不再停留于“一眼看穿”的單一書體的章法上。
2.不同點
(1)漲墨的使用
《贈愚谷詩》的材質是綾,且王鐸多用濃墨、粗筆,故多處出現漲墨,并使用墨繼法,通過增加墨繼次數追求墨色變化,漲墨位置隨機且間隔出現,拓展了墨色變化的范圍。
第(1)段起首“巖”字,雖然沒洇在一起,但作為起首,王鐸在書寫一開始便默許了漲墨情況;下一行的“彩”與一字之隔的“諸”也出現漲墨,但并未與“巖”在同一排;第三行中“貌”出現漲墨。漲墨連續三行都在中間區域,王鐸卻避免使三處處同一高度。無論是他有意設置還是筆者的過度解讀,都無法否認這樣安排的合理性。
需要注意的是,第(4)段字小筆細,多使用增加筆畫的異體方法,幾乎無漲墨,這說明漲墨的使用是王鐸的有意選擇。
傅山《嗇廬妙翰》中的漲墨更顯隨意。字幅全篇較王鐸的小,且篇幅長,書寫材質為紙。傅山也明顯使用了墨繼法,但不論大字粗筆還是小字細筆均出現漲墨,出現頻率大致相同且不高,因此《嗇廬妙翰》中的漲墨是一種墨繼書寫習慣。本卷篇幅長,不追求筆畫對比,字體結構疏松,筆畫規矩內斂均會降低墨色的豐富度,所以傅山主動接受漲墨的出現但不刻意為之,使一些直率的筆畫具有立體感,分布在傅山支離的字形中,全卷視覺節奏依舊均衡。
(2)篆隸筆法
王鐸是傳統帖學系統的書家,《贈愚谷詩》中草書的轉折處多使用源自于唐楷的“提按”動作。他自重草書,在談論漢碑時以篆法為宗,對于隸法相當漠然,其關注的是碑刻中古文字的字形,非后世碑學所追求的古拙意趣。[3]
傅山是碑學書法的倡導者,在草書中多使用源自于篆隸的“使轉”筆法。盡管從他早期行草作品來看,已發現多使用“使轉”而較少“提按”的趨勢,但不排除他運用了碑學筆法。
《嗇廬妙翰》第(18)段,在隸書中上溯篆書結構,即用隸筆寫篆書。并標注:“此法質樸,似漢之。此法遺留少矣。《有道碑》僅存典刑耳。”現在我們無法看到《有道碑》,但可知傅山追求古拙的漢隸筆法與王鐸頗不同。
三、結語
在晚明尚奇的氛圍中,雜書卷冊是基于諸體兼備的技能上,將形式的多樣性與內容的繁雜發揮到極致。
王傅二人的作品都將順暢閱讀的功用放在視覺欣賞之后,漲墨、異體字、行距不清等,使讀者難以順暢清晰讀下去。但這種書法創作中情感的表達,是二人創作中的自覺表現。這種有意識的發掘,強調了書法除去實用性之外的觀賞性。他們受惠于那個時代,綜合了前人帖學與碑學的成就,批判學習,為書學重新賦予時代新意做出了各自獨特的貢獻。
注釋:
[1]白謙慎.傅山的世界[M].北京:三聯書店,2016:163,168.
[2]朱惠良.臨古之心路:董其昌以后書學發展研究之一[J].故宮學術季刊,1993,(03).
[3]薛龍春.崇古觀念與王鐸書作中的“奇字”[J].藝術學研究.2007,(00).
參考文獻:
[1]白謙慎.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紀中國書法的嬗變[M].北京:三聯書店,2016.
[2]楊建峰編.中國傳世書法[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1.
作者單位:
西北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