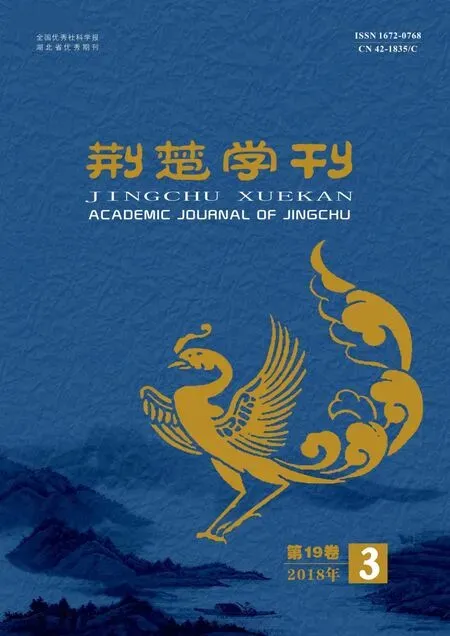劉海章教授學術(shù)研究綜述
(荊楚理工學院 文學與傳媒學院,湖北 荊門 448000)
劉海章(1936—2016),又名涂宗流,湖北省荊門市人。1960年畢業(yè)于華中師范學院中文系,同年分配到湖北江漢師范學院(后改為江漢師專,荊州師專前身,現(xiàn)并入長江大學)工作。1962年調(diào)回荊門,先后擔任中學、中專語文教師。1983年任荊門市教師進修學校校長、華中師范大學荊門函授站站長。1987年評聘為湖北省成人高校副教授。1990年任荊門大學學術(shù)委員會主任,1992年兼任湖北省社會科學院荊門分院文史所所長。1993年6月晉升為教授。曾任湖北省語言學會常務理事、副秘書長,全國漢語方言學會會員,湖北省楚國歷史文化學會會員。主要從事語言學、現(xiàn)代漢語方言學以及地域歷史文化研究,在語言學、地方史和楚文化等方面都有被學術(shù)界重視的研究成果,先后出版研究著作10余部,發(fā)表論文60余篇(1)。
從時間上說,劉海章教授的學術(shù)研究工作可以1996年為界,分前后兩期(2)。1996 年前,劉教授主要從事語言學的教學與研究,出版了《文言句讀通釋》(合著,文心出版社,1986)、《古代漢語簡明教程》(撰寫音韻部分,中國地質(zhì)大學出版社,1988)、《文言字詞句》(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荊楚方言研究》(合著,華中師大出版社,1992)等四部論著,尤其在“荊楚方言”方面的研究具有開創(chuàng)性,在語言學研究領(lǐng)域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此一階段,劉教授還主編了《荊門歷史風貌》(武漢出版社,1993)、《荊門史話》(第一卷主編,中國三峽出版社,1994),為荊門地方史研究做出了開創(chuàng)性的貢獻。論文《春秋楚都地理位置辯》(1995)以翔實的文獻資料對春秋楚都不在今江陵紀南城作了頗有說服力的論證,對楚學界產(chǎn)生重要影響。
1996 年以后,他潛心于楚文化研究,專攻“郭店楚簡”和“陸九淵心學”。主要論著有《郭店楚簡先秦儒家佚書校釋》(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2001)、《郭店楚簡平議》(國際炎黃文化出版社,2002)、《郭店楚簡研究》(香港銀河出版社,2002)、《道之源——郭店老子研究》(汕頭大學出版社,2006)、《德之華——郭店楚簡儒書研究》(中國三峽出版社,2010)、《陸子心語》(國際炎黃文化出版社,2002)等,其“郭店楚簡”系列研究在國內(nèi)外有較大影響。下文結(jié)合劉教授的代表性論著對他的學術(shù)研究成果加以分析。
一、語言學研究
刊發(fā)在《中學語文》1980年第4/5期合訂本的《“生的偉大 死的光榮”語言內(nèi)部結(jié)構(gòu)的我見》是現(xiàn)在所能知道最早發(fā)表的一篇文章。當時,劉教授還在中學教語文,所寫論文多半發(fā)表在《中學語文》上,往往是他教課之心得,體現(xiàn)出他熱愛語文、勤奮探索的教育和治學態(tài)度。這類文章還有《現(xiàn)代漢語“是”字認定句》(《中學語文》1981年第3期)、與《“是……的”辨》(《中學語文》1982年第4期) 等。
1983年起,劉教授開始擔任荊門市教師進修學校校長,教學的課程從“現(xiàn)代漢語”轉(zhuǎn)為“古代漢語”,研究發(fā)表的論文也同時轉(zhuǎn)向。如發(fā)表于《字詞天地》1984年第2期的《古代漢語所字詞組中的“所”》與發(fā)表于《荊楚語言學刊》的《古代漢語V+N2+N1結(jié)構(gòu)》(1986年第1期)、《短語述論》(1986年第1期)、《反切語今讀》(1987年第2期)、《漢字的形、音、義》(1987年第5、6期)等,分別對古代漢語中的“所”字詞組、動詞與名詞的搭配、短語、反切、漢字等問題進行了研究探索,涉及面比較廣泛。專著《文言字詞句》(1989)則是一部別具體裁的古代漢語研究力作。
先生對于普通語言學與古漢語的研究探索,可以用《迷惘、反思、探索——中國現(xiàn)代語言學研究述略》(《社會科學研究》1989年第2期)作為一個小結(jié)。此外,先生退休前所作《試論漢字的寫詞方法》(《荊門大學學報》1993年第2期)則可視作前期研究興趣的余緒。
1987年,作為華中師范大學荊門函授站站長的劉先生被評聘為湖北省成人高校副教授,從這一年起,他的語言學研究又一次轉(zhuǎn)向,開始以一位具有深厚語言學功底的荊門學者的身份研究本土的方言。這類論文有《荊門話的狀態(tài)助詞“噠”》(《荊楚語言學刊》1988年第2期)、《湖北荊門話中的“V人子”》(《語言研究》1989年第1期)、《荊楚方言瑣議》(《荊楚語言學刊》1989年第1期)、《荊門話與普通話比較記略》(《荊楚語言學刊》1989年第2期)、《荊楚顫音探源》(《荊門大學學報》1990年第3期)等。如:《湖北荊門話中的“V人子”》一文針對荊門話中“V人子”這樣一種比較特殊的語言結(jié)構(gòu)(“子”念[r],顫音,是個詞尾),與山西文水話中的“V+人”結(jié)構(gòu)進行了比較。認為荊門話“V人子”具有以下不同:1. V不限于“表示外界刺激人體某一部分而引起不舒服感覺的動詞”;2.“V人子”中不能插入其他成分,但“V人”之間可以插入表示程度的“死”。
同時,上述文章與其同期發(fā)表的關(guān)于個體認識語言學的論文互為表里(3),終于促成其在方音辨正學上自成一家,產(chǎn)生出《語言是言語和思維的統(tǒng)一產(chǎn)物》(《荊州師專學報》1989年第4期)、《現(xiàn)代漢語方言與民族共同語》(《荊門大學學報》1994年第3期)、《方言腔調(diào)辨正》(《荊門大學學報》1996年第2期)、《方音辨正的理論基礎》(《荊門大學學報》1996年第3期)這些具有較大影響的語言學理論研究成果。如《語言是言語和思維的統(tǒng)一產(chǎn)物》認為:意象思維和直覺言語的統(tǒng)一是語言產(chǎn)生的起點;在言語和思維的統(tǒng)一中長期聚合語言成素,形成語言;在有語言的人類社會,思維離不開語言;語言在言語與思維的統(tǒng)一中形成,在言語與思維的對立中發(fā)展。此文具有相當深厚的思辨功底,暗示著劉先生日后的思想史研究之路。《方言腔調(diào)辨正》一文認為方言腔調(diào)辨證是學習普通話進行方音辨證的重要內(nèi)容之一。不同方言腔調(diào)的區(qū)別,一是聲音,二是語氣。方言腔調(diào)辨正的內(nèi)容主要有兩個,一是以聲調(diào)為中心的包括連續(xù)變調(diào)在內(nèi)的說話語調(diào);二是以特定語氣詞的特殊發(fā)音為中心的語氣。以荊門為例,作者認為20世紀50年代以前的荊門人說話高而促,之后,由于受荊門煉油廠工人(多東北話)的影響,音高下降,變得舒緩,且屈調(diào)漸亡,多直調(diào)。荊門是古荊楚的中心地帶,北有楚皇城,東有郊郢,南有楚紀南城,荊門話具有代表性的語氣有噠、沙、些、啵、子等,其中“些”(今讀se)、“子”(讀顫音r)都是源于《楚辭》的語氣詞。先生認為荊門人學普通話,在方言腔調(diào)辨正上,除了調(diào)整聲調(diào)調(diào)值以外,恐怕要下功夫丟掉表現(xiàn)荊門方言語氣的幾個有代表性的語氣詞。從方言研究來說,荊楚顫音是十分重要的方言現(xiàn)象,但從學習普通話來說,這卻是應該丟掉的。《方音辨正的理論基礎》認為普通話語音與方言語音之間的對應規(guī)律是學習普通話進行方音辨正的理論基礎。語音對應首先是各方言語音與所從出的母語語音的對應(歷時對應),反映方言語音對母語語音的繼承和演變規(guī)律。其次是從出于同一母語的各方言語音之間的對應(共時對應),反應方言語音演變的差異性。1997年7月,在“首屆官話方言國際學術(shù)討論會”上,剛剛榮退的劉教授以《荊楚方言的形成及其特點》為題向大會作了專題報告,其觀點受到參會的國內(nèi)外專家的肯定。所有這些,均反映出劉教授的語言學研究并非停留在理論層面,而是有著對于現(xiàn)實的關(guān)懷和生命的溫度。
在語言研究方面,劉先生還有《毛澤東著作中的并列分承句法現(xiàn)象》一文載入《毛澤東著作語言論析》(湖北教育出版社,1993)一書,該書于毛澤東誕生一百周年出版,在語言學界也有重大影響。《荊楚方言研究》(1992)一書中,對今天屬于北方方言的荊楚方言從古到今縱向的演變和當今地理上橫向的分布都做了充分地論證。特別是對荊楚方言所特有的(顫音)的音值和它的產(chǎn)生及區(qū)域分布了詳盡的描述,為語言學界所重視[1]。
二、荊門地方文化研究
荊門地方文化的研究并非劉教授致力較多的領(lǐng)域,但也在荊門地理、荊門地方文化名人兩個方面有所涉及,且形成一定的影響。如其《春秋楚都地理位置辯》(《荊門大學學報》1995年第1期)一文,從殷商至春秋古荊楚的地理形勢以及楚滅國擴疆的歷史進程中的有關(guān)歷史事件,來辨識春秋楚都的地理位置。通過《詩經(jīng)》《左傳》《呂氏春秋》及當代研究成果等翔實的文獻資料,對前輩學者童書業(yè)、石泉所持“春秋楚郢都不在今荊門市紀山之南的紀南城遺址,而應在宜城縣南(偏東)約15公里的楚皇城遺址”這一說法作了頗有說服力地論證,在楚學界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類似的文章還有《古代荊門的地理位置和水陸交通》(《荊門大學學報》1993年第3期)。
對荊門地方文化名人的研究,劉先生關(guān)注較多的是曾在荊門任知軍的宋代思想家陸九淵,且在先生的研究中儼然成為一個專門的領(lǐng)域,故于后節(jié)專論,此處不贅。對與荊門相關(guān)的另外兩位文化名人老萊子與關(guān)羽,先生則有《試論老萊子的“隱”和“孝”》(合撰,《荊門大學學報》1994年第1期)、《關(guān)羽與荊門》(《荊門大學學報》1994年第4期)等文章論及。在《試論老萊子的“隱”和“孝”》一文中,結(jié)合有限的史料,對荊門歷史上第一位文化名人——“二十四孝”之首的老萊子生平及思想進行考證:他是一位德恭行信、安貧樂道的哲學家,他于楚靈王三年(前538)隨族人遷至鄢;楚惠王三年,老萊子在鄢地會見孔子。楚惠王八年(前481)楚國公室“白公之亂”,逃耕于蒙山之陽。他雖然一生“言道家之用”,主張“治人事天”“清靜為天下定”,卻又以“隱”“孝”聞名于世。他的“隱”是對楚靈王及以后諸位楚王行霸政的不滿;他的“孝”,則是人性復歸意義上的“純孝”。二者看似淵源不同,但實則互相關(guān)聯(lián)。正像清代荊門知州舒成龍所說:“余謂萊子之孝,非隱無以成之;萊子之隱,唯孝益能終之。”(《荊門直隸州志·老萊山莊》)在《關(guān)羽與荊門》一文中,則結(jié)合史料,對關(guān)羽鎮(zhèn)守荊州的大本營進行考證,通過多方鉤稽,再從語言學的角度,結(jié)合歷史地名和地方傳說,認為三國時期關(guān)羽的軍營本部當在今荊門南郊的掇刀石。
三、陸象山心學研究
《禮記·學記》云:“時教必有正業(yè),退息必有居學”。劉先生任教時,以語言學、古代漢語為正業(yè);退休之后,則出于對曾任荊門知軍的“百世大儒”——陸九淵的興趣,開始閱讀張立文先生的《陸九淵評傳》,逐漸萌生了研究陸九淵思想的想法[2]386,此后約有兩年左右的時間沉潛在《陸九淵集》的閱讀與思考之中。終于從1999年起,以涂宗流的筆名發(fā)表了一系列關(guān)于象山其人與“象山心學”的論文與著作。
《不能讓“事實湮于意見”——就陸九淵研究與張立文先生商榷》(《荊門職業(yè)技術(shù)學院學報》1999年第1期)是劉先生研究象山心學的發(fā)軔之作。此文首先就張立文先生所說荊門軍治所在“湖北當陽”的說法進行了辨析,劉先生據(jù)《陸九淵集》中十則自述之郡治地理與《宋史·地理志》(荊湖北路)之三條記載,尤其是荊門軍移治當陽的時間在“端平三年”(1236年,距象山離世已43年)之材料,斷定“當陽”說的謬誤;其次,就張先生此文斷句兩處發(fā)出疑問,并就斷句之不同引發(fā)的張先生對“象山心學”中“有諸己”和“此心澄瑩中立”等思想的曲解進行辨析。
緊接著劉先生又撰寫了《應歷史地評價陸九淵——就陸九淵荊門之政與張立文先生商榷》一文。張立文先生在《陸九淵評傳》中對陸九淵的荊門之政評價并不高,說了三件并不光彩的事情:一是防止和鎮(zhèn)壓農(nóng)民起義;二是聯(lián)合鄰郡,搜捕地方“逃卒”;三是修郡學,講學授徒,宣揚主觀唯心主義。以今日之眼光來看,張先生的觀點有著鮮明的時代特色,并不是科學客觀地認識陸象山的態(tài)度,劉先生出于對荊門先賢的景仰,力辯其誣,雖有袒護之心,卻能實事求是。劉先生從陸九淵荊門之政的歷史背景、憂國忘家的思想基礎、鎮(zhèn)壓農(nóng)民起義事實不足等方面分析張論之誤,又勾稽大量史料總結(jié)陸九淵荊門之政的四件大事:一曰備戰(zhàn)練兵,鞏固次邊;二曰建立保伍,除暴安良;三曰整頓稅收,開源節(jié)流;四曰移風易俗,正乎人心[2]387-389,[3]。
上述兩篇與張立文先生探討的文章更多地還只是關(guān)于生平、背景的核證,真正探討象山心學的文章是劉先生的“陸九淵心學九辨”系列論文(4)。在這組論文中,劉先生認為:陸象山的“心即理”說不是“主觀唯心主義的宇宙觀”,也不是主觀唯心主義的哲學命題,而是陸象山對現(xiàn)實人生的哲學觀照,是張揚人的主體意識的心學的理論基石;“先立乎其大者”是以怎樣“大做一個人”為前提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是象山理想人格對宇宙的一種態(tài)度,是“與天地合其德”的一種自我表白;“此心此理,實不容有二”是對天下正理的張揚;象山弟子徐仲誠“如鏡中觀花”是關(guān)于心物(內(nèi)外)關(guān)系的譬喻,是反對物欲、保有人之本心的提倡;象山所說“本心”即仁義之心,“本心”的去存是區(qū)分君子、小人的重要標準,因而也具有澄清吏治的作用;象山“天道”“人道”是貫通的,皆可從人性之道求之;“格物是下手處”既切近“人情物理”(倫理),又有著超倫理的指向;“自反”是為學、明理的根本路徑,與“用心多馳騖于外”者相異,“無我”則是“忘己”,是明理、致知所達到的一種精神境界(5)。
劉先生關(guān)于陸九淵研究的總結(jié)可以《陸子心語序說》為代表,此文系他為著作《陸子心語》所作的序。在序文中,他認為:象山人格是憂國憂民、無私無畏;象山哲學是發(fā)明本心、堂堂正正做人;研究陸象山,要心通意解,著著就實。正是本著“心通意解,著著就實”的研究態(tài)度,所以,他扎扎實實地讀象山文集,逐字逐句地詮解其“平時書句與所作文字”,以“講習稽考”的功夫匯纂成《陸子心語》一書,由為學、明道、察理、立心、做人五篇分而析之。要之,劉先生注重的是陸象山讀書、學問“不求聲名,不較勝負,不恃才喬,不矜功能”,只求保有“至大、至剛、至直、至平、至公”的正大純粹人格的高尚品格,可謂象山八百余年后的知音人。
四、郭店楚簡研究
1993年10月在紀山古墓群中發(fā)現(xiàn)的郭店1號楚墓,出土有字竹簡730枚,發(fā)現(xiàn)先秦時期儒家、道家文獻共18篇,13 000余字。其中簡本《老子》據(jù)竹簡長短分甲、乙、丙三篇,是迄今為止所見最早的《老子》版本,且“老子丙”中有14枚不見于傳世本《老子》;而楚簡儒書中的《五行》《性自命出》《唐虞之道》《語叢》等均是儒家經(jīng)典中罕見的篇章,其文獻學價值及思想史意義之重大,引起許多著名學者的重視。1998年5月,《郭店楚墓竹簡》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進入新世紀,已經(jīng)完成陸九淵研究的劉教授帶著學術(shù)日新的氣象,又開始投身于郭店楚簡的研究。劉先生對于郭店楚簡這一出土文獻的研究,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工作:一是篇章結(jié)構(gòu)研究;二是文字研究;三是分句通釋。如發(fā)現(xiàn)《絕智棄辯》(老子甲)第22簡中“我欲不欲而民自樸”之后有個不同于分章記號(小墨方塊)的“し”(勾形)符號,而此符號前后又存在“佐人主治國之策”與“佐人主治國之德”的區(qū)別,將之定為分篇符號。再如,《絕智棄辯》(老子甲)第1簡中的“民復季子”,劉先生據(jù)《玉篇·子部》認為“季子”即稚子,“復季子”與“復歸于嬰兒”意思相近。又如《絕智棄辯》(老子甲)第13簡中“道恒亡為也”的“為”,先生認為與“亡為而亡不為”中的“為”不同,他據(jù)俞樾《諸子平議·莊子·養(yǎng)生主》引《廣雅·釋詁》“取,為也”,“然則‘為’亦猶‘取’也。”認為“亡為”即“無所求取也。”[4]3
劉先生在重視出土文獻文字釋義的同時,也重視文本社會的、歷史的因素。比如,他認為《治人事天》(老子乙)第1簡中“治人事天”的說法,不應出于戰(zhàn)國時期,具有春秋時代的思想特征[4]3。在《郭店楚簡道家作品芻議——郭店楚簡與老子、老萊子、關(guān)尹子》(《荊門職業(yè)技術(shù)學院學報》,2002年第2期)一文中,他認為傳世本《老子》是道家后學中佼佼者對道家思想高度整合之作,其作者當是《史記·老子傳》中的楚國苦縣厲鄉(xiāng)曲仁里人李耳。《郭店楚簡》中的道家作品三冊是傳世本《老子》成書之前就存在的有關(guān)道家思想的著述。《絕智棄辯》(老子甲;簡長32.3cm、兩端修成梯形的39枚)、《治人事天》(老子乙;簡長32.3cm、兩端修成梯形的39枚)應是春秋道家原創(chuàng)者思想的表述,其作者可能分別是老子、老萊子,擬或是老子、老萊子的弟子對老子、老萊子思想的表述。《大一生水》(含老子丙;簡長32.3cm、兩端修成梯形的39枚),似為關(guān)尹子所作,其“大一”理論與《莊子·天下》所記述的關(guān)尹“主之以太一”的思想相一致。
在不到五年的時間里,他先后完成了《郭店楚簡先秦儒家佚書校釋》(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2001)、《郭店楚簡平議》(國際炎黃文化出版社,2002)這兩部著作。略晚些的《郭店楚簡研究》則是先生與幾位荊門地方學者合撰之作,其中,文獻注、釋、譯部分也出自先生手筆。這種文獻整理的基礎性工作,既可見劉先生深厚的語言文字功底,也可看出他嚴謹勤奮的學術(shù)態(tài)度。
在撰寫編著這些著作前后,先生寫下了大量札記,如“郭店楚簡校釋札記”“郭店楚簡《老子》校文釋補”“郭店楚簡《語叢》編連問題的思考、再思考”等。對郭店楚簡的思想史意義及其現(xiàn)實意義也進行了比較深入的思考,著作如:《道之原——郭店老子研究》(汕頭大學出版社,2006)、《德之華——郭店楚簡儒書研究》(中國三峽出版社,2010);論文如:《對世界本原的理性回答——評郭店楚簡中老子的“道”》(《沙洋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1年第1期)、《對天下大治的哲學思考——評郭店楚簡老子乙“言道家之用”》(《沙洋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1年第2期)、《郭店〈老子〉與今本〈老子〉的比較研究》(《荊門職業(yè)技術(shù)學院學報》2003年第5期)、《郭店〈老子甲〉的“道”與“德”》(《荊門職業(yè)技術(shù)學院學報》2004年第1期)、《郭店〈老子乙〉的“日損”與“清靜”》(《沙洋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5年第2期)、《學習和研究〈郭店儒書〉的現(xiàn)實意義》(《沙洋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7年第1期)、《〈郭店楚簡〉與中華文明——讓中華文明的元典永放光芒(上)》(《沙洋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7年第4期)、《〈郭店楚簡〉的哲學思想與構(gòu)建和諧社會——讓中華文明的元典永放光芒(下)》(《沙洋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8年第1期)等。在《道之原——郭店老子研究》中,劉先生以文字的全面核校為基礎,通過郭店《老子》與今本《老子》的比較,尤其將郭店《老子甲》《老子乙》《太一丙》與老子的“修道德”,老萊子的“言道家之用”,關(guān)尹、李耳論“道”聯(lián)系起來思考,以追溯《老子》文本的源頭,可視為論文《郭店楚簡道家作品芻議——郭店楚簡與老子、老萊子、關(guān)尹子》的拓展。在《德之華——郭店楚簡儒書研究》中,劉先生結(jié)合楚簡《六德》《五行》《魯穆公》《唐虞之道》《忠信之道》論述早期儒家的“道德論”(人倫情感、人性追求、道德理想與操守),結(jié)合《性自命出》《窮達以時》論述早期儒家的“天道論”(天命與人性、人性與人情、人情與人道、人道以身為主心、早期儒家窮達觀),結(jié)合《緇衣》《尊德義》《君子于教》論述早期儒家的“人道論”,均能切近史料,不作空談。
通過對郭店儒書的深入研究,劉先生對孔子的仁學思想還有較為新穎的探索,他認為孔子仁學是對社會人生的觀照,是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內(nèi)容的政治倫理哲學。孔子說“仁”,是從不同的角度表述(或為“達德”、或為“心之德”、或為“善之道”、或為“克己”、或為“愛人”)。在孔子的仁學話語中,“人”是社會的人。孔子認為真正的“人”要“知天命”“明道”“行道”。孔子的仁學,以有別于西方世俗化人文主義的東方社會化人文主義為其思想基礎,要求“人”參與社會、關(guān)心天下,求得“己身”與“他者”和諧一致(6)。
通過對劉海章教授學術(shù)生涯的梳理,可以發(fā)現(xiàn),無論是任教還是退休,先生始終筆耕不輟,以學術(shù)為己任。雖然部分觀點尚可商榷,論著內(nèi)容時有重復,但始終能注重將學術(shù)研究與荊門的地方文化相聯(lián)系,堅持學以致用的理論態(tài)度,堅持不同流俗的學術(shù)思考,體現(xiàn)出他在學術(shù)研究中的堅韌毅力與生命熱度。
注釋:
(1) 參考黃漢江主編:《中國社會團體會長秘書長辭典》,上海:上海科學技術(shù)文獻出版社,1999年,第332頁;陳建初、吳澤順主編:《中國語言學人名大辭典》,長沙:岳麓書社,1997年,第523頁;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劉海章/55703?fr=aladdin.
(2)以1996年為界的兩期之劃分,參考張曉珍《荊門市檔案館為老教授建專題檔案》,《中國檔案報》2007年2月8日第4版,論著介紹部分有增補。
(3)如《影響個體語言習得的諸因素》(《荊門大學學刊》1989年第2期)、《論個體言語認知的發(fā)展》(《荊門大學學報》1991年第4期)、《言語活動·語言和言語》(《高師函授學刊》1991年第5期)、《論言語認知與智力、非智力諸因素的關(guān)系》(《高師函授學報》1992年第3期)等。這些論文對語言的本質(zhì)作了新的解釋,對普通語言學理論的豐富的有重要參考價值。
(4)含“心即理”辨、“先立乎其大者”辨、“宇宙便是吾心”辨、“此心此理,實不容有二”辨、“如鏡中觀花”辨、“心、本心”辨、“道、理”辨、“格物是下手處”辨、“自反、無我”辨。
(5)九辯要旨分別見于涂宗流《陸子心語》,香港:國際炎黃文化出版社,2002年,第404、412、418、421、433、447、460、473、485頁。
(6)涂宗流、劉丹,《孔子仁學思想新探》刊于《沙洋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6年第1期,第5-8頁,此文后收入《德之華——郭店楚簡儒書研究》,中國三峽出版社,2010年。
參考文獻:
[1] 陳建初,吳澤順.中國語言學人名大辭典[K].長沙:岳麓書社,1997:523.
[2] 涂宗流.陸子心語[M].香港:國際炎黃文化出版社,2002.
[3] 涂宗流.陸九淵荊門之政功不可滅[J].撫州師專學報,1999(2):89-92,97.
[4] 涂宗流.郭店楚簡平議·前言[M].香港:國際炎黃文化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