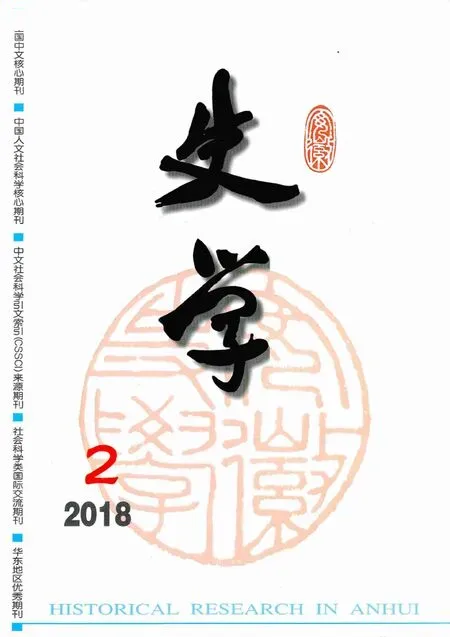從同姓到同宗:宋明吉安地區(qū)的宗族實(shí)踐
黃志繁
一、提出問(wèn)題
學(xué)術(shù)界關(guān)于中國(guó)宗族的研究,已經(jīng)達(dá)到了相當(dāng)高的水準(zhǔn)。可以說(shuō),已經(jīng)基本超越了功能主義的傾向,而從中國(guó)社會(huì)制度和歷史發(fā)展的實(shí)際出發(fā)來(lái)認(rèn)識(shí)宗族問(wèn)題。科大衛(wèi)和劉志偉認(rèn)為,宗族的發(fā)展實(shí)踐,是宋明理學(xué)家利用文字的表達(dá),改變國(guó)家禮儀,在地方上推行教化,建立起正統(tǒng)性的國(guó)家秩序的過(guò)程和結(jié)果。①[英]科大衛(wèi)、劉志偉:《宗族與地方社會(huì)的國(guó)家認(rèn)同:明清華南地區(qū)宗族發(fā)展的意識(shí)形態(tài)基礎(chǔ)》,《歷史研究》2000年第3期。或因宗族研究成果相對(duì)集中于廣東、福建、香港和臺(tái)灣等地區(qū)的緣故,學(xué)術(shù)界對(duì)明清以來(lái)宗族組織的發(fā)展歷程研究雖然已相當(dāng)深入,但對(duì)宋至明初宗族組織的演變并沒(méi)有很清晰的描述,從而導(dǎo)致對(duì)宋明時(shí)期宗族組織的實(shí)踐和具體運(yùn)作缺乏深入的了解。根據(jù)錢(qián)杭的研究,無(wú)論是上古經(jīng)典文獻(xiàn),還是后來(lái)的宗族實(shí)踐活動(dòng)都表明,宗族是“父系單系世系”“建構(gòu)”的產(chǎn)物,而不是“血緣”關(guān)系自然延伸的產(chǎn)物。②錢(qián)杭:《宗族建構(gòu)過(guò)程中的血緣和世系》,《歷史研究》2009年第4期。不過(guò),該研究并沒(méi)有涉及到宋明時(shí)期宗族建構(gòu)的過(guò)程。實(shí)際上,從宋代到明代宗族組織的發(fā)展,最為核心的當(dāng)是“宗法倫理庶民化”,即宋明理學(xué)家們的宗族建構(gòu)開(kāi)始突破宗法的限制,突破祭祀祖先的代數(shù),從而使宗族組織建立有了理論上的依據(jù)。③鄭振滿:《明清福建家族組織與社會(huì)變遷》,福建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然而,從宗法倫理理論上的突破到宗族實(shí)踐并非一蹴而就的。④可參見(jiàn)鄭振滿:《莆田平原的宗族與宗教——福建興化府歷代碑銘解析》,《歷史人類學(xué)學(xué)刊》第4卷第1期,2006年4月;劉志偉:《鄉(xiāng)豪歷史到士人記憶:由黃佐自敘先世行狀看明代地方勢(shì)力的轉(zhuǎn)變》,《歷史研究》2006年第6期;常建華:《明代宗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60—398頁(yè)。
迄今為止,關(guān)于宋明時(shí)期宗族組織發(fā)展的研究中,仍有一個(gè)關(guān)鍵問(wèn)題尚未厘清,即宗族組織是以何種方式建立起來(lái)的。正如錢(qián)杭論文所指出的,宗族組織是“世系建構(gòu)”的產(chǎn)物,不是血緣發(fā)展的結(jié)果,那么,一群有著同樣姓氏的人,是如何“建構(gòu)”起他們的宗族組織的呢?賀喜對(duì)北宋歐陽(yáng)修所編《歐陽(yáng)氏譜圖》流變的考察,非常精彩地揭示了不同地域的歐陽(yáng)氏后人,通過(guò)不同層次的遷移傳說(shuō),和圖譜建立聯(lián)系,建立實(shí)體性宗族的過(guò)程。在賀喜看來(lái),宗族起初只是一個(gè)概念或理想,后來(lái)混合了地方經(jīng)濟(jì),就成了實(shí)體化的宗族。⑤賀喜:《〈歐陽(yáng)氏譜圖〉的流變與地方宗族的實(shí)體化》,臺(tái)灣《新史學(xué)》2016年冬季卷。即使如此,我們依然可以追問(wèn),宋明時(shí)期的地方宗族實(shí)踐者是如何突破宗法倫理的代數(shù)限制,而在實(shí)際生活中“創(chuàng)造”出一個(gè)宗族組織的。⑥D(zhuǎn) avid Faure:The Lineage as a Cultural Invention:The Case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Modern China,Vol.15,No.1(Jan.,1989),pp.4—36.一個(gè)明顯的事實(shí)是,在朱熹的理論中,家廟祭祀只能由自己上溯到高祖,而只祭祀五代顯然是無(wú)法建構(gòu)起一定規(guī)模宗族組織的。因此,從理論或概念化的宗族到實(shí)體化的宗族實(shí)踐,除了賀喜所指出的認(rèn)同共同的宗族圖譜和經(jīng)濟(jì)因素之外,應(yīng)該還有若干世系的組織原則需要確認(rèn)和運(yùn)用。
江西吉安地區(qū)自宋代以來(lái)就是經(jīng)濟(jì)發(fā)達(dá)、人文繁榮的區(qū)域,宗法理論實(shí)踐出現(xiàn)的也比較早。北宋時(shí)期,歐陽(yáng)修就在他的家鄉(xiāng)永豐縣修撰了家譜,為吉安地區(qū)的宗族實(shí)踐作出了表率。宋明時(shí)期,吉安地區(qū)的修譜和建祠等宗族實(shí)踐活動(dòng)比較頻繁,特別是修譜活動(dòng),蔚然成風(fēng),至今留下了大量的譜序和譜論,為我們研究該時(shí)期吉安地區(qū)的宗族建構(gòu)活動(dòng)打下了較好的史料基礎(chǔ)。本文即擬對(duì)宋明時(shí)期吉安地區(qū)的宗族實(shí)踐展開(kāi)研究,并由此討論其宗族組織演變的相關(guān)理論問(wèn)題。
二、同姓而不同宗:宋代吉安歐陽(yáng)氏的修譜活動(dòng)
北宋皇祐四年(1052年),在外為官多年的歐陽(yáng)修帶著母親的靈柩回到了永豐,將母親與父親合葬在家鄉(xiāng)鳳凰山瀧岡之后,撰寫(xiě)了著名的《瀧岡阡表》。熙寧三年(1070年),歐陽(yáng)修在青州太守任上,將《瀧岡阡表》碑立于父母親安葬地不遠(yuǎn)的道觀西陽(yáng)宮中,碑石正面刻《瀧岡阡表》,背面刻《歐陽(yáng)氏世系表》。在《瀧岡阡表》中,他闡述了修《歐陽(yáng)氏世系表》的緣由:“嗚呼!為善無(wú)不報(bào),而遲速有時(shí),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于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shí)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jiàn)于后世,而庇賴其子孫矣!”⑦歐 陽(yáng)修:《瀧岡阡表》,《歐陽(yáng)文忠公集》卷25,《景印文淵閣四庫(kù)全書(shū)》第1102冊(cè),臺(tái)灣商務(wù)印書(shū)館1986年版,第202頁(yè)。可見(jiàn),《歐陽(yáng)氏世系表》不在于修撰一個(gè)完整的歐陽(yáng)氏族譜,而是通過(guò)修撰世系,彰顯其父親的善德,使其能庇佑后世。所以,雖然《歐陽(yáng)氏世系表》對(duì)后世影響巨大,但從族譜修撰的角度來(lái)看,并不嚴(yán)謹(jǐn),甚至有很多錯(cuò)漏。⑧《歐陽(yáng)氏世系表》有多種版本傳世,賀喜已經(jīng)進(jìn)行了詳細(xì)的比對(duì),并認(rèn)為石本和刻本雖然有很多不同,但世系基本相同。
南宋吉安地方大儒歐陽(yáng)守道就委婉地批評(píng)歐陽(yáng)修所修世系存在問(wèn)題:“予歐陽(yáng)氏家吉州自唐中世刺史府君始,大約距今五百余年。子孫散居諸邑,或徙他州,不可盡考。姑以見(jiàn)居而未徙者言之,戶不啻百計(jì),丁不啻千計(jì)矣,其間最著僅文忠公一人,自刺史府君視子孫,可謂最著者之少也。族譜非最著者,其誰(shuí)宜為?宜乎公之為之也!然公譜未廣,又頗有誤……文忠公游宦四方,歸鄉(xiāng)之日無(wú)幾,其修譜又不暇咨于族人,是以雖數(shù)世之近,直下之派,而屢有失亡。”①歐陽(yáng)守道:《書(shū)歐陽(yáng)氏族譜》,《巽齋文集》卷19,《景印文淵閣四庫(kù)全書(shū)》第1183冊(cè),第664—665、665頁(yè)。在歐陽(yáng)守道看來(lái),歐陽(yáng)修是廬陵地區(qū)歐陽(yáng)氏最為著名的人物,族譜理應(yīng)由他來(lái)修,但是歐陽(yáng)修公務(wù)繁忙,在家鄉(xiāng)的時(shí)間太少,所以所修世系即使離他最近的都“屢有失亡”。族譜修撰不嚴(yán)謹(jǐn)導(dǎo)致的后果就是,雖然同為廬陵歐陽(yáng)氏,但各派系之間都有自己的族譜,且互相之間族譜世系并不吻合。歐陽(yáng)守道繼續(xù)說(shuō)道:“予前后所見(jiàn)同姓諸譜,但在廬陵諸邑者已六七本,各巨帙細(xì)書(shū)。至鄰郡清江、宜春、長(zhǎng)沙同姓亦各有譜,往往出以相示,參較上世,率不相合,皆無(wú)一本略同者,此不可曉也。安得遍與諸家借聚,與民先細(xì)訂之乎!姑識(shí)此以俟他日。”②歐陽(yáng)守道:《書(shū)歐陽(yáng)氏族譜》,《巽齋文集》卷19,《景印文淵閣四庫(kù)全書(shū)》第1183冊(cè),第664—665、665頁(yè)。可見(jiàn),歐陽(yáng)修所修之世系并沒(méi)有起到統(tǒng)一各地歐陽(yáng)氏的作用,到了南宋末年,吉安地區(qū)的歐陽(yáng)氏各自修撰自己的家譜,并無(wú)統(tǒng)一的世系。所以歐陽(yáng)守道并不認(rèn)為他與歐陽(yáng)修有共同的世系,而廬陵之所以稱為“歐鄉(xiāng)”也和歐陽(yáng)修沒(méi)有關(guān)系。③賀 喜:《〈歐陽(yáng)氏譜圖〉的流變與地方宗族的實(shí)體化》,臺(tái)灣《新史學(xué)》2016年冬季卷。可見(jiàn),雖然歐陽(yáng)修所修的世系成為后世歐陽(yáng)氏建構(gòu)的基礎(chǔ),但是至少到南宋末年,遍布吉安地區(qū)大大小小的歐陽(yáng)姓,并沒(méi)有共同認(rèn)可的世系。嚴(yán)格地說(shuō),吉安歐陽(yáng)氏只是一群群的同姓?qǐng)F(tuán)體,并沒(méi)有整合成一個(gè)“宗族”。
歐陽(yáng)氏的情況并非個(gè)案。明初解縉回憶楊萬(wàn)里家族時(shí)說(shuō):“楊氏既多,所至迭盛。予嘗觀其閫鄉(xiāng)譜、大同譜、四院譜、龍圖譜、靖共兩院譜、蜀中院譜、渡江院譜、浙院譜、浦城譜、吉水楊莊譜、上徑譜、湴塘譜、小南江譜、今翰林楊公士奇所輯泰和譜。何其隨寓而盛也!龍圖已上不待言矣!其曰‘靖共’者,長(zhǎng)安坊名,其在唐元和長(zhǎng)慶間一院不下數(shù)十百口,族長(zhǎng)堂前有木榻,朝退問(wèn)安,擲笏其上,堆積明旦亂取以去,俸錢(qián)所入,至逾百萬(wàn),祿仕之盛,古未有也。”④解 縉:《泰和楊氏族譜序》,《文毅集》卷8,《景印文淵閣四庫(kù)全書(shū)》第1236冊(cè),第714—715頁(yè)。從解縉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即使到了明初,吉安楊氏共有14種之多,且各有譜系,還遠(yuǎn)達(dá)不到整合成一個(gè)“宗族”的要求。有些譜,例如“靖共”譜,更多的還是在追憶唐時(shí)的繁盛,向往大家族族人大多出仕為官的夢(mèng)想。聯(lián)系歐陽(yáng)氏和楊氏的情況,我們可以看出,宋朝到明代初年,吉安各大家族雖然有建立宗族的愿望,但是更多的是向往魏晉隋唐以來(lái)世家大族的榮光,這些同姓?qǐng)F(tuán)體和明中期以后南方地區(qū)普遍出現(xiàn)的“宗族”組織還有很大的差距。常建華系統(tǒng)地考察了明代吉安地區(qū)宗族組織的發(fā)展和理論基礎(chǔ)后,提出了“故家論”,認(rèn)為明初以楊士奇為代表的吉安士大夫?qū)⑿拮V的實(shí)質(zhì)定位于延續(xù)魏晉以來(lái)的“故家”傳統(tǒng),正是基于這一史實(shí)作出的判斷。⑤常建華:《明代宗族研究》,第360—398頁(yè)。
實(shí)際上,北宋時(shí)人大多認(rèn)為,大宗譜法很難繼續(xù),唯有“以五代為限,五世則遷”的小宗譜法可以修撰。⑥錢(qián) 杭:《中國(guó)古代的世系學(xué)》,《歷史研究》2001年第6期。歐陽(yáng)修在修完《歐陽(yáng)氏譜圖》后,曾經(jīng)對(duì)此進(jìn)行過(guò)詳細(xì)的闡述:“譜圖之法,斷自可見(jiàn)之世,即為高祖,下至五世玄孫而別自為世。如此,世久子孫多,則官爵功行載于譜者不勝其繁。宜以遠(yuǎn)近親疏為別,凡遠(yuǎn)者、疏者略之,近者、親者詳之,此人情之常也。玄孫既別自為世,則各詳其親,各系其所出。是詳者不繁,而略者不遺也。”⑦歐 陽(yáng)修:《集本歐陽(yáng)氏譜圖序》,《歐陽(yáng)文忠公集》卷21,《四部叢刊初編》第49—50冊(cè),臺(tái)灣商務(wù)印書(shū)館1967年版,第532頁(yè)。歐陽(yáng)修并不認(rèn)為族譜修撰可以無(wú)限制地追溯遠(yuǎn)祖,不斷地?cái)U(kuò)大規(guī)模,而是應(yīng)嚴(yán)格區(qū)分親疏,以上自高祖,下自玄孫為核心纂修。因?yàn)橐粋€(gè)人最多有可能活著見(jiàn)到自己的高祖,即上延五世,同理下延五世,到了玄孫輩則應(yīng)“別自為世”。另一位族譜大家蘇洵也表達(dá)了類似的觀點(diǎn)。他說(shuō):“凡今天下之人,惟天子之子與始為大夫者,而后可以為大宗,其余則否。獨(dú)小宗之法,猶可施于天下。故為族譜,其法皆從小宗。”⑧蘇 洵:《族譜后錄上篇》,《嘉祐集》卷14,《景印文淵閣四庫(kù)全書(shū)》第1104冊(cè),第951頁(yè)。蘇洵與歐陽(yáng)修所修族譜對(duì)后世影響很大,所謂“歐體”“蘇體”成為后世修譜的兩種重要體例。⑨相比之下,“歐體”的影響更為深遠(yuǎn)一些。歐陽(yáng)修開(kāi)創(chuàng)了宋代的士風(fēng)、文風(fēng)和學(xué)風(fēng),是宋代士大夫的“人格典范”,也是“歐體”風(fēng)靡天下的重要原因,參見(jiàn)范衛(wèi)平:《歐陽(yáng)修理性人格及其對(duì)現(xiàn)代人格建構(gòu)的啟示》,《南昌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13年第1期。但是,他們都基本恪守“小宗之法”的宗法倫理原則,不對(duì)宗族世系做無(wú)限制的擴(kuò)展。在這種理論指導(dǎo)下,不難理解,宋代吉安歐陽(yáng)家族為什么無(wú)法統(tǒng)一世系,成為嚴(yán)格意義上的宗族了。
在具體實(shí)踐中,過(guò)于苛守小宗之法,顯然無(wú)法適應(yīng)家族人口擴(kuò)張的需求。特別是在宋代的江西,大家族特別多,小宗之法的局限性非常明顯,歐陽(yáng)守道就提及廬陵歐陽(yáng)氏“戶不啻百計(jì),丁不啻千計(jì)矣”。實(shí)際上,正是由于“小宗之法”的局限過(guò)于明顯,在歐陽(yáng)修所撰寫(xiě)的世系中,也已突破了上追5世的限制,而是追溯到了9世,即從歐陽(yáng)萬(wàn)至他自身。在譜論中,歐陽(yáng)修也沒(méi)有明確指出要限制世系上追5世,而只是強(qiáng)調(diào)了以5世為核心的原則,這應(yīng)是對(duì)現(xiàn)實(shí)的一種變通。無(wú)論如何,宋代的吉安地區(qū),雖然存在許多同姓大家族,但他們各自為陣,沒(méi)有形成統(tǒng)一的世系,最多只能是同姓,而不是同宗。
三、同姓而同宗:忠節(jié)楊氏的世系建構(gòu)
楊萬(wàn)里家族是吉安地區(qū)另一具有重要影響的大家族,家族因出了南宋末年堅(jiān)守建康城而英勇就義的“忠襄公”楊邦乂和以文章節(jié)義聞名于世的“文節(jié)公”楊萬(wàn)里,而被稱為“忠節(jié)楊”。關(guān)于宋代楊氏宗族的史料,目前能找到的只有清嘉慶二年(1797年)刻印的《楊氏人文紀(jì)略》中的兩篇文獻(xiàn)。①該文獻(xiàn)為本人在吉水縣湴塘楊萬(wàn)里故居考察時(shí)所獲得。一篇為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年)楊存所作,一篇為宋寧宗慶元五年(1198年)楊萬(wàn)里所作。楊存所作的《楊氏流芳譜系序》摘錄如下:
文友生輅,仕江南李氏,始遷廬陵,初為虞部侍郎,出知吉州刺史,因家居廬陵郡,今為楊氏一世祖。輅生二子,曰銳曰鋋。銳生宏嗣,宏嗣生二子。曰延安為上徑高祖,曰延規(guī)為楊莊中高祖。鋋生宏徹。宏轍生二子。曰延宗為湴塘高祖;曰延邦為江南高祖。謂之江南,即吳里小江之南,是為本族高祖。延邦生子七人。曰戩為曾祖。戩生五子,曰倫為祖。倫生二子,曰郊為考。考生三子。長(zhǎng)曰布季,次曰本次,即存也。二世祖鋋為海昏令,即今建昌縣。三世祖宏徹有墓在東岡山落水塘。高、曾、祖、考先塋咸在,歲圮不替。自輅始遷,子孫世為廬陵儒行士族,繼有顯者。元祐間改為吉水中鵠鄉(xiāng)人也。存重念楊氏綿遠(yuǎn),中間分為四族,圖以示來(lái)者,庶知源流不紊也。其詳載家譜。宋徽宗宣和五年七月中元孫朝請(qǐng)大夫通判洪州主管神霄□清□□□□□□□□□田事存謹(jǐn)序。②楊存:《楊氏流芳譜系序》,《忠節(jié)楊氏人文紀(jì)略》卷1《譜序》,清嘉慶二年刻本。

楊存曾擔(dān)任過(guò)洪州通判,后被封為“中奉大夫”,其事跡載入《吉水縣志·名宦》中,歷史上應(yīng)真有其人。從《楊氏人文紀(jì)略》后面的相關(guān)記述來(lái)看,這篇譜序無(wú)疑是楊氏宗族里程碑式的作品。其重要意義在于,確立了楊輅為廬陵始祖,并從楊輅往下,至延字輩,共分為“四族”,分別為上徑、楊莊、江南、湴塘四支,從而排列出了完整的世系,使原本散處吉水各地的楊氏宗族有了共同的譜系。更重要的是,楊存還為楊氏的世系制作了圖,使其世系更為清晰。這一世系圖示如上欄。
楊氏后世所修族譜均大致照抄楊存排列出來(lái)的祖先系譜,正如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楊氏族譜序所言:“是吾族雖本源侍郎,而支流則始盛于四世,故八世中奉公起而譜其世次,此吾族之有譜所自也。”③楊嘉謨:《續(xù)忠節(jié)總譜記》,《忠節(jié)楊氏人文紀(jì)略》卷 1《譜序》。“中奉公”即楊存,可見(jiàn)到了清代,楊氏族人仍認(rèn)為他們宗族世系是楊存所編定的。與楊存的序相比,楊萬(wàn)里的序就顯得比較謹(jǐn)慎。今摘錄其序文如下:
輅之二子銳、鋋居廬陵城中。其居楊家莊,自銳徙也,今延安、延規(guī)之子孫,其后也;居湴塘者,自鋋徙也,今延宗、延邦之子孫,其后也。二族自國(guó)朝以來(lái)至于今,第進(jìn)士者十有三人。楊莊居其九,曰丕、曰純師、曰安平、曰求、曰同、曰邦、曰邁、曰炎正、曰夢(mèng)信;湴塘居其四,曰存、曰杞、曰輔世、曰萬(wàn)里。蓋楊氏自太尉伯起以來(lái),大抵以忠孝文學(xué)相傳。而近世卓然冠吾族者,忠襄公也。公之死節(jié),余既為之行狀,上之史官,已有傳矣。而十三人者,公父子及其二孫,凡一家而四人焉……其《唐表序》《呂夏卿大同譜序》《中奉府君族系圖序》,今列篇首,俾來(lái)者有所稽焉。宋寧宗慶元五年己未六月一日孫通奉大夫?qū)毼拈w侍制致仕萬(wàn)里謹(jǐn)序。④楊萬(wàn)里:《重修楊氏譜序》,《忠節(jié)楊氏人文紀(jì)略》卷 1《譜序》。
楊萬(wàn)里序最為明顯的變化是,楊存序中的“四族”變成了“二族”,即直接將銳和鋋作為楊莊和湴塘的始祖,而不是從“延”字輩算起。但楊萬(wàn)里序文重點(diǎn)似乎不在祖先世系,而重在強(qiáng)調(diào)楊氏人文興盛,對(duì)祖先源流和世系,表現(xiàn)的也比較慎重,申明把“《唐表序》《呂夏卿大同譜序》《中奉府君族系圖序》”放在族譜前面,希望將來(lái)有所考證。《中奉府君族系圖序》即楊存宣和五年所作的族圖,表明楊萬(wàn)里對(duì)楊存所列世系是有疑問(wèn)的。盡管楊萬(wàn)里無(wú)心考訂家族世系,但他無(wú)意中把楊輅在吉水的分支由“四族”變成“二族”的說(shuō)法,卻對(duì)后世影響很大,后來(lái)的楊氏族譜基本上都延續(xù)了這種說(shuō)法。
我們無(wú)法判定兩篇序文的真假,楊萬(wàn)里的序也不見(jiàn)于他的《誠(chéng)齋集》。但我們可以判定,這兩篇序至少應(yīng)為明初及以前的作品。明初,吉水名人解縉曾為泰和楊氏作過(guò)長(zhǎng)篇序言,中間對(duì)楊萬(wàn)里的序有大段引用。解縉的序載入他的文集,真實(shí)性比較高。解縉《泰和楊氏族譜序》中,指出明初楊氏家族分支較多,譜牒也比較混亂,而且沒(méi)有共同的世系,所以他花了很多篇幅考證始祖楊輅。解縉序?qū)钍霞易遄畲蟮呢暙I(xiàn)在于,他成功地考證了楊氏始祖楊輅不是如楊萬(wàn)里等人所認(rèn)為的在南唐李氏時(shí)期定居廬陵,而是后吳(即五代楊行密所建吳國(guó))時(shí)期定居廬陵。這一觀點(diǎn)被后來(lái)該族歷修族譜所采用。①解縉:《泰和楊氏族譜序》,《文毅集》卷8,《景印文淵閣四庫(kù)全書(shū)》第1236冊(cè),第714—715頁(yè)。
真正將楊氏紛繁復(fù)雜的世系統(tǒng)一起來(lái)的是明宣德年間擔(dān)任廣西副憲的楊瑒,他在宣德八年(1433年)主持重修了族譜。他有序文記述其經(jīng)過(guò),指出在修譜之前,楊氏族人楊義方已經(jīng)修訂了族譜,這個(gè)族譜雖然被楊瑒?wù)J為“欠考索”,但影響卻極大,“諸本皆因之”,因此,楊瑒才下定決心在繁忙的行政事務(wù)之余重新修訂。楊瑒這次修譜,采用的是從“中奉公”楊存到解縉所反復(fù)考訂的世系。楊瑒的修譜活動(dòng),是對(duì)族中存在的各種版本族譜進(jìn)行修訂和考證,有疑問(wèn)的則仍其舊,存疑待后人來(lái)解決。楊瑒還強(qiáng)調(diào)了職業(yè)正當(dāng)(儒、農(nóng))方可入譜,如果行為有辱先德,則將其除名,即所謂“為儒、農(nóng)者皆詳注其派;如有失身玷先德,則黜而弗錄”。②楊瑒:《楊氏重修族譜序》,《忠節(jié)楊氏人文紀(jì)略》卷 1《譜序》。楊瑒修訂族譜的根本目的就是要統(tǒng)一“忠節(jié)楊”氏的世系,將所有的楊氏族譜統(tǒng)一成一個(gè)大家認(rèn)可的“官方”版本。至此,自南宋開(kāi)始比較混亂的“忠節(jié)楊”氏終于正式統(tǒng)一了世系。值得注意的是,根據(jù)道光《吉水縣志》記載,楊瑒是“忠襄公之后”,③道光《吉水縣志》卷22《人物志·宦業(yè)》,臺(tái)灣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1225頁(yè)。即不是湴塘楊氏,而是楊莊楊氏,所以他組織在湴塘修祠和修譜活動(dòng),應(yīng)該包括了兩支楊氏。正如下文所說(shuō),經(jīng)過(guò)他的努力,楊氏有了統(tǒng)一的世系、祠堂和族譜,這兩支楊氏的宗族建設(shè)應(yīng)該說(shuō)基本完成了,所謂“忠節(jié)楊”也就成了世系完整且統(tǒng)一的宗族。
與此同時(shí),與吉水相鄰的泰和縣,另一位在地方社會(huì)有重要影響的人物楊士奇,成功地將自身家族與吉水楊輅家族聯(lián)系在一起。楊士奇在為其家譜作序時(shí)有比較清楚的解釋:“文友生輅,來(lái)居廬陵郡中,則廬陵楊氏始祖也。廬陵府君二子,銳徙吉水楊家莊,鋋徙吉水湴塘。銳之孫延安又徙上徑,延安孫允素始徙泰和,則泰和楊氏始祖也。泰和楊氏族故有譜刻石置縣西延真觀,元季觀毀于兵,石壞刻本亡逸,士奇求之廿余年不得。近得族父與芳翁寄示所修《譜圖》一帙,其間傳系失于接續(xù)者,亦多矣。竊懼其益久而益廢也,乃本《譜圖》所載,準(zhǔn)歐陽(yáng)氏五世以下別自為世之法,而統(tǒng)錄之。其傳系失于接續(xù)者,皆仍舊位置,而詳注于下方。庶幾延真刻本有出,可以參補(bǔ),名曰《泰和楊氏族譜》。”④楊 士奇:《泰和楊氏族譜序》,《東里集續(xù)集》卷13,《文淵閣四庫(kù)全書(shū)》第1238冊(c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24—525頁(yè)。根據(jù)楊士奇的說(shuō)法,泰和楊氏族譜本來(lái)是刻石放在延真觀中的,但元末毀于兵火,他根據(jù)族人保留的譜圖,重新修撰了族譜。按照他的說(shuō)法,泰和楊氏的始祖乃是從吉水楊家莊遷來(lái)的,自然也就和吉水楊氏系出同源了。
楊士奇還仿造楊存,為泰和楊氏的世系修了譜圖。他修族譜和譜圖的態(tài)度是比較嚴(yán)謹(jǐn)?shù)?“士奇既作《楊氏族譜》,而欲便于觀覽也,又作此圖,且欲刻之分畀族之人……此圖上自府君輅始遷廬陵,以再遷泰和,于今廿有三世。其間或書(shū)字、或書(shū)名、或書(shū)行、或書(shū)號(hào)者,凡四百九人。失其字名、行號(hào),但書(shū)某以識(shí)之者十有五人,總四百二十四人。夫譜泰和之族,必自廬陵府君始者,尊吾所從出,且舊圖之錄也,其上失系屬者……皆仍舊圖位置,庶幾傳疑之意。而今廿二世以下子孫尚多。此但載舊圖所錄及士奇所知者。蓋族人散處,且士奇仕于外,不得訪錄,姑明其統(tǒng)系之緒而已。統(tǒng)系明,將后有繼修者,得緣此而錄也。”⑤楊士奇:《泰和楊氏重修族譜圖序》,《東里集續(xù)集》卷12,第515—516頁(yè)。楊士奇在修族譜和譜圖時(shí),參考的是族人的舊圖和各派的分譜。在制訂譜圖時(shí),對(duì)一些有缺失的世系,仍按照舊圖照錄,不隨便增加和添補(bǔ)。近世的族人,則根據(jù)他自己所了解的真實(shí)情況收錄,經(jīng)過(guò)嚴(yán)格的修訂,該族譜和族圖共登錄了424人。
通過(guò)這次修譜,楊士奇家族和楊萬(wàn)里家族擁有了共同的祖先。可以推測(cè),由于吉水楊氏這一支擁有崇高的地望(涌現(xiàn)了楊邦乂和楊萬(wàn)里等名人,號(hào)為忠節(jié)楊氏),許多周邊的楊姓也紛紛通過(guò)建構(gòu)世系,在系譜上加入其家族。楊士奇這次修族譜活動(dòng)也可以看成明初吉安地區(qū)修族譜活動(dòng)的一個(gè)縮影。
經(jīng)過(guò)一系列的努力,到了明初,吉水楊氏基本上確立了始遷祖和排列出了基本的世系,周邊的楊氏也建立了和吉水楊氏的聯(lián)系。即使如此,楊氏家族的“宗族建設(shè)”還只停留在整理和建構(gòu)祖先譜系的層面,和明中期以后南方普遍出現(xiàn)的“宗族”組織還有很大的差別。
四、“忠節(jié)”傳統(tǒng)與“忠節(jié)楊氏”的形成
南宋時(shí)期,吉水楊氏聲譽(yù)漸隆。他們首先在科舉上獲得了巨大的成功,楊萬(wàn)里對(duì)此頗為自豪,他曾在給人寫(xiě)的記文中提及家族舉業(yè)的輝煌:“宋中興以來(lái)……臨軒策士,凡二十有三,得人眾矣,不可得而詳已。惟我大江之西,有一族而叔侄同年者,一時(shí)艷之,以為盛事,若予與故叔父麻陽(yáng)令諱輔世是也;有一家從兄弟同年者,若予族叔祖忠襄公之二孫曰炎正、曰夢(mèng)信是也;有產(chǎn)兄弟而同年者,若吾州印岡之羅曰維藩、曰維翰,蘭溪之曾曰天若、曰天從是也。”①楊萬(wàn)里:《靜庵記》,辛更儒箋校:《楊萬(wàn)里集箋校》卷76,中華書(shū)局2007年版,第3141頁(yè)。在他列舉的三個(gè)科舉成功的例子中,有兩個(gè)就是他們家族的。事實(shí)上,加上楊萬(wàn)里本人,到南宋末年,他們家族至少涌現(xiàn)了13位進(jìn)士,這不能不說(shuō)是巨大的成功。
比科舉上的成功更為重要的是,家族人物在“忠義”氣節(jié)表現(xiàn)上獲得的巨大聲譽(yù)。楊萬(wàn)里曾經(jīng)自詡為“天下第一”。他曾說(shuō):“吾族楊氏自國(guó)初至于今,以文學(xué)登甲乙者,凡十有一人。前輩之聞?wù)咴煌吞锕⒅蟹罟源耍酝吞锕⒅蟹罟笾林蚁骞运拦?jié)倡一世。于是楊氏之人物,不為天下第二。”②楊萬(wàn)里:《鳣堂先生楊公文集序》,《楊萬(wàn)里集箋校》卷78,第3187頁(yè)。“忠襄公”即楊邦,他在金兵攻打建康時(shí)被俘,堅(jiān)貞不屈,被金人剖心,其英雄壯舉至今仍流傳不已,南京還有古跡“楊邦剖心處”。正因?yàn)槠鋲蚜倚袨闉闂罴也┑镁薮竺暎瑮钊f(wàn)里才有底氣自贊家族“人物不為天下第二”,楊萬(wàn)里本人則以文章和忠義并舉而聞名天下。他不僅詩(shī)文杰出,而且晚年聞知韓侂胄北伐,絕食而死,死后謚“文節(jié)”,一時(shí)也是名動(dòng)天下,成為士大夫的榜樣。
廬陵楊氏作忠節(jié)祠者何?昔金人侵宋,沿江諸郡皆望風(fēng)奔潰,其先忠襄公邦以建康通判被執(zhí),大罵死;韓侂胄專國(guó)擅政柄,文節(jié)公萬(wàn)里以寶謨閣學(xué)士,家居聞之,三日不食死,故合而祀之也。中祀建康通判贈(zèng)通奉大夫存者何?嘗以直抗蔡京為楊氏忠義開(kāi)先也。別祀廣東經(jīng)略使長(zhǎng)孺、吏部郎官孫、子同知昆山州事學(xué)文者何?經(jīng)略仁聲義實(shí),風(fēng)槩天下,在廣東三歲祿入七萬(wàn)緡,盡以代民輸丁租,不持一錢(qián)去;吏部闿通敏惠,奉法循理為時(shí)良臣;昆山好德尚義,能以私錢(qián)復(fù)文節(jié)故居,割田百畝以建祠事。皆克紹先烈者也……故廬陵若歐陽(yáng)氏、楊氏、胡氏、文氏又有身致干淳之治,若周文忠氏皆國(guó)家之元?dú)庖玻鴼W陽(yáng)氏又廬陵之元?dú)夂酢@ド街釉?qǐng)記忠節(jié)祠,故并及之。③揭傒斯:《楊氏忠節(jié)祠記》,《文安集》卷10,《景印文淵閣全書(shū)》第1208冊(cè),第241頁(yè)。
該文被收入揭傒斯的文集,具有比較高的可信度。這次楊氏為家族賢明設(shè)立專祠,帶有很強(qiáng)烈紀(jì)念名人的意味,目的是為了弘揚(yáng)家族中的“忠”和“節(jié)”兩種可貴品質(zhì)。這次共祭祀了5位名人,忠襄公楊邦和忠節(jié)公楊萬(wàn)里自不必說(shuō),還有前文提到的建康通判楊存、廣東經(jīng)略使楊長(zhǎng)孺、吏部郎官楊孫、楊孫之子昆山同知楊文學(xué)。雖然后面三位名氣不及楊邦和楊萬(wàn)里,但都有可值得稱道的事跡,因而得以專祀。實(shí)際上,設(shè)專祠祭祀名人還有一個(gè)目的,突破禮法中臣民不得建家廟的規(guī)定。所以,雖然名義上建的是祠堂,但揭傒斯仍不斷解釋為什么要祭祀這些楊氏名人。
頗具戲劇性的是,倡導(dǎo)建立忠節(jié)祠的昆山知州楊學(xué)文,并不是湴塘本地人,而是楊氏在四川的后代。若干年后,楊士奇留下了一段文字,讓我們得以了解楊學(xué)文建忠節(jié)祠的經(jīng)過(guò)。根據(jù)他的說(shuō)法,揭奚斯說(shuō)楊氏由四川遷入根本就是錯(cuò)的。真實(shí)情況是,唐代有個(gè)祭酒叫楊膳,跟隨唐僖宗避難而進(jìn)入四川,成為四川楊氏的先祖,楊氏后來(lái)又遷居廬陵安成,所以安成楊氏和楊莊、湴塘的楊氏并不是同一支派,所謂“雖皆居廬陵,而所從來(lái)者實(shí)異”。但是,后來(lái)安成楊氏的族正楊仲“乏嗣”,“以其先與楊莊、湴塘同出漢太尉,乃至湴塘求叔先之子珪孫為嗣,更名孫,仕為贛州路總管、吏部侍郎,孫之子知昆山州事學(xué)文,不忘其父所生,以私錢(qián)復(fù)文節(jié)故居,又割田百畝,建忠節(jié)祠,故孫、學(xué)文皆得列祠祀中。”④楊士奇:《書(shū)揭學(xué)士〈楊氏忠節(jié)祠記〉后》,《東里集》卷9,《文淵閣四庫(kù)全書(shū)》第1238冊(cè),第100—101頁(yè)。從中可以看出雖然同為居住在廬陵的楊氏,但楊莊、湴塘的楊氏和從四川遷至廬陵“安成之族”的楊氏雖屬同姓但并不同宗,揭傒斯文將兩支楊姓混為一談是錯(cuò)誤的,因?yàn)樗吹闹皇撬拇钍系淖遄V(“蜀之譜”),后來(lái)安成之族的楊氏后裔肇慶知府楊仲謹(jǐn)無(wú)后,將湴塘楊叔先的兒子楊珪孫過(guò)繼為自己的兒子,改名“楊孫”,楊孫后擔(dān)任贛州路總管,其子昆山知州楊學(xué)文為了不忘記父親的出生地,以自己的私錢(qián),給予湴塘楊氏100畝田地,同時(shí)建立了忠節(jié)祠,因此楊學(xué)文和他父親楊孫的牌位也就放入了忠節(jié)總祠。
這個(gè)頗具戲劇性的故事,再一次清晰地展現(xiàn)了世系不完全相同的同姓,如何通過(guò)種種手段,建立其共同的聯(lián)系,從而達(dá)到聯(lián)宗的目的。楊學(xué)文建立忠節(jié)祠,固然有所謂“不忘其父所生”的樸實(shí)愿望,但是和大名鼎鼎的“忠節(jié)楊”攀附上關(guān)系,又未嘗不是重要目的之一。雖然建立這個(gè)祠堂包含了楊學(xué)文的私心,但祠堂卻成了楊氏卓絕名聲的物化象征。如果說(shuō)元代忠節(jié)祠還只是個(gè)名人紀(jì)念堂的話,到了明代,其名人紀(jì)念堂的色彩漸漸褪去,開(kāi)始演變?yōu)榧易屐籼昧恕?/p>
明初宣德年間,曾經(jīng)重修族譜的楊瑒主持了對(duì)忠節(jié)祠的重修。安福人明代名臣李時(shí)勉有記曰:“故元盛時(shí),楊氏之賢同知昆山事學(xué)文,始復(fù)文節(jié)故居為祠,規(guī)制廣于前而益加多。歲久弗治田,蕪宇傾……楊之賢季琛以舊臣膺京兆之舉,作令南海,次修祠之顛末,命宜修授予請(qǐng)記焉……增設(shè)始祖吉州公及屯田、清謹(jǐn)二龕,諸小宗顯宦敘昭穆從祀,廢像設(shè)用木主,刻世系、祀田、祭器、牲幣、酒儀、設(shè)科條于碑陰,祭用冬至、立春,子孫緣歲專直祠祀。祠宇壞漏,輒飭無(wú)怠,怠者罰如科條。所以尊祖而垂后,可謂遠(yuǎn)也已!可謂詳也已于乎!此可以為世勸,豈特楊氏而已哉!”①李 時(shí)勉:《楊氏重修祠堂記》,《古廉文集》卷3,《文淵閣四庫(kù)全書(shū)》第1242冊(cè),第698—699頁(yè)。通讀全文,可發(fā)現(xiàn)這次重修忠節(jié)祠變化有三:主祀增設(shè)了始祖和屯田、清謹(jǐn)二位神位,且按照昭穆順序從祀了其他名人;廢除了宋代祭祀常用的影像,改為木制的神位;將世系、祀田、祭器、牲幣、酒儀、設(shè)科條(管理規(guī)章)刻在石碑的背后,且規(guī)定了冬至、立春祭祀祖先。從這些變化中不難看出,忠節(jié)祠已經(jīng)轉(zhuǎn)變?yōu)榧易屐籼谩?/p>
忠節(jié)祠在明初的轉(zhuǎn)變,根本原因在于禮法的改變,即朱熹的《家禮》被朝廷采用,設(shè)立祠堂,祭祀四代祖先成為合法的事情。②常建華:《明代宗族研究》,第360—398頁(yè)。但是在嘉靖朝夏言上書(shū)之前,祭祀始祖其實(shí)并不合明代禮法(合乎程頤理論),忠節(jié)祠增設(shè)始祖顯然是有僭越禮制之嫌,然而,這恰恰說(shuō)明忠節(jié)祠性質(zhì)已經(jīng)發(fā)生了根本變化,以至于必須增設(shè)始祖才能達(dá)到收族的效果。至此,忠節(jié)楊氏已經(jīng)基本完成了宗族建設(shè),有了統(tǒng)一的世系、祠堂和祀產(chǎn)。
然而,忠節(jié)楊氏的宗族發(fā)展腳步并沒(méi)有停止。明嘉靖九年(1530年),擔(dān)任廣西副使的楊必進(jìn)聯(lián)合吉水、廬陵、泰和、永豐、安福、萬(wàn)安、信豐七邑楊氏后人在廬陵郡城建立了一個(gè)聯(lián)宗祠。時(shí)任江西右布政使的鐘芳為之記:“楊氏自南唐虞部侍郎公始居吉之湴塘,今廬陵、泰和、永豐、安福、萬(wàn)安、信豐楊姓皆其支派……自侍郎而下,顯者得八,謚者五,曰襄、曰節(jié)、曰靖、曰文、曰忠、曰貞,皆美謚。而祠獨(dú)曰忠節(jié),蓋舉盛以該之,沿舊額也。”③鐘 芳:《廬陵楊氏忠節(jié)祠碑》,《筠溪文集》卷9《記類》,《四庫(kù)全書(shū)存目叢書(shū)》集部第64冊(cè),齊魯書(shū)社1997年版,第575—576頁(yè)。這次建祠活動(dòng),頗有聯(lián)宗的性質(zhì),但又明顯不同于清代各地普遍出現(xiàn)的以同姓聯(lián)誼為目的的聯(lián)宗。祠堂選址在郡城,而不是老祠所在地湴塘,既為了方便各地后人祭拜,又使這個(gè)總祠有點(diǎn)聯(lián)宗祠的意味。總祠中共擺放了9塊牌位,除了始祖之外,都是在歷史上有影響的楊氏名人,并不完全按照世系來(lái)。此次聯(lián)宗參與的地域廣泛,除了吉水之外,還有吉安(廬陵)、泰和、永豐、安福、信豐等6縣,號(hào)稱“七邑”。前面已經(jīng)分析過(guò)泰和楊氏是通過(guò)楊士奇的努力將他們這一支與湴塘楊氏聯(lián)系在一起的,其他幾個(gè)縣如何將其世系與湴塘楊氏聯(lián)系在一起,不得而知,但他們屬于“忠節(jié)楊氏”后裔顯然是被湴塘楊氏認(rèn)可的。
在建總祠的同時(shí),楊必進(jìn)還主持興修了《忠節(jié)楊氏總譜》。這次修的是總譜,而不是湴塘的支譜,楊必進(jìn)在談及修譜進(jìn)程時(shí)說(shuō):“乃先集族在吉水者以為各邑望,不越季,而各邑亦有持系來(lái)者。”④楊 必進(jìn):《忠節(jié)楊氏總譜序》,《忠節(jié)楊氏人文紀(jì)略》卷 1《譜序》。乾隆年間楊氏后人回憶這次修譜:“至二十三世南樓公乃取本族之散徙于各邑各郡者而合修之,名《楊氏忠節(jié)總譜》。總譜遂為吾族本支一大觀,今所謂南樓公譜是也。”⑤楊嘉謨:《續(xù)忠節(jié)總譜記》,《忠節(jié)楊氏人文紀(jì)略》卷1《譜序》。文中的“南樓公”即楊必進(jìn)。修撰《忠節(jié)楊氏總譜》,在楊氏歷史上還是第一次,也是楊必進(jìn)建總祠后的又一次重大活動(dòng)。或許是為了更好地凝聚族人,楊必進(jìn)在這篇序文后面,還作了一篇名《原始》的文章,重點(diǎn)考證楊氏始祖楊輅。他說(shuō),關(guān)于始祖到底何時(shí)到廬陵,各派“紛紛議論,卒無(wú)定論”,有必要加以確認(rèn)。經(jīng)過(guò)嚴(yán)格考證,他認(rèn)為“乃知所謂在宋者,固非也;所謂在南唐者,亦未為定論;所謂在唐末吳楊初年者,固得之矣。”也就是說(shuō),他同意解縉的觀點(diǎn)。楊必進(jìn)再次考證楊氏始祖楊輅定居廬陵的時(shí)間,可謂用心良苦,表明他要求七邑楊氏族人必須有共同的宗族文化認(rèn)同。
有一個(gè)事實(shí)必須指出,號(hào)召七邑楊氏后人修建總祠和總譜,并不是件輕松的事情,所以這次聯(lián)宗活動(dòng)能持續(xù)多久,始終是個(gè)疑問(wèn)。到了清乾隆年間,楊氏族人想續(xù)修《忠節(jié)楊氏總譜》而不得:“由南樓公而來(lái),至于今二百三十有七年,代增孔多已倍五世之親,而譜猶未續(xù)。識(shí)者憂之!族之議修總譜也,蓋有年矣……歲在癸卯,湴塘忠節(jié)祠冬祭日,吉邑子姓咸集。祭畢,復(fù)議曰:譜事不可緩,總譜之修未可待也。不如取總譜而繙刻之,就其在吉邑者而續(xù)修之,其在各邑郡必自詳其支譜,則俟后之賢者而合續(xù)之。”⑥楊嘉謨:《續(xù)忠節(jié)總譜記》,《忠節(jié)楊氏人文紀(jì)略》卷1《譜序》。文中的“南樓公”即楊必進(jìn)。乾隆年間,又重建了忠節(jié)總祠,但是這次的忠節(jié)總祠基本按照市場(chǎng)化規(guī)則運(yùn)作。《楊氏人文紀(jì)略》中保留了一份乾隆三十九年(1874年)忠節(jié)楊氏總祠的告示,今列如下:
楊忠節(jié)總祠重建以丙戌年告竣,崇祀新主,今聞各后裔欲崇進(jìn)主位,特此通聞。約訂本年十二月初三日請(qǐng)主附廟,凡有仁孝為本念者務(wù)于十一月廿四日赍費(fèi)來(lái)祠,以便□修主牌,至于上主費(fèi),悉沿丙戌年舊例開(kāi)載于后:
一忠孝節(jié)義理學(xué)名宦及歷朝進(jìn)士名標(biāo)志乘者從未經(jīng)□上主,本屆補(bǔ)入,后裔只出修主之資。
一舉人每位主金壹兩陸錢(qián)正。
一恩撥副貢每位主金貳兩,出仕者照舉人例。
一生監(jiān)飲賓職員每位主金貳兩陸錢(qián)正。
一隱德每位主金叁兩正。
一修主上主之貲各后裔自辦不在主金之內(nèi)。
一所上主位務(wù)開(kāi)清官爵世系地名及其諱其號(hào)。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初一日
告示中的丙戌年,當(dāng)是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根據(jù)乾隆三十一年的舊例,不難看出,忠節(jié)楊氏總祠的牌位放置已經(jīng)形成了比較成熟的定制,即按照功名和封爵明碼標(biāo)價(jià)。
清代忠節(jié)楊氏聯(lián)宗運(yùn)作不是本文討論的重點(diǎn),之所以在此提及,一個(gè)根本的原因就是我們可以通過(guò)清代楊氏宗族的運(yùn)作規(guī)則看出明嘉靖年間聯(lián)宗活動(dòng)的影響,即明代開(kāi)始的聯(lián)宗活動(dòng),一直維系到清代。明嘉靖年間的聯(lián)宗活動(dòng)一個(gè)根本的影響就是,基本確定了“忠節(jié)楊氏”的輻射范圍和“忠節(jié)文化”的宗族文化認(rèn)同。自此,提及“忠節(jié)楊氏”必然和楊邦、楊萬(wàn)里的“忠節(jié)”形象緊密聯(lián)系,而其始祖則必然為五代時(shí)期定居于廬陵的“楊輅”。而且,并不是所有姓楊的都能夠稱之為“忠節(jié)楊”,“忠節(jié)楊”的后人必須是從吉水、吉安(廬陵)、泰和、永豐、安福、信豐等七縣中“奉楊輅為始祖,弘揚(yáng)忠節(jié)文化”的楊氏族人中播遷演化而來(lái)。
五、討論
宗族是中國(guó)歷史上非常重要的組織,甚至可以說(shuō),是中國(guó)人特有的既包含對(duì)血緣關(guān)系的認(rèn)同,又包含著中國(guó)傳統(tǒng)社會(huì)宗法觀念和倫理觀念的組織。中國(guó)歷史學(xué)家突破人類學(xué)家關(guān)于宗族組織是個(gè)功能主義組織和單純世系群體的認(rèn)識(shí),將其放置于歷史社會(huì)演變進(jìn)程中考察,是非常重要的進(jìn)展。毫無(wú)疑問(wèn),“宗法倫理的庶民化”和“國(guó)家認(rèn)同意識(shí)的推廣”是促使宗族組織發(fā)展非常重要的,也是相輔相成的兩個(gè)因素。但是,作為一個(gè)建構(gòu)的世系組織,其世系建構(gòu)的原則非常關(guān)鍵。從宋明時(shí)期吉安地區(qū)的宗族實(shí)踐活動(dòng)看來(lái),突破“小宗之法”的限制,建構(gòu)一個(gè)“始祖”是其關(guān)鍵節(jié)點(diǎn)。正是“始祖”的構(gòu)建,使宗法世系得以成功突破五代的限制,隨之而來(lái)的祠堂建設(shè)、族譜修撰也就順理成章。“始祖”其實(shí)并不是一個(gè)姓的開(kāi)始者,也不是一個(gè)地方的開(kāi)基者,甚至也有可能不是宗族歷史上最有聲望的人,而是某個(gè)時(shí)間節(jié)點(diǎn)出于某種世系建構(gòu)需要而產(chǎn)生的某一群人共同認(rèn)可的“祖先”。正如吉安楊氏在明代建構(gòu)出來(lái)的“廬陵始祖楊輅”一樣,他之所以出現(xiàn),是因?yàn)槊鞒鯒钍显凇白诜▊惱硎窕壁厔?shì)之下,宗族發(fā)展形勢(shì)需要建構(gòu)出這樣一個(gè)歷史人物。正是“始祖”的成功建構(gòu),楊氏才有可能有共同的世系,才有可能組織成為一個(gè)“宗族”。不過(guò),要指出的是,建構(gòu)一個(gè)實(shí)體化的宗族需要的不僅是世系統(tǒng)一,還需要一定的物質(zhì)基礎(chǔ)和祠堂、族譜等物化的精神象征。因此,始祖的構(gòu)建和世系的統(tǒng)一并不必然導(dǎo)致實(shí)體化宗族的出現(xiàn)。楊氏只有到了明宣德年間才通過(guò)建立祠堂、編修族譜等活動(dòng),建立起實(shí)體化的宗族。
在楊氏建立起實(shí)體化宗族后,楊氏家族還開(kāi)始了聯(lián)宗活動(dòng)。在聯(lián)宗活動(dòng)中,“始祖”的構(gòu)建是和宗族文化建設(shè)結(jié)合在一起的。吉安楊氏在建構(gòu)始祖“楊輅”的同時(shí),也整合了楊氏歷史上著名的兩個(gè)人物“文節(jié)公楊萬(wàn)里”和“忠襄公楊邦乂”,形成所謂的“忠節(jié)楊氏”。也就是說(shuō),在建構(gòu)出共同始祖“楊輅”的同時(shí),也形成了楊氏獨(dú)特的“忠節(jié)”文化。我們相信,從宋朝到明代,南方中國(guó)許多地方的同姓大族,也經(jīng)歷了吉安楊氏相似的歷程,通過(guò)“始祖”的構(gòu)建,將并無(wú)血緣關(guān)系的同姓群體,整合成了具有相同世系的同宗群體。與此同時(shí),形成了宗族獨(dú)特的文化。只不過(guò),各姓之間可資利用的物質(zhì)和文化資源不同,從而規(guī)模和文化成色不一樣罷了。①例如:著名的“義門(mén)陳”即表明了陳氏獨(dú)特的宗族文化;南方的黃姓大多認(rèn)可自己是“峭山公”的后代,則說(shuō)明了“始祖”對(duì)宗族建構(gòu)的重要性。楊揚(yáng)考察南昌萬(wàn)氏家族的歷史,發(fā)現(xiàn)其家族原來(lái)也是四個(gè)不同的支系,通過(guò)構(gòu)建一個(gè)祖先更遙遠(yuǎn)的世系關(guān)系,四個(gè)支系成功聯(lián)合構(gòu)成了一個(gè)宗族。②楊 揚(yáng):《從宗族到聯(lián)宗:明清南昌萬(wàn)氏宗族的個(gè)案研究》,南昌大學(xué)碩士學(xué)位論文,2014年。
錢(qián)杭對(duì)中國(guó)歷史上的聯(lián)宗組織進(jìn)行過(guò)深入考察,他從世系學(xué)的角度認(rèn)為,聯(lián)宗過(guò)程中存在著對(duì)“始祖”靈活認(rèn)定和對(duì)大、小宗法的超越,并明確表示聯(lián)宗不是宗族實(shí)體,而是一個(gè)宗族地域聯(lián)盟。③錢(qián)杭:《血緣與地緣之間:中國(guó)歷史上的聯(lián)宗與聯(lián)宗組織》,上海社會(huì)科學(xué)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340—349頁(yè)。從吉安楊氏宗族發(fā)展的歷程看來(lái),同姓到同宗的發(fā)展,實(shí)際上是一個(gè)動(dòng)態(tài)過(guò)程,中間并無(wú)明顯的界限。我們似乎可以說(shuō),宣德年間楊氏有了統(tǒng)一的世系、祠堂和祀產(chǎn),因而是個(gè)實(shí)體化的宗族,然而這個(gè)實(shí)體化的宗族,又是湴塘、楊莊聯(lián)宗的結(jié)果,甚至還摻合了源自四川的楊氏。宣德以后的楊氏顯然還在不停地謀求與其他楊姓的聯(lián)宗,從明嘉靖年間到清乾隆時(shí)期,楊必進(jìn)建立的聯(lián)宗組織也一直在運(yùn)作。因此,我們可以說(shuō),從同姓不同宗的群體,到同宗的實(shí)體化宗族,再到虛擬化的聯(lián)宗組織,是一個(gè)動(dòng)態(tài)的、連續(xù)的發(fā)展過(guò)程,不宜過(guò)于強(qiáng)調(diào)聯(lián)宗的非宗族性質(zhì)。聯(lián)宗發(fā)展到一定程度,“宗”的外延不斷擴(kuò)大,其必然又會(huì)與“姓”趨于一致。
同姓群體可以“從同姓到同宗”,當(dāng)然也可以“從同宗到同姓”。所以明代以后在南方地區(qū)廣泛出現(xiàn)了宗族組織,到了清代即出現(xiàn)了聯(lián)宗高潮,以至于乾隆皇帝一度要“毀祠追譜”,限制聯(lián)宗活動(dòng)。①然而,這種聯(lián)宗活動(dòng)一直持續(xù)至今,以至于天下同姓幾乎都可共享一套共同的“世系”和“祖先”了,即形成所謂“天下某姓系一家”的說(shuō)法,形成各姓標(biāo)準(zhǔn)而統(tǒng)一的“百家姓源流”。
吉安地區(qū)宋明時(shí)期的宗族實(shí)踐歷史表明,考察宗族問(wèn)題,宗法倫理庶民化和國(guó)家認(rèn)同意識(shí)的推廣固然重要,但“始祖的建構(gòu)”所帶來(lái)的世系突破也是關(guān)鍵環(huán)節(jié)。只有始祖成功構(gòu)建出來(lái),宗族的世系有了一個(gè)起點(diǎn),族譜的統(tǒng)一和祠堂的修建才能順理成章,同姓才能轉(zhuǎn)變成同宗。隨著后世宗法禮制的進(jìn)一步松弛,始祖認(rèn)定所帶來(lái)的世系起點(diǎn),又被進(jìn)一步突破,從而演變成為同姓即同宗的局面,所謂“天下某姓是一家”的觀念深入人心,從而出現(xiàn)了“天下某姓通譜”“百家姓源流”等文化現(xiàn)象,此時(shí)血緣關(guān)系已經(jīng)變得不重要,宗族文化成為同姓認(rèn)同的核心。然而,雖然天下同姓都是一家,擁有共同的姓氏文化了,但是同姓之間還是有微妙的差別,正如前面所論述的,并不是所有中國(guó)楊姓都可稱之為“忠節(jié)楊”,只不過(guò)這種微妙的差別往往湮沒(méi)在強(qiáng)大的姓氏文化之中而不易被人發(fā)覺(ju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