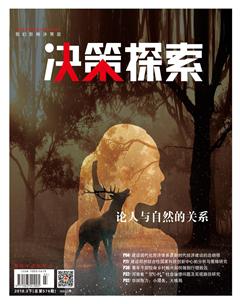河南省“空心村”社會治理問題及實現路徑研究
高鵬 馮秋季
農村勞動力轉移對分流農村人口、加速城鎮化建設、促進城鄉一體化進程有著積極的推動作用。但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速度和規模要適度,轉移超出或不足,都會對農業生產和農村社會生活造成消極影響。改革開放后,空心化問題已經從對村落空間的影響,逐步擴展到對農村人口結構、經濟發展、社會治理等諸多方面的影響。河南省作為農業大省和人口轉移大省,農村“空心化”現象比較突出,選取河南省作為樣本研究“空心村”社會治理問題具有典型意義。
一、河南省農村勞動力轉移和農村“空心化”情況
河南省是人口大省,勞動力資源豐富。截至2016年年末,全省總人口10788.14萬人,其中常住人口達到9532.42萬人。這為河南帶來一些“包袱”。一是農村人口比重仍然較大,城市反哺農村的任務較重。截至2016年年末,全省農村人口4909.20萬人,占常住人口的51.5%,總量居全國第一位。二是城鎮化水平低,48.5%的城鎮化率遠低于全國57.35%的平均水平,僅高于云南、甘肅、貴州、西藏4省區。三是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數量大,農村“空心化”程度高。2016年年末,全省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2876萬人,占全省農村常住人口的58.6%,其中向省外輸出勞動力近1200萬人。
人口的流出對傳統家庭和社會結構的穩定性造成沖擊。調查顯示,在外出務工的農民工群體中,有超過3/4的人只能半年或一年回家一次,影響外出務工人員回家探望的主要因素為“怕耽誤工作、影響收入”和“路程較遠、路費太貴”。75%的被訪者表示只能讓留守兒童吃飽穿暖,在教育、溝通、引導和保障安全等方面“心有余而力不足”。55.4%的被訪者認為外出務工是導致農村離婚率上升的主要原因。將近一半的人認為,青年人外出務工導致老人過度勞累,無法安度晚年。傳統鄉村社會中鄰里互助關系也在逐漸被瓦解,社會日趨個體化;親戚之間的社會互動頻率降低,親屬關系逐漸疏離。
二、河南省“空心村”社會治理存在的主要問題及其成因
(一)“空心村”社會治理主體與治理對象同時缺位
青壯年是農村經濟社會各項建設的主力軍和農村基層政治建設的合適人選,但研究表明,近年來這些人群流出的速度在不斷增加。基于對包括收入差距在內的種種城鄉差距的現實考慮,青壯年大多選擇離開農村去城市發展,造成農村精英階層斷代的局面。留守群體由于受年齡、知識、體力、精力等種種限制,缺少參與鄉村經濟社會建設和社會治理的能力和精力,使得一些鄉村公共事務出現無人問津的情況,有的鄉村已無法組織起正常的公共生活,進一步降低了商業服務投向農村的規模效益和愿望。
(二)基層黨建和民主政治建設工作出現“空心化”
常年在外的農民工與農村的利益關聯不斷弱化,雖然他們不愿意放棄農村戶口和土地,但一般不愿意自付成本回鄉參加“選舉”。由于村“兩委”選舉時間跨度較長,離家較遠的農民工回鄉參選的意愿非常低,58.1%的受訪者表示不會因選舉而中止打工、經商。留守群體成為參與“空心村”基層黨建和民主政治建設的真實主體。村“兩委”換屆面臨著“誰選舉”和“選舉誰”雙重主體缺失的尷尬境地。有些村的村干部換屆甚至無人競爭,不得不由年齡較大、無力外出打工的人擔任。
(三)“一元化”鄉村組織治理能力不足
改革開放后,“鄉政”不斷萎縮,部分農村地區出現了“權威真空”。薄弱的經濟基礎和落后的管理模式難以支撐“空心村”治理結構由管理型向服務型轉變。一些村基礎公共設施損壞后無力維修,公共服務供需矛盾突出。在資源整合、發展經濟、提供公共服務等方面能力不足。村黨支部和村委會缺乏自主意識和自主能力,“等”和“靠”的思想較為濃重。絕大多數“空心村”的“兩委”既抓黨建、政務,又經營集體經濟,同時還負責提供公共服務,因角色和利益沖突難以形成工作合力,并不時造成掣肘。農村新型股份合作經濟形態發展滯后、數量少,其他社會組織發育更加緩慢,力量弱小,難以有效承接政府職能轉移。村“兩委”權力比較集中,容易導致村官腐敗現象的出現,以及引發干群沖突、引發上訪告狀等群體性事件。
(四)農民的家庭保障能力較低,社會保障水平不高
在“空心村”中,老年人參加農業勞動的現象十分普遍,60歲至70歲的老人仍有78%參加農業勞動,70歲以上的老人也有41%以上參加農業勞動。大量青壯年勞動力紛紛外出,留下了大量的空巢老人,傳統家庭原來能提供給他們的家庭保障和精神慰藉越來越少。目前,農村社會保障主要由新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及農村五保制度等構成。由于農村經濟發展水平低,農民對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缺乏信心,大多數地區農民投保時都選擇了最低的檔次(2元)。經專家測算發現,按照這一標準,農民60歲后每月最低只能領取73元養老金,即便按照最高標準繳費,最多也只能獲得每月129元的養老金,顯然無法滿足老年人基本的生活需要。
(五)治安狀況惡化,影響社會穩定,加劇農村人口流出
治安狀況惡化是農村“空心化”的“副產品”。由于留守群體受年齡和身體狀況的局限,法律意識、防范意識較薄弱,防范能力不足,犯罪分子在“空心村”的違法犯罪活動更加“肆無忌憚”。“空心村”留守群體的生命安全得不到較好的保障。另外,由于部分“空心村”村委對違法人員不敢管,怕得罪人,對村民的生產、糾紛和文化生活不想管,放任自流,村民參與賭博、封建迷信活動、治安刑事案件和群體性事件均時有發生。
三、河南省“空心村”社會治理的實現路徑
(一)構建多元化治理體系,解決鄉村社會多元化利益需求
首先,要合理劃分村“兩委”的權限和職責,在鄉村推動“政、經和服務分離”改革,恢復其自治組織的本來面目。村黨支部主抓基層黨建工作,村民委員會承擔鄉村社會治理和服務職能,集體經濟組織負責管理集體資產,其他社會組織協助村“兩委”開展各項社會活動。其次,要依靠行政力量和政策扶持給“空心村”一個“原動力”,使各種經濟組織和社會組織快速壯大起來。培育龍頭企業、專業合作社、行業協會等多元主體,拓展服務范圍,重點加強農產品加工、銷售、儲藏、包裝等服務。最后,運用資金扶持政策,引導社會力量參與農村社區建設,在農村公益、文化活動、科技服務等領域推行政府購買服務制度,拓寬農村社會組織發展空間。鼓勵建立村民理事會等民間社會組織,協同參與農村社會建設和社會治理工作。
(二)加大城市反哺農村、財政轉移支付力度,提高村干部待遇,強化“空心村”經濟發展“內核”
“空心村”集體經濟薄弱,相當一部分村子只有負債,沒有集體收入。所以,要突出“城市反哺農村、財政為群眾服務”的理念,構建財權與事權相匹配的社會事務公共資源配置機制,由省、市兩級建立利益協調和補償機制,對“空心村”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力度,尤其是統一規劃、統一標準,推動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建設,加大交通等基礎設施建設力度,提升“空心村”公共服務能力。
由于人口流失嚴重,精心準備的好政策、好點子和技術培訓班少有人問津,難以發揮作用。調查顯示,如果回鄉就業家庭經營性年收入能達到3萬元上下,有相當一部分50歲以上的農民工會返回鄉村。如果能在農業規模經營、民宿經濟或旅游服務業等方面提供更多創業空間,那么40歲以下的中青年農民工也會樂意回鄉創業。“火車跑的快,全靠車頭帶”,發展農村經濟,就要發揮好“帶頭人”的作用,一要做好在外人員情況調查和資產情況摸排,選出一批有資金實力的“帶頭人”。二要做好本村經濟資源、文化資源、歷史資源、旅游資源的排查和挖掘工作,與“帶頭人”實現項目對接,運用政策杠桿、財政杠桿、金融杠桿吸引“能人”回鄉創業,帶動外出務工群體回鄉就業。
在許多“空心村”中,村干部領著最基本的補貼,做著最低限度的管理工作,甚至要靠兼職補貼家用,這顯然無法對青壯年人形成吸引力。為解決這一問題,建議創新村干管理和保障機制,把村級工資、經費納入縣級年度財政預算,把村干部納入事業人員隊伍管理,提高村干部的待遇,建立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實行基本養老保險,統籌安排好農村基層干部生活保障、發展空間和退休保障。例如廣東省翁源縣每年為每個村從縣財政劃撥工作經費,村“兩委”干部月平均工資達2000余元,有效提升了村“兩委”班子的戰斗力和凝聚力。在解決村干待遇的基礎上,嚴格推行考核制度,對年齡大、身體差、違規違紀、考核末位的村干部問責淘汰。
(三)強化源頭治理、動態管理,扭轉“空心村”治安頹勢
要解決“空心村”分散冷清、缺乏視頻監控、缺少治安巡邏力量、留守人員自我保護意識不強、抵抗能力弱的現實情況,就要在“空心村”中堅持人防、物防、技防相結合,推進網格化服務管理,推動“天網工程”向農村地區的覆蓋,在“空心村”重要出入地段安裝監控探頭。對于“空心村”地區的群眾,要加大治安防范宣傳力度,增強村民維護自身安全的意識,將“空心村”地區村民自我防范能力和意識提高到一個新水平。抓好村民群防群治,重點照顧“空心村”地區。充分整合各種社會資源,將防范巡邏、矛盾調解、幫扶工作等各種群防群治力量結合起來,對“空心村”及其周邊地區加大治安防范力度,盡力提高群眾的環境安全感。實踐證明,但凡防范巡邏工作能正常堅持的村落,各類可防性案件的發生率都會顯著下降。深化駐村警務工作,對“空心村”要定期和不定期進行治安巡查、暗訪和走訪,多關心孤寡老人,多關心留守人員,不給心懷叵測的人造成有機可乘的僥幸心理。駐村民警要有意識地增加對“空心村”地區治安的關注度,關心群眾的生產生活安全,及時檢查各類治安隱患,想方設法堵塞各種治安漏洞。
【本文系2016年度河南省政府決策研究招標課題“空心化趨勢下農村社會治理問題研究”(2016B296)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新鄉醫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