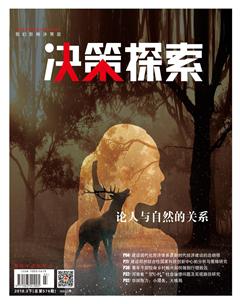從隋唐洛陽城城市功能的 轉變看唐朝前期洛陽的開放性
楊麗
洛陽長期作為都城,有著深刻的歷史淵源和社會背景。在地理位置上,洛陽處于東西南北交通的中心,四通發達,運輸供給方便;在政治、軍事上,洛陽踞天下之中,扼形勢之要;在文化上,洛陽是東西南北交融之區,借此可以彌合關隴、山東、江南長期分裂后的文化差異。洛陽長期作為隋唐的都城(唐高宗建洛陽為東都;武則天正式以洛陽為首都,取代長安的地位;中宗復位后,仍改洛陽為東都,成為僅次于長安的政治中心),在我國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唐朝,大放異彩,將著名史學家班固在《東都賦》中“洛邑處乎土中,平易闊達,萬方輻輳”描述的“輻輳”作用發揮得淋漓盡致。
一、隋唐以軍事防御功能為目的
隋唐洛陽城布局嚴整,氣勢宏大,達到中國古代建筑文化的高峰。宮城皇城位于全城西北隅,占據高地便于防御。宮城為皇室居住之所,皇城為執政所在地,宮城南邊為皇城,北邊建重城,東邊隔著東城,西面連著西苑,戒備堅固而嚴密。這樣的布局雖然不是隋唐兩代首創,但在隋唐兩代有所增益。市場及居民里坊建在宮城、皇城的外圍,以高大的城墻與這兩城相分割,里坊的面積也比前代大為縮小,并且里坊和市場之間也都建有高大的圍墻,便于其對居民區的控制,具有濃厚的軍事管制的性質。這種嚴格的里、坊制度,構成了大道筆直、坊墻聳立的景觀。從中可以看出,隋唐洛陽城設計布局是以軍事防御功能為目的的。
二、對外開放的社會需求要求城市功能的改變
洛陽是當時僅次于長安的大都會和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其文明程度遠遠超出當時的世界各國。因此,它就像磁石一樣,吸引著亞、歐、非各國的人們。長期的物質和文化交流不僅使統治階級受益,而且廣大人民群眾也得到了實惠,因此對外開放成為這一時期的社會需求。隋唐兩代實行全方位的對外開放政策,對諸國前來進行朝貢貿易的一貫采取歡迎態度,并給與相當優厚的待遇。
這種對外開放的社會需求必然要求在進行城市規劃設計時更加關注城市的商業、手工業功能。當政治穩定、經濟發展后,必然導致原有設計規劃意圖的崩潰。雖然唐代前期的洛陽城面積“周回五十二里”,比長安城“周回六十七里”要小,但設立了3個市場,即南市、西市、北市,比長安的東市、西市多出1個。南市即隋朝時的豐都市,當時占據了兩個坊的面積,唐代時期沿用并縮小了半坊,而且四面各開3個門,以方便人們的生活。據元《河南志》卷一記載,“周十一里,通門十二,其內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甍宇齊平,遙望如一。榆柳交蔭,通渠相注,市四壁有四百余店,重樓延閣,互相臨映,招致商旅,珍奇山積。”從中可以看出其繁華景象。西市即隋朝的大同市,處于外郭城的最西南,顯得相當偏僻,但也是一派繁華景象:“其中有邸,一百四十一區,資貨六十六行”。通遠市即隋朝時的北市,據杜寶《大業雜記》載,這一代在唐初“天下舟船所集,常萬余艘,填滿河路,商販貿易,車馬填塞,若西京之崇仁坊”。
三、新型城市功能突破了軍事管理的束縛
隨著洛陽城的穩定繁榮,南、西、北三市已滿足不了工商業迅速發展的需要,市場以外交易場所不斷擴大、增多,各商店紛紛在正鋪前加造偏鋪,以增加營業面積。容納不下的店鋪便開始向三市附近的坊、里及街道兩旁蔓延。北市附近更是繁盛,旅館、酒店大都集中在這里。洛河之北,東城之東的清化坊、時邕坊、殖業坊等皆有客舍或旅館,由此影響了市容觀瞻,以至于政府不得不于景龍元年(707年)為了整頓兩京諸市場的商業秩序而發布敕文:“禁止兩京市諸行自有正鋪者,不得于鋪前更造偏鋪。”交易時間也不斷延長,以至半夜仍然車馬人喧,異常熱鬧。市場管理逐漸合理,設立專人負責評定各類商品的物價,校訂交易時商人使用的度量衡器。居民里坊間高大的坊墻也漸趨虛設,打破了設計規劃者人為的規定,也突破了軍事管理的束縛限制。
里坊規劃和貿易市場的不斷突破,標志著洛陽城市功能的轉變。以政治、軍事功能為主的封閉式城市格局發生了動搖。工商業逐漸成為城市的重要組成部分,為宋代長巷式布局的城市興起奠定了基礎。正是因為這種民族文化的兼容并包使得洛陽在唐代成為世人矚目的國際大都會,同時也在中外交流史上寫下了濃重的一筆。洛陽古代的開放性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中國傳統文化的開放與包容,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經濟的發展與社會的進步。當今在“一帶一路”倡議的引領下,洛陽作為絲綢之路的東方起點,要想對中國與亞歐國家的經濟、文化交流作出應有的貢獻,對古代洛陽開放性的傳承顯得更加重要和急迫。
(作者單位:洛陽師范學院附屬中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