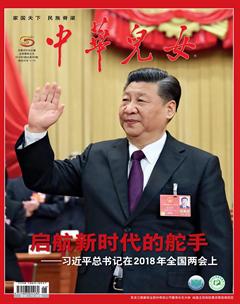足夠的“時間成本”催生等量價值的作品
作家與刊物的關系,尤如農夫與農田——作家需要刊物以耕種自己的作物,刊物也需要作家前來耕耘以保證自家的農田不致荒蕪。由此而產生的收成,既取決于天候是否風調雨順,更取決于農夫與農田是否相濡以沫。身為作家而擁有若干個相濡以沫的刊物,實在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幸事。回想起來,《中華兒女》在我多年的文字耕耘中,稱得上是意義獨具。
記憶最深的,是在1995年。初秋時分,我與眾多文友受《中華兒女》之邀從北京出發,抵達重慶后,登上了一艘美麗的江船。江船順流而下,直奔三峽而去。我們就著旖旎的兩岸風光,聆聽編輯們的策劃方案,談說各自的選題內容。不等穿越整個三峽,那艘美麗的江船便載滿了各式選題,其中不乏一些重大選題,或關乎歷史,或關乎現實。記得此次同行的有毛澤東主席之女李訥、周恩來總理專職攝影師杜修賢等。出身領袖家庭的李訥衣著簡樸,言談舉止端莊可親,看上去完全就是尋常人家的普通女子。看到街邊書攤在兜售有關她父母情感的地下出版物,標題起得奪人眼球,李訥面色平靜地走過,只有我們可以想見到她內心深處的波瀾。后來,面色平靜的李訥在一座石橋上激情飛揚。那是與劉少奇主席的兒子劉源的不期而遇!當時他們兩人從石橋兩頭分別走過來,隔著大老遠就都向對方伸出了手臂。當他們兩人的雙手緊緊相握時,隨團攝影師用鏡頭記錄下了那個意味深長的歷史瞬間。從頭至尾,我默默注視著他們,心頭涌動著一種親眼見證歷史的感慨,那是用多少詞匯也無法道盡的紛雜繁復……
劉宏偉檔案:
劉宏偉,原八一電影制片廠文學部高級編審。中國作協會員、中國散文學會會員、中國電影家協會會員、中國電視藝術家會員、中國電影文學會會員、北京電影藝術家協會會員。出版過長篇小說、紀實文學10多部,創作過電影劇本及電視專題片、電視連續劇多部,曾獲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中國人民解放軍圖書獎及“華表獎”、“金雞獎”等。
回到北京后不久,我如約交出了關于中國耕地保護的報告文學《誰來養活中國人》。誰知深得《中華兒女》編輯部厚愛,待到刊出時,給我換了個更“大號”的標題和特大號的字體——《中國的天塌了嗎》,弄得我都有些飄飄然起來……那時的《中華兒女》,常常會舉辦編輯與作者互動式的座談會。記得在一次座談會上,著名學者張友漁先生特意評說了我那篇報告文學在選題上的重大與作者寫作時所付出的功夫;而著名作家畢淑敏則評說道,這是一種“高時間成本”的寫作。隨后,大家就“寫作的時間成本”做了充分的話題討論,最終的結論是,為《中華兒女》寫稿,值得付出足夠的“時間成本”。
事實證明,足夠的“時間成本”當能催生等量價值的作品,付出與得到的交換鐵律,同樣適用于寫作領域。后來,我出版了長篇小說《地產魅影》,其理念與素材就受益于那篇報告文學的“時間成本”。可以說,正是當年的那篇報告文學《中國的天塌了嗎》,直接催生了后來的長篇小說《地產魅影》。因此,在人民文學出版社與國土資源部共同為《地產魅影》主辦的新聞發布會上,在《地產魅影》榮獲第八屆茅盾文學獎參評證書時,我的感恩名單中少不了《中華兒女》!
如今,30年的歲月過去了,《中華兒女》到了風華正茂的年齡段。在眾多的刊物中獨具魅力,正是因了她鮮明的時代感與強烈的使命感,再加上考究的文字與版式,讓我禁不住對她關注再關注……
不消說,《中華兒女》早已是我的良師益友了,她邀我一起親近這個前所未有的大時代,激勵我成為巴爾扎克所崇尚的那種“時代書記員”式的作家。
最好的感恩,就是永不辜負!
責任編輯 余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