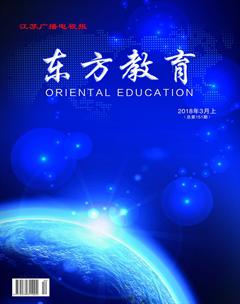中國農村題材電視劇的審美風格研究
摘要:農村劇作為我國電視劇類型的一個重要分支,回顧它的發展史,既可以視為我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農村面貌和農民生活發展變化的一部“編年史”,亦是當代農民30多年來的心靈史詩。總體來說以農村背景為依托,集中地反映了時代變遷中的農村在物質、精神兩個層面農民的發展與變化。筆者主要通過審美風格的研究展現農村純凈優美的風景之外,通過樸實的鏡頭傳達出農村獨特的鄉土氣息及傳統文化面貌,為我們構筑了一道審美的人文景觀。
關鍵詞:電視劇;農村題材;審美風格
一、農村劇概念界定
農村題材電視劇,由于它在不同的時代變遷中演變出了不同的審美特征,所以學界對于它的定義也是處在不斷地完善中,其實任何一種概念的界定都會讓人在“顧此失彼”中左右為難。不言而喻,農村題材電視劇也應是在多思維、多視角、比較研究中妥協與折中的結果,在均衡中兼顧中庸之美。農村題材電視劇概念總體上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狹義上將所有“三農”和“涉農”題材電視劇統稱為農村題材電視劇,雖帶有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仍具有十分廣泛的影響。
鑒于在進入新世紀以后我國農村經濟發展狀況和農民的思想的嬗變在質上發生了改變,所以廣義的農村題材電視劇也極具代表性,以“新農村建設”為拐點,內含城市的交融和比照的意味,關照農村主體中人存在的角色與位置,相應弱化了農村民情風俗、地域色彩,以藝術創作表現農村人守土、離土、返鄉的艱辛與酸楚,秉承記錄農村社會與文化范式集視聽語言予以影像觀照的一種電視劇類型,即為農村劇。
二、農村劇的審美風格
通過對農村劇概念的闡述,我們也能洞察出農村劇創作必然隱含著審美風格,通過借助對農村的記錄與價值取向,反映現代文明與農村遭遇后的情況進行對照,實現其獨特的現實主義審美價值。人作為農村劇中的主體性在人物塑造中以他們的生存狀態為主,在反思中批判、在批判中走向引領與超越并呈現出自己的特色和模式。
2.1.通過題材彰顯現實主義風格
現實主義題材的電視劇基于對客觀現實的冷靜觀察與理智分析,直接揭示現實矛盾、生存狀態。僅從這類電視劇的發展概況就能洞察出這一點,在此過程中,追尋農村社會的普遍價值為旨歸,借用電視這門藝術,以生動的影響關照凸顯了農村劇的真實。
首先,表現在進入新世紀后中國的文化格局變化使得的農村劇在藝術創作與主流意識形態的關系上有了新的轉型,之前的農村劇主要成為黨和政府的喉舌,進行一定程度的教育宣傳,成為政治權力的附庸和有效管理手段,觀眾在這樣一種光影體驗中顯然是被動的。新世紀農村劇已不是黨和政府的“傳聲筒”,題材趨于多元化、更加的豐富,更重要是規避了這一圖解式的宣傳教育功能,從題材上的表達來看,也更具人文情懷,從鄉土中國的國情出發,表現改革的沐浴春風后國家帶給農民的一系列實質性的惠利,在創作中謹遵“三貼近”原則。實現現實主義的故事與故事的現實化完美融合。譬如電視劇《希望的田野》中,鄉長無視國家紀律與惡霸勾結實現自己的私利及政治意圖,將拖拉機圖偷走制造不在場的證據嫁禍給別人,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排斥異己將新任村長逼走,這些也是映射了現如今農村的基層政治的腐敗問題。
其次,研究農村劇,必然離不開它的歷史背景,把它放在宏大的國家變革中去關照,注重它的本體性研究,這也為后來學者提供一個詳實的影像研究資料。農村劇在起步階段便以平實的鏡頭聚焦于改革開放的現實生活、反映現代性與農村遭遇后激起思想嬗變與情感波瀾,探索農村走向現代化的必由之路。接著又緊貼“三農問題”進行一場農民與農村變革圖景的演繹。深刻透視了農民由物質跨越到精神上的變化,這些劇兼顧思想性、現實性與藝術性,譜寫了一曲新時期鄉土中國農民與農村波瀾壯闊的“山鄉巨變”之歌。
三、敘事手法的真實性
電視作為一個展現農村華麗巨變的絕佳載體,通過視聽語言對鄉村真實環境的描繪,發揮了綜合藝術的再現性,農村劇基于客觀現實,注重對藝術真實的表達。它以影像畫面作為藝術語言,展現了農村純凈優美的風景,傳達出農村獨特的鄉土氣息。既遵循了藝術創作規律,又是對鄉村、農民的一次全面關照與透視。
3.1.傳遞鄉土畫面的真實美感
農村劇試圖用一種樸實無華鏡像語言一覽無余的描摹著農村的真實地貌,觸碰著人們對于原生態的農村自然景象的追求與渴望,誘發觀眾在觀影過程中迸發的一種返璞歸真的情懷。這些都給予觀眾極大的審美體驗,從而提升藝術作品的人文內涵。此處僅東北和西北農村劇為例,劇中展示了其地標性的風物。《籬笆·女人和狗》展現了東北地處邊陲、白山黑土及東北特有的籬笆小院都明顯地交代了故事發生的地理環境;《神禾塬》中展示了西北的黃土高坡及當地群眾居住的建筑風格——窯洞。這些極具平實的畫面最大程度的還原了地域性風貌,極大滿足了觀眾的審美體驗。
3.2.劇中突出人的主體性
農村劇的精髓就在于對劇中人物形象的塑造,通過對人物語言的精雕細琢及本色出演風格,使之達到精氣神的完美統一,把人的主體性作為第一要務,反映出劇中人的性格、心理和氣質,惟其如此,才能滿足群眾低層次文化需求的大眾化,才能窺視到那種含蓄深沉的情感表述,這也是農村劇給以觀眾的終極關懷和價值呵護。
3.3.人物語言的通俗化
語言的通俗化能顯示出一種地域文化,譬如“東北三部曲”之稱的《籬笆女人和狗》劇中巧姑的深沉、棗花的善良、香草的仗義等性格都是通過她們通俗化語言來表現的;《平凡的世界》中盡顯陜西方言,特別是在每次孫少平和媳婦秀蓮吵架中我們會多次聽見少平對媳婦說:“你再能,小心我錘死你”這樣極具特色的陜西方言使用很容易喚起我們的情感體驗,在觀影過程中不禁大笑,同時也能體會到少平對于媳婦的無奈之舉。這種方言的使用不僅能表達出深刻的道理,也符合農村劇的語言特性。
3.4.啟用本土演員
從某種程度上講,農村劇是農村生活變遷的一部心靈史詩,是現實農村改革的一個縮影,所以,啟用本土演員能夠更好地調動觀眾的情感,符合農村劇的真實,這就是為何一般情況下導演很少啟用大牌明星,而是那些不為人知的“新面孔”,進一步講,這些人都會有一種鄉土氣息,比如《鄉村愛情》系列、《馬大帥系列》、《黨員二楞媽》這些劇中人物用通俗化的語言進行本色表演,其中有些本身就是農村出身,所以他們的表演更具本土化,更符合這類電視劇的出演,同時會增加農村劇的真實性和親切感。如果啟用大牌明星或觀眾極為熟悉的演員,人們就會先入為主地認定他們是在“演”電視劇,但啟用“新面孔”往往會剔除觀眾固有的“為演而演”的慣性思維,從而引發觀眾獲得情感共鳴。
特別是在地域性比較強的作品中,我們體驗到的不僅是演員的情感充沛的表演,即使在屏幕之外,也會有一種與屏幕演員對話的既視感,產生這樣一種“相鄰體驗”亦成為農村劇頗具生命力的藝術基因。
3.5.人物塑造的多元化
只有通過對于“人”的讀解,才有可能深入到對“人性”的詮釋,特別是農村劇發展,集中反映了從建國之初到改革之年再到進入新世紀后,農村的發展昭示著中國的巨變,在這其中,農民的身份和地位也潛移默化的發生根本性變化!源于根深蒂固的宗法傳統觀念尚存締造了一批愚昧思想落后的“男權主義”。如《籬笆女人和狗》中的茂源老漢,他心地善良、做事公正,資歷深、有威望卻觀念陳腐。兒媳婦不能懷孕便勸丈夫銅鎖去醫院檢查,一向待棗花視如己出的茂源老漢卻轉而責怪埋怨起棗花。合理性在他們的眼中消失殆盡,“一家之主”成為他們的代名詞,留下的只有一種封建男權的家長形象。
其次,進入新世紀后的農村劇在人物塑造上規避了模式化的套路:即克服對于農村干部都是“高大全”的塑造,不是一味的為他們歌功頌德、樹碑立傳,而是加入了常人所有具有的七情六欲,人身上的“真性情”搬到屏幕中,雖有堅毅、執著、不服輸的品質。但他們身上與生俱來的性格缺陷、私己主義,對感情的情不自禁也一同表露出來,既真實又能產生共鳴。譬如《鄉村愛情》中的謝廣坤,一心對官場權利的向往,便把希望寄托在剛剛大學畢業的兒子身上,認為開墾荒地從事農業種植沒有前途,為了如他所愿,從中作梗兒子婚姻,幾經周折攀附官場關系,這種小農意識立刻凸現出來,它是農民對權利的一種趨奉,是眾多趨炎附勢、對權貴渴求的典型代表。無獨有偶,在《希望的田野》中我們看到了一名好干部——徐大地,工作中他務實肯干,講究效率,有理想帶著大家勤勞致富的干部形象,充分發揮了作為一名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除此之外導演也在竭力挖掘他身上的人性與人情,劇中沒有刻意回避他與妻子親昵、擁抱的動作,在失去親人的痛楚,這些人物的塑造更傾向于人性化,也更加真實可信。
這種多元化人物的塑造成為推動劇情進展的潤滑劑,通過對這些“中間式”村民形象的挖掘,加強了作品的思想性與藝術性,這種帶有現實批判精神和直指主體性亦為作品增添了新的精神內涵和藝術品位。
四、喜劇元素植入為作品增添藝術含量
電視作為一門“家庭藝術”,其功能不僅僅體現在藝術教育上,更是維系其家庭成員的情感紐帶,帶給觀眾更多的精神撫慰和審美愉悅,隨著人們生活節奏的加快和受后現代主義思潮的影響,自進入新世紀后,眾多的農村劇將喜劇元素植入其中,通過喜劇氛圍來吸引觀眾,經過市場認證,這種喜劇化風格的作品也易獲得觀眾的青睞!觀眾也期望從電視中能得到放松和歡樂,是他們高強度工作之余的一種精神壓力的消解。總體觀望,這些作品都善于運用夸張的表演、幽默詼諧的臺詞、方言的加入來制造喜劇效果。特別是把人物身上的某些弱點進行夸張、錯位性的表現出比正常人還弱智等性格缺陷來制造笑點和觀賞性。
首先是地域特色文化與電視的無縫隙連接。趙本山系列作品來分析:《劉老根》劇中大量植入“二人轉”藝術,將東北人那種大起大落、豪爽直率的性格盡顯銀屏,《馬大帥》中讓人印象深刻的哭喪片段,感情真摯,臺風幽默同樣得到觀眾的稱贊;而與之相對的另一部作品《黨員二楞媽》中則加入陜北的信天游片段,將自己心中情感含蓄深情的表達出來,讓我們領略到濃郁的陜北地域文化及人物的真性情。
其次是喜劇手法靈活運用。尤為體現在東北農村劇中,《劉老根》中藥匣子就是一個典型人物形象,他自詡為“有素質、有品位的文化人”,深入生活中是一個喜好賣弄文采,卻時常張冠李戴,自稱醫術高明,有醫德,追求名利、謀取私利卻是他的代名詞,劇作正是利用這些人物言行的反差來制造強烈的喜劇效果,讓人忍俊不禁;同樣在《籬笆女人和狗》巧姑的人設也堪稱絕妙,在與村人爭吵時,妙語連珠,讓對方毫無招架之力,回到家中卻私底下開小灶煮餃子,她的“奸和滑”與大媳婦的“直與憨”也形成鮮明的對比,易讓人感受到來自生活的喜劇之樂,這些對于藝術作品的加工再創造,更好的趨于觀眾的接受心理,使整部作品的喜劇效果烘托的恰到好處。
五、把道德意識和文化內涵寓于創作中
所謂的道德意識,就是對真善美、假惡丑的正確判斷,并自覺地在作品中歌頌真善美,抵制假惡丑,農村劇的創作在這一方面有了很大的提升,農村劇一個本來就與現實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性,因此,在創作的時候更不能局限于表象的真實,須透過具體的事件,挖掘其反映出來的社會的、人文的、歷史的內涵,從而達到本質、哲理的真實。
電視文化應具有人文關懷,倡導人們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它所關懷的是人的精神世界和心靈狀態,具有超越時代、社會的特質。具體表現在對人的命運、價值、理想等方面的關懷,對精神文化現象的反思,以及對理想的價值觀和人格統一的塑造。優秀的藝術作品都充滿了對“人之所以為人”的價值解讀。
農村題材電視劇敘事手法多以小見大,表現的多是農村真實的生活原態,從生活中挖掘情感表述,這也是緊扣“三貼近”原則,在創作中關照現實,堅持以人為本,從生活中汲取素材進行再創造,但也并非所有的生活素材都可以成為農村題材電視劇所表達的對象,畢竟電視劇不是紀錄片,它具有審美的標準,而美感只是其價值取向之一。
新世紀后農村劇注重農民的精神需求,訴求農民內心世界的表達儼然已成為創作者孜孜不倦的追求和創作理念。素有“東北三部曲”之稱的《籬笆·女人和狗》便以改革開放來東北大家庭的分化與新舊觀念的張力為切入點,以此引發的對于個體生命的精神裂變與心靈苦楚為主要內容,將現代性歷史進程中個體精神的焦慮、彷徨與掙扎進行了細致的描繪與呈現,此劇觀照了改革大潮中農民心靈蛻變的痛苦,將人文關懷作為作品價值取向,不僅劇中的畫面具有現實性,而且人物性格符合特定年代的邏輯,堪稱民族根性與時代脈搏的佳作,對后來農村劇的創作也具有示范意義,堪稱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村的“村史”!
而處于全面確立期的電視劇代表《喜耕田的故事》也是透視人文關懷很好的一部作品。該劇中的喜耕田、二虎為了農村發展與和諧可以說是殫精竭慮、舍身忘我,樹立了村干部的標榜形象,但并非一味的“高大全”形象,而是聚焦了這個時期改革中的難點問題,從農民喜耕田的視角再現了新農村建設中的問題,因而具有強烈的現實主義風格,表述農村中瑣碎的生活,一反口號式的氣勢磅礴的農村變革圖景,這個過程中我們感受到的是農民本身的態度由被動轉為主動,在適應時代變化的基礎上,農民們潛意識里滋生的一種主觀能動性行為。是時代變革后帶給他們實質性的互惠推動他們改革的欲望,創作者真正地關懷著農民的生活和精神狀態。正是這種道德意識和人文精神的滲入使得作品更具文化內涵。
結語:
農村劇總體在數量上處于上升趨勢,但能夠稱得上精品的卻鳳毛麟角,特別是在進入新世紀后作品大多與娛樂性相結合導致很多作品缺少文化內涵和人文關懷,只是單純的充當了精神食糧,且有格調低俗化的趨勢。農村劇固然要通俗易懂,但不等于媚俗,在美學品格追求上應更注重文化品位的提升,呈獻給觀眾豐富的審美體驗同時能夠若有所思。
參考文獻
[1]薛晉文:《中國農村題材電視劇研究》[M],中國電影出版社,2013年
[2]魏南江:《中國類型電視劇研究》[M],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1年
[3]孔靜:《東北農村題材電視劇藝術特色研究》[D],西北大學,2009年
[4]孫國強:《論當代農村題材電視劇的發展與審美特征》[D].桂林:廣西師范大學,2010年
[5]托婭:《論新世紀以來農村題材電視劇的創作特色》[D].呼和浩特:內蒙古師范大學,2010年
作者簡介:劉振博(1993.11——),男,漢族,陜西咸陽人,藝術學碩士,專業:戲劇與影視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