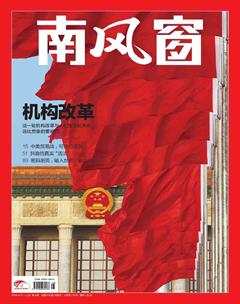特朗普為何“拉黑”俄羅斯
雷墨

最近俄羅斯與西方國家之間相互驅逐外交官的行為,在規模上創下了冷戰后歷史之最。甚至在冷戰高潮期間,這樣的規模也甚為罕見。
盡管事件起因是俄前情報人員及其女兒在英國遭人下毒,但真正的看點是美國與俄羅斯之間的較量。這兩個國家“出手最重”,相互驅逐了對方60名外交官,關閉了對方一個總領館。
在外交層面,大規模驅逐外交官、關閉使領館是國家間關系惡化的顯性標志。
真假曖昧
這一切,都發生在美國有一位“親俄”總統的背景下。2016年競選期間,特朗普頻頻對俄羅斯釋放善意。那時,他反對對俄經濟制裁,質疑北約的存在價值,甚至認為應該承認克里米亞并入俄羅斯。
入主白宮后,雖然這些競選語言沒有變成現實政策,但他還是多次表達改善美俄關系的意愿。在外交場合,特朗普對北約盟國領導人表現得一臉怒氣,對普京卻看上去畢恭畢敬。特朗普對莫斯科的曖昧態度,似乎是一個謎。
特朗普外交的基調,起初是建立在“反奧巴馬”基礎上的。他對俄羅斯釋放善意的初始動機,某種程度上說是反對奧巴馬對俄羅斯的惡意。事實上,執政一年多以來,特朗普政府對俄政策行為,在強硬程度上一點不輸奧巴馬。去年4月,美國導彈襲擊敘利亞政府軍目標;12月,特朗普批準向烏克蘭提供包括反坦克導彈在內的致命武器。這些都是奧巴馬政府時期未曾逾越過的政策界限。
2016年12月,奧巴馬政府以俄羅斯干預美國大選為由,驅逐了35名俄駐美外交官。今年3月26日,特朗普政府以俄涉嫌在英國“投毒”為由,驅逐了60名俄駐美外交官,并關閉俄駐西雅圖總領館。從與美國利益關聯度來看,兩件事中后者遠不如前者,但特朗普回應的強度卻遠甚于奧巴馬。在某些分析人士看來,特朗普對俄羅斯下重手有刻意為之之嫌,他需要通過對俄強勢來撇清自己的當選與莫斯科之間的關系。
“通俄門”是特朗普極力躲避的一扇門。對俄干預美國大選的調查有三個執行主體,其中眾議院情報委員會的調查已于今年3月23日終結,結論是沒有發現特朗普競選團隊與俄羅斯有勾連的證據。但參議院與特別調查委員會的調查仍在繼續,而且后者的調查對象已經擴展到特朗普家人。所以在目前這個階段,特朗普對俄外交的首要、同時也是最緊迫的目標,是不讓“通俄門”持續發酵,以免侵蝕自己當選的合法性。
特朗普新提名的國務卿蓬佩奧和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在對俄態度上都是十足的鷹派。蓬佩奧在很多外交議題上與特朗普“理念相合”,但唯獨不認可他對俄羅斯的曖昧態度。他在出任中情局局長期間,一直力推對俄羅斯干預美國大選加以制裁。博爾頓在獲得提名后,仍公開批評特朗普打電話祝賀普京勝選的做法。這樣的執政團隊將如何影響特朗普政府未來的對俄外交不得而知,但傳遞信息的功能已經體現出來。
不過,特朗普對俄外交中也并非完全沒有改善美俄關系的意愿。3月20日,他不理會身邊顧問們“不要祝賀”的提醒,主動給普京打電話祝賀其成功連任。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這都不會只是禮節性的問候。特朗普對此解釋稱,建立良好的美俄關系,不是為了他個人的利益,而是為了美國的利益。“俄羅斯能幫助解決朝鮮、敘利亞、烏克蘭、‘伊斯蘭國,甚至即將到期的美俄《削減戰略武器條約》等問題。”
“克林頓與葉利欽一起吹過薩克斯,布什曾說他看到了普京的靈魂,被特朗普鄙視的奧巴馬也曾派希拉里去按下美俄關系的重啟鍵。”
特朗普的這種想法是否站得住腳暫且不論,但的確符合他外交中的“交易思維”。在他看來,美俄是有可能通過討價還價,在地緣政治上達成交易的。一味地對抗,就沒有了“交易”的可能。而且,把“讓美國再次強大”作為政治承諾的特朗普,不會沒有讓自己成為“偉大總統”的想法。在諸多重大國際問題上,俄羅斯都是美國避不開的談判對象。這樣來看,特朗普對俄羅斯的曖昧態度可謂亦真亦假。
無形之手
“通俄門”讓特朗普對俄羅斯的曖昧態度,蒙上了一層神秘色彩。但在外交操作手法上,特朗普對俄羅斯“示好”一點也不神秘。
美國喬治城大學俄羅斯問題學者安吉拉·斯坦特曾寫道,冷戰后歷任美國總統,都曾把美俄兩國視為能聯手解決世界重大問題的大國。“克林頓與葉利欽一起吹過薩克斯,布什曾說他看到了普京的靈魂,被特朗普鄙視的奧巴馬也曾派希拉里去按下美俄關系的重啟鍵。”
但與其前任不同的是,特朗普對俄外交的蜜月期,還沒有開始就結束了。特朗普身邊有太多制約他的無形之手,讓他連重啟的機會都沒有。被特朗普炒魷魚的前國務卿蒂勒森,在告別講話中還在警告美國要提防俄羅斯。美國財長姆努欽多次警告俄羅斯不要破壞美國的穩定。3月15日,國土安全部與聯邦調查局聯合發布報告,詳述美國遭俄網絡攻擊的細節。不難想象,如果想緩和美俄關系,特朗普在他的政府內部最能體會到孤獨感。
還是在3月15日,美國財政部宣布對俄羅斯5家實體和19名個人實施經濟制裁,報復其干預美國大選和網絡攻擊行為。這是特朗普政府首次以干預美國大選為由,主動追加對俄經濟制裁。當天,美國共和黨全國委員會特意發布聲明,對特朗普對俄強硬的做法表示肯定。這個聲明與其說是肯定,不如說是施壓,提醒特朗普立場別后退。也就是說,共和黨內部的政治氛圍,至少對特朗普的對俄外交構成了軟性約束。
硬性的約束來自國會。去年7月底,美國國會援用《敵國貿易法》通過對俄羅斯(以及伊朗和朝鮮)的制裁法案。根據美國的政治制度,這個法案總統特朗普是無權撤銷的。更為微妙的是,這是冷戰后美國首次動用這個法律制裁俄羅斯,隱含的意思是,美國在官方文件上將俄羅斯定義為“敵國”。1992年葉利欽與老布什簽署的《戴維營宣言》,明確美俄不視對方為“敵國”。微妙之處,折射的是美俄關系的深刻變化。
特朗普改善美俄關系的希望之所以渺茫,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整個美國政界對俄羅斯的認知已經變得相當負面。從美國的角度看,如果說近年來的烏克蘭危機、敘利亞危機,導致俄羅斯形象惡化,那么干預美國大選的行為則讓這種形象演變為“毒化”。無論是今年11月的中期選舉還是2020年的大選,俄羅斯因素都會是特朗普的政治負資產。甚至,改善美俄關系也會成為主流候選人不愿觸碰的政治紅線。
“很大程度上這是幻想的破滅,這個幻想就是特朗普長期認為的與普京達成某種大交易。”美國前駐俄羅斯大使威廉·伯恩斯,在談到美國驅逐俄羅斯外交官事件時這樣說。在卡內基莫斯科中心學者波波·羅看來,幻想破滅的不只是華盛頓,還有莫斯科。“美俄關系比冷戰后任何時期都更加惡化了,莫斯科起初希望特朗普的勝選可能啟動俄美接觸,現在這個希望已經破滅了。”
矛盾交匯點太多,利益連接點又太少,是制約美俄關系更本質的因素。目前俄羅斯對外貿易中,對美貿易額占比僅為4%。相比之下,歐盟、中國對美貿易額占比約40%和15%。在美國貿易伙伴中,俄羅斯的排名從未進入過前20位。從經濟角度講,俄羅斯對美國的重要性即便不是微不足道,也是相當微小。俄羅斯與美國經濟的弱連接性,導致其幾無反擊美國經濟制裁的籌碼。
新冷戰?
3月31日,美國駐圣彼得堡領事館降下星條旗,60名美國駐俄外交官收拾行囊打道回府。
早在美國宣布關閉俄駐西雅圖領事館后,俄駐美使館方面曾回應稱,美國想讓哪個駐俄領事館被關閉?是符拉迪沃斯托克、葉卡捷琳堡還是圣彼得堡?莫斯科最終選擇關閉圣彼得堡領事館,或許是想傳達某種特殊意義。18世紀末美國與俄國建交時,大使館就設在圣彼得堡。如今的美國駐圣彼得堡領事館,正是在當初原址上所建。
梅德韋杰夫總統時期建立的俄美雙邊總統委員會,多年前就停止了運作。上一次俄羅斯總統正式訪問美國,還需要追溯到2009年普京任總理的時候。
俄羅斯的回應看似在展現強硬,實則只是在表達情緒。關閉對美俄外交關系具有象征意義的領事館,并不意味著莫斯科打算與華盛頓“絕交”。據美國媒體報道,在俄前雙面間諜于英國遭人下毒事件曝光后,俄駐美大使阿納托利·安東諾夫一直在主動尋求與美國政界人士接觸。但截至美國宣布驅逐俄外交官,安東諾夫只見到了幾位國會議員,而副總統彭斯、白宮辦公廳主任凱利、司法部長塞申斯等政府要員,均選擇避而不見。
安東諾夫求會見而不得,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美俄之間的外交溝通已經出現了明顯的問題。梅德韋杰夫總統時期建立的俄美雙邊總統委員會,多年前就停止了運作。上一次俄羅斯總統正式訪問美國,還需要追溯到2009年普京任總理的時候。4月2日,俄總統助理烏沙科夫透露,特朗普在3月20日與普京通話時,曾提議在華盛頓舉行首腦會晤,俄方對此態度積極。
短期來看,這樣的美俄首腦會晤舉行的可能性并不大,如果不是根本不存在的話。或許,特朗普有學習里根總統的意圖,希望重演美蘇戰略大交易的歷史,但他并不擁有重演歷史的現實條件。
此外,困擾特朗普的“通俄門”掩蓋了這樣一個事實,即美俄關系正呈現出越來越多的冷戰特點,而且這并不以特朗普的意志為轉移。
俄羅斯學者康斯坦丁·庫德利在去年底的一篇文章中寫道,雖然此前美國人或多或少在尋求把俄羅斯融入全球化進程,但如今他們正在采取相反的政策,最大限度地遏制俄羅斯,并將其孤立在國際市場之外。經濟制裁的殺傷效果,不會止于經濟層面。只要美歐的經濟制裁不解除,莫斯科提出的諸如歐亞經濟聯盟這樣的戰略,實施起來就會舉步維艱。美國的次級制裁(制裁相關第三方),一直使中亞國家在與俄羅斯的經濟合作上投鼠忌器。
經濟制裁、大規模驅逐外交官,對俄羅斯也是一種政治殺傷。因為這些外交行為,客觀上在把俄羅斯塑造成國際社會的“另類”。從這個意義上說,美俄關系正在滑向冷戰式對抗。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主席理查德·哈斯就認為,美俄關系已經陷入了冷戰。他近日撰文稱,美國人必須認識到防守是不夠的。“無論出于何種原因,如果特朗普繼續縱容俄羅斯,那么美國國會、媒體界、學術界都應該公開曝光普京的墮落統治。”
某種程度上說,特朗普需要“拉黑”俄羅斯,才能避免自己被俄羅斯的另類形象給拖下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