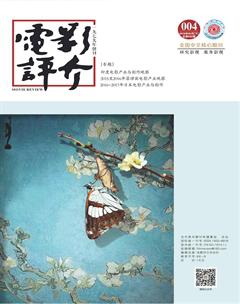醫療媒介形象的重構與傳播
宋陽 佟延秋
2017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其中“健康”一詞共出現351次。在十九大報告中,一系列有關“健康中國”的戰略被提,這也是為應對人口老齡化和整體醫療資源不足全球性挑戰所貢獻的中國解決方案。我國目前的醫療現狀仍呈現出倒金字塔結構,大量患者更傾向于到醫療資源豐富的三甲醫院,基層醫療機構難以吸引患者,醫患關系仍是2017年醫療輿情的關鍵詞。
隨著社會的網絡化,傳播媒介的結構和性質發生了根本性的變革,傳播媒介對微觀個體行為的影響也日益顯著。紀錄片是一種以真實生活為創作源泉,以真人真事為表現對象,以展現真實為目的,通過真實引發人們思考的非虛構的影視作品。[1]紀錄片不僅僅是一種形象傳播,其中還種蘊含著公共政策。[2]近年來,形象傳播紀錄片層出不窮,類型不斷豐富,題材更加多元化、立體化。紀錄片中非虛構的敘事模式特別適合醫療媒介形象傳播,其鮮明的在場感,對促進公眾理解相關政策、事件具有重要作用。紀錄片由于其內容題材選擇面廣,不受時空限制,反映社會現實,對引導社會良性發展、構建和諧醫患關系具有重要的意義。
《人間世》最早見于莊子的一文,由七個故事組成,這些故事的主旨分別為:內養、安命、誠言、慎行、藏拙,討論的是人世艱險,但在內修“心齋”之術的基礎上,外修誠言、慎行、藏拙工夫,可以達到內圣外王之境,既可應時用世,又可全身自保,提出的是一種基本的為人處世之道。與此不謀而合的是,同名紀錄片《人間世》(以下稱《人間世》)向人們發起了一場關乎生與死的靈魂追問,其播出恰逢2017年我國醫患輿論的頻發期,該片的播出被認為是消解醫患矛盾的“銀彈”,但傳播學理論研究表明,媒介的傳播效果是有限的。疾病尚無法全部治愈,一部紀錄片更是無法做到藥到病除。[3]
世界衛生組織(WHO)對健康的定義是:“健康不僅是軀體沒有疾病和身體不虛弱,而且是身體、心理、社會功能三方面的完滿狀態。”健康包括三重含義:其一,軀體沒病;其二,身心健康;其三,幸福美滿。[4]《人間世》作為現實生活之鏡,展現出紀錄片創作的最高價值,通過真實影像的力量直面醫患關系的現狀,敢于突破人們的認知邊界,激發受眾思考,從而重構社會對醫患關系本質的思考。因此,有必要對《人間世》的審美呈現進行探討。
一、《人間世》的敘事特色及傳播價值
(一)各自獨立而又相互呼應的敘事策略
《人間世》以上海多家知名醫療機構為背景,以急診室、手術室、重癥監護室等醫患矛盾、沖突的高發區為拍攝地點,記錄了醫生、患者、家屬三者之間的日常所見、所思、所感。該片由8個攝制組在沒有劇本、沒有提綱的情況下,歷經兩年完成,拍攝過程采用直接電影的方式進行拍攝,24小時、三班倒、蹲點拍攝,沒有人物預設,沒有情節預設。[5]《人間世》共10集,每集關注一類醫療主題;這樣的設置其實目的非常明顯,即以醫療機構為空間,通過具體的醫療案例構建出整體醫療的立體空間。雖不能反映醫療現狀的方方面面,但紀錄片作為社會的一個縮影,那些沒有被鏡頭所記錄的案例、場景則留給觀眾片后思考和想象。
如第1集《救命》中結尾字幕:2015年,瑞金醫院心臟外科,共收治1803名病人,70%為危重病人,死亡率為1.5%;2015年,瑞金醫院急診室,共收治7412人,死亡474人;2015年,瑞金醫院急診搶救室,入院人數266人,231人搶救成功。
從中可以看出,醫學并不能達到全部治愈,也會有失敗,這些都是真實生活的寫照——不完美,但真實。
真實是化解矛盾的力量源泉。醫患之間信息不對等、醫療機構市場化、醫患雙方行為博弈等對醫患關系產生影響。[6][7]無論是醫生還是患者,本質上都是作為人的屬性而存在的。在當下的醫療媒介形象傳播語境中,《人間世》特別注重對醫患關系中人的關注,關注那些共同面對來自于健康威脅和挑戰的人群,他們可能是醫生,也可能是患者,也可能是身體健康的人,這使得《人間世》在當下的傳播能夠引起觀眾的共鳴。醫生站在病床旁邊觀察病人與病人倒在床上觀看醫生,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心態。醫患矛盾將醫生和患者至于一種相互對立的位置,但醫生和患者在面對疾病的立場是一致的,這種悖論的成因多種多樣。《人間世》通過鏡頭語言回應著這段至今仍熠熠閃耀著人文之光的銘言,同時也將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再次擺在世人面前——疾病到底是不是可以完全治愈?與那些展現“完美”的醫療類題材的電視劇相比,《人間世》更多的是用客觀的鏡頭將現代醫學在疾病面前的現實和無奈,冷靜地展示給觀眾。人有的時候最難接受的就是現實,《人間世》的這種真實并非只是客觀的真實,更是心靈的真實。作為一個觀察者,而不是一個控制者,《人間世》讓觀眾站在自己面前,懷著敬畏的心態來面對這個世界。[8]
(二)“直接電影”式的敘事手法
《人間世》在敘事手法上,深入到正在發生的醫療事件當中,從第一人稱視角出發,讓觀眾親歷事件發生現場,給觀眾最直觀的事實感。在節目欄目化、紀錄片商業化的今天,《人間世》這種相對傳統的記錄方式與商業化醫療題材影視作品中經常出現的那些驚心動魄的手術過程、讓人潸然淚下的解說詞、極強視覺沖擊力的特效相比,《人間世》所呈現出的醫療場景與公眾心目中的醫療場景存在較大差異。《人間世》讓人們從客觀冷靜的視角重新審視生命、疾病和醫學,讓受眾從更加客觀冷靜地接受現實,引發對醫患溝通的反思。
醫患雙邊行是信息、技術、市場博弈的結果。患者方,患者作為主體的“離場”所導致的醫患間缺乏交往合理性的根基、醫患間信息不對稱所致權力地位不平等、醫患雙方因缺乏共同的“生活世界”而難以有效溝通。[9]法國哲學家米歇·福柯提出知識與權力的共謀,醫學知識的高度專業性必定與權威性相伴;當患者遭受病痛時而不得不求助于醫生,而高度專業化的醫學知識體系加劇了醫患之間由于信息不對稱所導致的患者弱勢地位。[10]德國著名哲學家、社會學家和思想家哈貝馬斯認為,在工業化程度較高的社會中,工具理性被發揮到極致,如果人與人之間的溝通理性沒有得到相應的發展,工具理性則會變為具有毀滅性的非理性。由于技術的進步并非價值中立,飛速發展的醫療技術得以進一步鞏固并加劇醫患雙方話語權的不平等。總體來講,社會經濟文化背景已成為影響醫患雙方的行為模式的主要因素。《人間世》在幾個特定或者說是固定的空間中,將醫生、患者、家屬、醫療體系整合在一起,這不僅僅是簡單的醫患關系,更是當今社會的真實寫照。
(三)理性化解說詞的運用
解說詞是紀錄片中很具表現力的敘事元素,是紀錄片創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紀錄片解說詞既要符合紀錄片的“真實”核心,同時還要富有藝術性并留給觀眾想象空間,既能渲染氛圍,又能引發思考。好的解說能讓紀錄片充分體現它的人類“生存之鏡”的價值。[11]
如第8集《堅持》:“醫學是一個不斷求證的過程,掛號,檢查,問診,手術,每一步似乎都環環相扣,嚴絲合縫……甚至會把醫生、患者,都推入無奈的境地。”這段解說詞將整個就醫環節全部概況,觀眾需要通過理性思維的補充才能解解說詞所要表達的含義,不僅抒發了作者的情感,同時也在引發觀眾的情感沖動。
《人間世》中的解說詞介入畫面的并不多,且都是出現在影片在中的關鍵節點處,這避免了對觀眾觀影思路被打斷,能夠留給觀眾一定的思考空間。紀錄片中的解說詞,是訴諸觀眾聽覺器官的一種文字語言,是作者理性思維的直接外化。紀錄片僅靠“電影眼睛”式的紀實手法很難達到歷史的厚重感。紀錄片需要一種詩性的語言,使其在被理解和被接受的過程中為紀錄片解說詞的發展提供合理的存在空間和創作表達。[12]受消費主義的商業導向、商業性紀錄片鋪天蓋地而來以及對收視率的追求下,傳統觀察式紀錄片受到巨大的沖擊,其拍攝的理念和策略遭遇種種質疑和挑戰。[13]《人間世》以堅持不介入、不干涉、長期觀察、讓事實價值自然凸顯的方式傳播科學精神的創作思維再次煥發出光彩。
二、《人間世》對醫學人文教育的啟示
醫學技術的發展對提高人類健康、延長人類壽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醫學技術發展背后的一面卻是忽視了醫學內在的、固有的人文內涵,有溫度的醫學不見了。[14]取而代之的是醫者威嚴冷峻的權威態度和晦澀難懂的專業術語,醫患之間的鴻溝越來越大。醫療活動中醫患雙方應當在理性因素的主導下發揮非理性因素的積極作用,有力遏制其消極作用,從構建更加和諧的醫患關系。[15]《人間世》以客觀冷靜的筆調,對醫生、患者、家屬三類人的行為進行忠實記錄,通過“真實”引發觀眾思考。使受眾通過影像認識和思考醫學、醫患關系,經過受眾分析、比較、推理和判斷得出結論;而非憑直覺、情緒狀態和潛意識形成的片面觀念對事物所作的結論、定性及形成的看法和觀點。[16]
醫學人文教育不僅需要情感的催化,更需要理性的支撐,二者缺一不可。任何時候都必須充分重視個體理性能力的培養,所以,真正合適的醫學人文教育在堅持理性與情感并重和統一的基礎上,決不能漠視理性教育的價值。一味地強調情感交流、情感融通作用,不僅無助于醫學人文教育目的的實現,而且也不利于個體高尚人格的培養。在非理性醫學人文教育實現的過程中,還是要以理服人,加強對受眾的理性認知能力培養。
醫學人文教育的本質是面向未來的。醫學教育的發展不是定位在自然人的高度,而是定位于社會人的高度為未來培養高素質的人才。《人間世》的超越性就在于通過畫面展現出現實世界向理想世界的轉化過程。醫學人文教育的超越性意義隨著社會的發展,無論是醫學人文教育活動本身,還是其表現的實踐價值以及潛在價值,都將越來越明顯。醫學人文教育的超越性鼓勵人們不再滿足眼前的物質利益,而是追求崇高的精神境界。
參考文獻:
[1]虞吉.渝派紀錄片:歷史文化支點與現實建構呈現[J].現代傳播,2009(5):86-88.
[2]佟延秋,宋陽.“一帶一路”倡議下渝派紀錄片提升路徑研究[J].電影評介,2017(12):6-9.
[3]梁君健.《人間世》展現了紀錄片的痛感與力量[N].新京報,(2016-08-22)[2018-02-03]http://sports.163.com/16/0822/
01/BV1NF8NF0005227R.html.
[4]唐鈞.“健康中國”不能被誤導為“醫療中國”[J].中國醫療保險,2016(10):24-25.
[5]羅鋒,鄔喬.題材突破與敘事超越——醫療紀錄片《人間世》的方法論與審美觀分析[J].中國電視,2017(5):24-28.
[6]顧昕.行政化還是市場化:醫療服務體系的制度演變[J].中國公共政策評論,2009(10):23.
[7]顧昕.健康產業發展之道:應先搞清利益機制[J].中國醫院院長,2017(6):85-87.
[8]黎小鋒.壁上觀世相——直接電影在中國的嬗變[J].北京電影學院學報,2011(1):16.
[9]尤爾根·哈貝馬斯.交往與社會進化[M].張博樹,譯.重慶:重慶出版社,1989:13.
[10]嚴予若,萬曉莉,陳錫建.溝通實踐與當代醫患關系重構——一個哈貝馬斯的視角[J].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7(3):171-177.
[11][12]佟延秋.紀錄片解說詞芻議[J].電影評介,2012(22):19-22.
[13]殷杰,畢志聰.當代科技紀錄片創作的哲學價值[J].山西高等學校社會科學學報,2017(5):10-13.
[14]方天云.醫學科技向左,人文向右?——論醫者職業風險的解構[J].醫學與哲學:人文社會醫學版,2011,32(9):39-41.
[15]伊焱,陳士福.醫患關系中的非理性因素及其優化探討[J].中國醫院管理,2014,34(5):60-61.
[16]宗寶玉,熊紅芳,李占江.老年抑郁癥患者的非理性信念和應對方式[J].中國心理衛生雜志,2012,26(1):1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