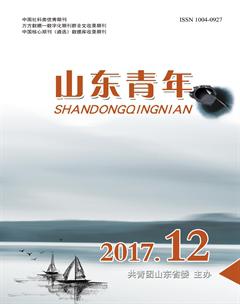試論劉敬的和親思想
王妍
摘 要:劉敬的和親思想是當時西漢初期特殊歷史背景下的產物,在西漢前期對匈奴的和親政策對緩和匈奴南下騷擾、保證邊境地區安寧起到了積極作用。其和親思想衍化為一種和親政策成為中國古代中原王朝對待少數民族政權的主要政治和外交手段之一。下面主要從劉敬和親思想的產生過程、內容、原因、影響等方面作簡單梳理。
關鍵詞:劉敬;和親思想;西漢;匈奴
劉敬,本名婁敬,后因劉邦賜姓改名劉敬,西漢初齊國盧人。時劉敬作為齊國的戍卒,正被發往隴西戍邊,同鄉虞將軍引薦他見劉邦,力陳都城不宜建在洛陽而應在關中。劉邦疑而未決,張良明言以建都關中為便,遂定都長安。賜姓劉,拜為郎中,號奉春君。
漢高祖七年,劉敬出使匈奴,認為不可擊匈奴,劉邦非但不聽,反將他押在廣武。劉邦先到平城,主力未至,冒頓單于傾全國之兵,乘劉邦巡視白登之際,將劉邦團團圍住。陳平解白登之圍后,高祖復歸至廣武,特赦劉敬,當面認錯,乃封劉敬二千戶,為關內侯,號為建信侯。后針對匈奴問題,劉敬建議與匈奴和親。
《史記》中詳細記載了劉敬提出的和親思想:
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當是時,冒頓為單于,兵彊,控弦三十萬,數苦北邊。上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群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為。”上曰:“誠可,何為不能!顧為柰何?”劉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彼知漢適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漢所馀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為子婿;死,則外孫為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兵可無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柰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①
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劉敬的和親思想十分具有針對性。首先,漢代初年,匈奴處于蓬勃發展的上升期,在冒頓單于帶領下,“西擊走月氏,南并婁煩、白羊河南王”②,“后北服渾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之國”③,“盡服北夷,而南于中國為敵”④,成為匈奴疆域最廣大的時期,時為漢朝最強勁的對手,和親思想有利于對抗強大的北方匈奴。其次,漢初國內經濟凋敝,加上連年戰爭造成國力虧損,不宜進行大規模征戰,且漢族屬農業民族,與匈奴相比,對土地的約束性大,時值漢朝實行無為而治的修養生息政策,和親思想適應了當時西漢國內外政治經濟環境。
劉敬和親思想的具體做法主要包括遣公主、歲奉匈奴、諭以禮節幾個方面。第一,“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⑤,即把長公主嫁給匈奴單于并且配以豐厚的嫁妝,這樣匈奴單于“必慕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原因是匈奴貪圖漢朝的豐厚財禮。漢朝這樣做正是迎合了匈奴貪圖財物的心理;第二,“以歲時漢所馀彼所鮮數問遺”,將一年四季漢朝多余而匈奴少有的東西多次撫問贈送,這樣做可以安撫匈奴,避免雙方發生大規模戰事,一定程度上緩解匈奴因物資匱乏而侵擾邊境的問題;第三,“使辯士風諭以禮節”,與匈奴贈送財物時,順便派能言善辯之人用漢朝禮節加以開導他們,冒頓在位時自然是漢朝的女婿,等到他死后,他的兒子漢朝外孫就是繼任單于,哪里聽說過外孫敢同外祖父分庭抗禮的呢?如此種種,便可“兵可無戰以漸臣也”⑥。
劉敬認為“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群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⑦。只有與匈奴和親,才能“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⑧。第一,美人計不僅可以解圍,還可以安邊。⑨漢初剛平定天下,國力不夠強大,以武力制服匈奴不可行,而冒頓單于憑借武力樹立起威勢,是不能用仁義道德說服的;第二,和親可以收到“無戰以漸臣”的效果。⑩把長公主嫁給匈奴單于并且配以豐厚的嫁妝,派能言善辯之人用漢朝禮節加以開導他們,這樣一來,“冒頓在,固為子婿;死,則外孫為單于”,而外孫是不會與外祖父為敵的;第三,以“和親協定”約束雙方。公元前199年,漢匈締結“和親協定”,主要包括五項條款:一是漢朝將公主嫁給匈奴單于;二是漢與匈奴劃疆立界:長城以北的大片土地歸匈奴單于,長城以內的土地仍歸漢朝所有,約定雙方互補侵擾,匈奴不準進到長城以內,漢朝居民也不得到長城以北;三是“漢與匈奴約為兄弟”,雙方成為兄弟之國,享有平等地位;四是漢朝“歲奉匈奴絮繒酒米食物各有數”,而匈奴不再侵擾漢朝邊境;五是雙方進行一些“通關市”的活動。此后通過和親,雙方確實保持了相對和平穩定的局面,說明“和親協定”對雙方的確實有一定的約束作用。
劉敬的和親思想是當時西漢初期特殊歷史背景下的產物,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外部因素也有內部因素。
外部因素主要來自匈奴的威脅。第一,從漢初到漢武帝時匈奴處于蓬勃發展的上升時期。匈奴自秦末漢初以來勢力不斷發展壯大,冒頓單于、老上單于、軍臣單于三朝執政期間,征服了東胡、丁零、月氏、烏孫等諸部,統一了北方草原。強大的匈奴成為漢朝西北邊境的重要威脅。第二,匈奴當時處于比西漢落后的社會形態,需要的是肥沃的牧場和眾多的奴隸。匈奴作為北方游牧民族,其主要生產經營方式是游牧和狩獵,對自然環境的依賴性很大,很多東西無法自給,而西漢的物質文明水平遠高于匈奴,再加上匈奴“茍利所在,不知禮義”的天性和“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的機動性,決定了西漢王朝不能以武力解決漢匈關系,只能采取相對緩和的和親政策。
內部因素主要取決于西漢王朝當時的政治經濟形勢。第一,西漢初期,經濟蕭條,民生凋敝。“漢興,接秦之敝,諸侯并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高祖乃令民得賣子,就食蜀、漢。天下既定,民亡蓋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漢朝無力抵御強大的匈奴,和親政策可以緩和與匈奴的矛盾,換取暫時的和平;第二,西漢地方割據勢力的反動與挑撥,對匈奴不斷侵擾漢朝邊境起了激化作用。西漢初期實行的是郡國并行制,各地大大小小的諸侯王國有二十多個。各諸侯王具有很大的獨立性,容易各自為政,造成藩鎮割據,成為威脅中央集權的離心因素。更有甚者,與匈奴勾結進行顛覆活動。西漢初年,漢高祖劉邦把韓王信改派到代地,建都馬邑城。匈奴大規模進攻馬邑,韓王信轉而投降了匈奴。劉邦聽說“信與匈奴欲共擊漢”,大怒,親自領兵前去迎擊匈奴,以致被圍困平城,后來利用陳平的“美人計”才得以脫困。第三,劉敬作為一屆謀臣,善于審時度勢,他深受儒家傳統的“夷夏觀”的影響,又加上不久前“白登之圍”的解除,啟發了劉敬,才產生了通過“遣公主、歲奉匈奴、諭以禮節”等方式達到“兵可無戰以漸臣”的和親思想。其中,“諭以禮節”還包含了“以夷變夷”的觀念,這也成為了此后中國古代民族關系思想的主要觀點之一。
對劉敬的和親思想演化為一種針對邊疆少數民族的和親政策。自漢高祖劉邦之后,惠、文、景至漢武帝初期,一直沿襲了與匈奴的和親政策。和親政策也產生了巨大的歷史作用:第一,和親期間,盡管匈奴仍時常襲擾侵掠西漢邊境,但雙方沒有發生大規模的戰事,邊疆秩序基本安定,一定程度上緩和了匈奴的侵擾,客觀上為西漢發展經濟、增強實力贏得了寶貴的時間,西漢得以休養生息,形成了“文景之治”的封建盛世,為漢朝的鼎盛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第二,和親政策促進了西漢與匈奴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和親公主帶去了中原先進的文化,對匈奴的經濟文化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和親政策中的互通關市加強了漢匈雙方的經濟交流。這種經濟文化上的交流不僅促進了民族融合,而且客觀上在我國整體民族心理認同等方面的形成發揮了巨大作用。
總之,西漢初期的和親政策是在漢朝與匈奴力量對比不平衡的狀態下,權衡利弊而選擇的合理的外交手段,也是當時漢匈關系的重要方面。西漢前期對匈奴的和親政策對緩和匈奴南下騷擾、保證邊境地區安寧起到了積極作用。和親作為一種處理民族關系的有效方式之一,后來逐漸成為我國各民族統治者處理民族關系的一種較為常用的政策。
[注釋]
①司馬遷:《史記》卷九十九《劉敬叔孫通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2719頁。
②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一十《匈奴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2890頁。
③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一十《匈奴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2893頁。
④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一十《匈奴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2890頁。
⑤ 司馬遷:《史記》卷九十九《劉敬叔孫通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2719頁。
⑥ 司馬遷:《史記》卷九十九《劉敬叔孫通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2719頁。
⑦ 司馬遷:《史記》卷九十九《劉敬叔孫通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2719頁。
⑧ 司馬遷:《史記》卷九十九《劉敬叔孫通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2719頁。
⑨ 崔明德:《兩漢民族關系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9頁。
⑩ 崔明德:《兩漢民族關系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9頁。
司馬遷:《史記》卷九十九《劉敬叔孫通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2719頁。
崔明德:《兩漢民族關系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9頁。
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一十《匈奴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2895頁。
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一十《匈奴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2895頁。
崔明德:《兩漢民族關系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0頁。
崔明德:《兩漢民族關系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1頁。
崔明德:《兩漢民族關系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1頁。
司馬遷:《史記》卷九十九《劉敬叔孫通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2719頁。
司馬遷:《史記》卷九十九《劉敬叔孫通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2719頁。
崔明德:《中國民族關系思想的有關問題》,《煙臺大學學報》2012年第4期,第46-5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