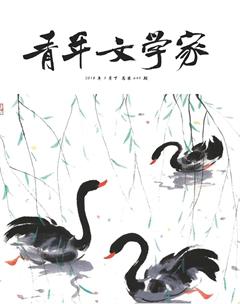論《葉甫蓋尼?奧涅金》與《罪與罰》中“回歸”的多重意義
摘 要:普希金的《葉甫蓋尼·奧涅金》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在風格、題材、人物等方面都截然不同,但兩書有相似的“回歸”意義,并在臨近結尾處得到了充分體現。本文結合兩書,聯系時代背景、作家思想,探討回歸的多重意義,根據空間轉換、人物精神信仰的轉變以及文化深層隱喻三個層次進行具體闡述。
關鍵詞:回歸;空間轉換;人物精神信仰;文化深層隱喻
作者簡介:唐曉雪,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2015級漢語國際教育專業,主要研究中國古代文學及語言學。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8)-09--02
《葉甫蓋尼·奧涅金》講述了貴族青年奧涅金的經歷,臨近結尾處寫了奧涅金回到彼得堡,在宴會上重遇達吉雅娜并燃起愛情的情節。《罪與罰》描寫了窮大學生拉斯柯爾尼科夫犯罪、自首和被流放的過程,臨近結尾處描寫了在荒涼的西伯利亞高原上,拉斯柯爾尼科夫突然抱住索尼婭雙膝的一幕。兩者看似并無聯系,卻展現出了相似的“回歸”意義。
“回歸”即出走后的回歸,可分為兩種,一種是顯性回歸,即生理意義上可見的、身體的移動,表現為空間位置的變化;另一種是隱性回歸,即心理意義上抽象的、精神的出走。
在顯性回歸的層次上,《葉甫蓋尼·奧涅金》的人物行跡直接有體現。奧涅金離開彼得堡去往鄉下,又離開鄉下出去旅行,最后回到彼得堡。整部作品也跟隨奧涅金從起點社交場開始,最終回到社交場。
《罪與罰》的回歸則需要跳出人物的生活框架,從更宏觀的層面來觀照。單就拉氏的行跡來看,他之前在彼得堡生活,后來被流放,身體出走到西伯利亞并未返回。但從整個人類歷史來看,這種從城市到自然、 從封閉空間到開放狀態的轉變確實可以稱作回歸。人類以前在森林、草原等開闊的“無邊界”地帶生存;后來建起了城鎮,用自己造的物質文明把活動空間限定在一個范圍之內。彼得堡就是一個相對封閉的空間,“妓院櫛比鱗次,居民們稠密地聚居在彼得堡中區”。拉斯柯爾尼科夫的房間“像口櫥柜”,馬爾美拉陀夫一家住在“籠子般的屋子”里。天空就像是一個巨型頂蓋,將彼得堡罩住,“街上熱得可怕,又悶又擁擠”。街上到處都是石灰、腳手架、磚塊、塵土,這意味著更多的密閉空間還在被建造。整個城市混雜著“夏天特有的惡臭”,這些臭味散發不出去,加深了封閉感。即使是走在路上的拉氏也是把自己封閉在糾結的心理狀態中,“不再注意周圍的一切”,“只是喃喃地自言自語”,仿佛帶著一個玻璃罩子在行走。在陀氏筆下,彼得堡就是一個“封閉”的存在。而流放地西伯利亞卻是一個完全與之對立的開放的狀態。那里人跡罕至,有寬闊、荒涼的河流,有“一望無際的草原”。灰色的大地、陽光的暖黃、初春草原的鮮綠構建出一幅開闊的圖景,給人以生機勃勃、充滿希望之感。在人類生存空間的意義上來看,拉氏的空間轉換就是一種回歸,回到了開放地帶。
在隱性層次上,兩書的主人公都通過心理意義的回歸得到了救贖,獲得了新生。奧涅金悟到了愛情,并以愛情為媒介,使生命體驗得以回歸。之前的奧涅金憂郁空虛,在彼得堡他“漫不經心地打了個哈欠”,伯父臨死前他卻“哈欠連天”,到了鄉下“他睡意朦朧”,他對一切都不大在意,對周圍事物都感到倦怠,這種昏昏欲睡的樣子寓示著他封閉了自己的感情體驗,也寓示著未完全覺醒的狀態。但他與連斯基能“彼此感到喜歡,每天騎馬會面難舍難分”,一方面是因為他們都接受了先進思想,有共同話題;另一方面,“詩人語言的熱烈激昂”和“永遠充溢著靈感的目光”吸引著奧涅金,他本能地向往這種熱度,是因為他所缺失的正是連斯基對于生命的熱情。在西方思潮的影響下,他的思想已走出了腐朽墮落的上流貴族階級,卻沒有走向下層人民。沒有得到歸屬及支撐的思想處于一種無根的漂泊狀態,在社會邊緣游走。他抑郁、空虛、冷漠,厭煩了大都市的生活,到了鄉下又覺得“同樣地叫人膩味”。
在重遇達吉雅娜之后,奧涅金體會到了愛情,“幻想驚擾了遲來的睡夢——時而纏綿,時而憂郁”,常人各種豐富的情緒回歸到他身上,使他又成了一個“活生生的人”,整個人變得有生氣了。從這個意義上看,他的愛情悲劇對他來說未嘗不是件幸事。他有了渴望,也就有了對生命的熱情。這種熱情可以進一步轉化為意志,將已分離的思想與行動結合起來。他敢于執筆給達吉雅娜寫情書,對她吐露深情,那么聯系到更深的層面,被排除在社會需求之外的他也有可能重新找到角色定位,成為被社會接納的一員。根據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當奧涅金的第三層情感與歸屬的需要被滿足之后,才能進一步達到自我實現的層次。
普希金在達吉雅娜拒絕奧涅金后結束小說,沒有交代他以后的命運。一個普希金的熟人說按照詩人的意思“奧涅金應該犧牲在高加索或十二月黨人武裝起義中”。暫且不論傳說是否屬實,筆者贊成這種說法。之前奧涅金是“死著活”,就像富蘭克林所說的“有的人25歲就死了,但直到75歲才埋葬”。雖然活著,卻是以“死著”的狀態,是被擠在社會邊緣不被任何階層需要的“多余人”。但他找回了敢愛且敢于表達愛的自己,成為一個真實的有血有肉的人,踏踏實實地活在世界上,用熱情取代縹緲的憂郁。這種熱情轉化為意志,投入到實際行動中,再結合他本有的進步思想,便能徹底使他覺醒,超越“多余人”停留的層次。如果最后處理成犧牲了,就正好是對舊的奧涅金模式的顛覆,成了“活著死”,形成更強烈的對比。盡管身體犧牲了,但走出了“多余人”這個角色,不再做“行動上的矮子”,找到自己人生的意義,也為俄羅斯尋找出路。
拉斯科爾尼科夫的回歸則是關于宗教信仰、關于思想狀態的回歸。之前他的房間陰暗低矮,讓人透不過氣。這樣的生活環境必然滋生細菌而使他發熱生病,而西方傳來的拿破侖主義也是一種“病毒”,感染了他的思想狀態,從而產生“殺人”這種癥狀。在彼得堡,妓女、酒鬼、高利貸者擠在一堆,雜亂交織的線條呈現出陰郁與暗沉的色調;擁擠的街道、悶熱的天氣、骯臟發臭的干草廣場與他的心境相互映襯,營造出沉悶繁雜令人窒息的氛圍。人們懷疑一切:權力、命運、信仰……形而上學的價值體系失效,人們失去了追求的意義。這是一個“上帝死了”的地方,彼岸消失了,空留此岸虛無的痛苦。
被流放至西伯利亞之后,寒冷的空氣仿佛給他進行了一次洗禮,他獲得了新生,得到了救贖。他的心靈被愛情滌凈了,陰郁沉重的顏色褪去,逐漸變得澄凈,等著染上屬于初春的希望的色彩。到這個場景,真正的“罰”已經結束了。盡管身體還要繼續服苦役,但“他獲得了再生,他也知道這點,作為一個再生的人充分地體會到這點 ”。
西伯利亞十分荒涼、人跡罕至,身體無法逃離,心靈卻是自由的。他從精神的荒原回到了有信仰的福地,“在那兒時間仿佛停滯不前,仿佛亞伯拉罕的時代和他的畜群還沒有過去”,在那兒仍然有虔誠和對生命的敬畏。這個開放的空間寓示著拉氏心境的開闊,愛情向其開放,宗教信仰向其開放,整個世界又重新向其開放。開放是為了生成,生成一個全新的凈化過的拉斯柯爾尼科夫。最終拉氏與索尼婭相愛之后,突然想到“難道現在她的信仰現在不能成為我的信仰嗎?”,他回到了東正教信仰,回歸到了俄國本土文化。
或顯或隱的回歸展現了主人公空間和精神上的轉變,也蘊含著更多的文化隱喻。《葉甫蓋尼·奧涅金》以奧涅金這一個體作為整個階級的代表,反映了當時存在的“多余人”問題。在奧涅金生活的時代,西歐先進社會思潮讓當時部分貴族青年意識到農奴制度和封建專制制度的腐朽。他們不滿于社會的黑暗, 在貴族的糜爛生活中感到空虛和厭倦, 思想已離開上層階級,但行動卻仍停留在原地,不起身尋找出路。思想與行動的分離帶來的是焦躁苦悶,使他們患上了“俄羅斯郁悶”。這部分青年在社會中找不到屬于自己的位置,成為“多余人”。而“回歸”社會,就成為他們的真正需要。
《罪與罰》則體現了關于俄羅斯民族文化道路的選擇。19世紀的彼得堡是西方文化匯聚的地方。拉斯柯爾尼科夫、盧任和拉祖米興在只有六步長的低矮房間里爭論的場景是當時俄羅斯文化擁擠狀態的縮影。偉人哲學、虛無主義、社會主義等與本土文化混雜,提供了多種選擇。正如劉亞丁先生所說,《罪與罰》是文化試錯的體現。19世紀的前五十年, 俄羅斯先進的知識分子都致力于向西方學習, 陀氏也是其中一員。他信仰傅立葉學說,并積極傳播法國空想社會主義,主張廢除農奴制,力圖改造俄羅斯文化。而到了19世紀中期,歐洲革命等事件使知識分子看到西歐資本主義文化的弊端,開始轉向俄國自身的文化。陀氏在服苦役的十年中與一本《圣經》相伴,成為東正教的虔誠信徒。他在《當代》雜志中宣告了否定學西方、回歸俄羅斯土壤的文化選擇。《罪與罰》中拉氏的生存地點從西邊的彼得堡到東邊的西伯利亞高原,這種空間運動的行跡也可看作是文化遠離西方的軌跡。
兩位作家在兩本書中以不同的方式呈現出了相似的“回歸”層次,必有緣由。一方面,這是俄國文學大師們共有的文學自覺性所促成的。他們以敏銳的洞察力發現社會發展過程中所存在的問題,并對其進行審視與思考,通過巧妙構思、精心安排來創造出揭示社會問題而又極具文學藝術的偉大作品。《葉甫蓋尼·奧涅金》的“回歸”不僅在內容上反映了當時典型的“多余人”問題,也在形式上成為其奏鳴曲式結構的一部分,呈現部、展開部、再現部的設計展現出“俄國文學之父”普希金的文學功底;《罪與罰》的“回歸”以細膩深刻的心理描寫展現出俄羅斯文化尋找出路的過程,即從學習西方的路上調轉馬頭,回歸本國“土壤”。
另一方面,或許普希金對陀氏的影響也可作為一種解釋。陀氏認為普希金在《葉甫蓋尼·奧涅金》中已經為俄國未來許多長篇小說的出現作了準備。他斷言,普希金所創造的形式、體裁、典型和性格幾乎囊括了后世整個俄羅斯文學的基因。這其中是否包括“回歸”意義我們不得而知。但《奧涅金》對陀氏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這是毋庸置疑的。從文本上來分析,《罪與罰》中的“回歸”也可看作是對《奧涅金》的延伸與深化。觀察角度從個人向人類轉變,回歸也進一步深入。《奧涅金》中的回歸尚有顯性,可直接由主人公的位置變化體現,而《罪與罰》中的回歸就是純粹的隱性,只能感知精神文化之路;奧涅金剛悟到愛情,悟到生命體驗時,敘述就戛然而止,要靠讀者深度挖掘才能想象進一步的發展趨勢,而《罪與罰》則直接點出拉斯柯爾尼科夫悟到東正教信仰,寫到了“悟”的深處。在這個層面上,可以說《葉甫蓋尼·奧涅金》與《罪與罰》是繼承與發展的關系。
“回歸”的多重意義只是以兩書臨近結尾的兩處情節為突破點,聯系文本及時代背景、作家思想等找出的共同點,兩部作品在整體的俄國人文精神、對西方文化的思考等其他方面也有深層聯系,值得進一步研究。盡管學界對《葉甫蓋尼·奧涅金》與《罪與罰》已有無數解讀,但闡釋與分析仍然在繼續,經典作品的內涵仍然無法窮盡,這就是經典的魅力。
參考文獻:
[1]普希金:《葉甫蓋尼·奧涅金》,丁魯譯,上海:譯林出版社,1996年,第15,26,34-35,42,50-51,227-229頁。
[2]陀思妥耶夫斯基:《罪與罰》,岳麟譯,上海:譯林出版社,1979年,第162-174,636-637頁。
[3]納博科夫:《文學講稿》,申慧輝等譯,北京:三聯書店,1991年,第253頁。
[4]劉亞丁:《文化試錯的民族寓言:<罪與罰>的一種解讀》,《外國文學研究》,2008年第5期,第44-4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