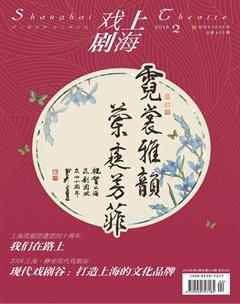姹紫嫣紅觀后
友竹

古典美
上昆的四十年,經過了執著守望與攻堅克難,遇到了機遇挑戰與重視呵護,得來了藝術成果與事業興盛。無論傳統的挖掘整固、原創的嘗試探索,還是人才的培養使用、市場的引導開發和國際的展示交流,上昆都有深厚的積累與良好的業績,從中可清晰地看到中國綜合國力提升、民族文化自信上揚、政府扶持力度增加、大眾鑒賞水平提高的美好軌跡。
外因是重要的,內因是更重要的。這內因不僅來自上昆四十年的熱愛與奉獻、耕耘與收獲,更源于昆曲藝術本體的生命力。正是昆曲的生命力賦予了上昆以生命力而不是相反。換言之,上昆以四十年的高質量劇目及演出,將昆曲的生命力加以維護并發揚光大,從而贏得了劇團的成就和榮譽。
昆曲的生命力,簡言之,古典美。昆曲在高雅深奧、令人感到敬畏的同時,能令人產生一見如故的情感。追根溯源,即古典美。觀眾既可以擁有深奧學問來鑒賞它,也可以毫無知識儲備去欣賞它,只消憑藉與昆曲古典美相通的氣質和氣息,外面則披著觀賞性這件美麗無比的外衣。古典美雖有強弱之分和隱顯之別,但普遍存在于人心。
然而,對于昆曲基于古典美的生命力,也不可作過高的估量。昆曲向被喻為“戲苑之蘭”,其剴切處不僅在其審美特征之典雅嬌柔,而且在其生存條件之高貴苛刻。昆曲誕生以來,不止一次遭遇絕滅之災,表明其極易受到外部環境包括政治、經濟、文化,尤其是思想觀念、審美趣味、社會風尚的負面影響,猶如蘭花,環境條件稍有不適,便不能開花甚至無法存活。似乎只有在經濟豐足、社會安定、人民富裕、文化昌榮的條件下,這枝“戲苑之蘭”才有生長和花繁葉茂的可能。學者王安奎認為:“只有盛世人們才需要昆曲,它那深厚的文化價值才會被當成真正的寶貝。”(王安奎《十年樹昆》,《藝術評論》2011年第6期)從歷史深度和宏觀角度看,這是一個很準確的判斷。若進一步加以分析,作為文化柔軟性與脆弱性的典型品種,昆曲與地方劇種相比有三點細節值得注意——
一是昆曲比地方劇種更易發生滅絕。包含獨特的方言、音樂、服裝、民俗的地域文化對地方劇種既有限制作用,又具保護穩定功能,而昆曲沒有后者優勢。學者劉禎認為:“對于不同的戲曲劇種應予以分級保護,側重保護那些具有重要歷史價值、文化價值、藝術價值的劇種和劇團。”(劉禎《傳統非遺如何活在當下》,《解放日報》2012年10月7日第4版)意將戲曲劇種以全國通行性與局部地域性、歷史悠久與相對年輕、底蘊深厚與相對薄弱的標準,進行分類和定位,進而加以有側重、分級別地保護。從保護對象和保護資源看,這是一個很必要的建議。昆曲作為對中國文學、戲劇、音樂、形體之美加以高端和系統呈現的、歷史悠久的全國性劇種,當是這種分級保護的首要和頂級對象。
二是昆曲比地方劇種更易保持本體。一旦得到有效保護,昆曲從劇目到演藝的悠久、豐贍、典雅甚至深奧,能使其更易得到應有的尊重和原生態的保存,比地方劇種更容易免受以“改革”“創新”“現代化”為名的刀斧,從而避免發生質地上的變異。同時,因為歷史悠久,昆曲在當代獲得生存的可能性反而增加了。一位年輕“昆蟲”(昆曲愛好者)表示:“昆曲那低眉舞帕、躬身拾葉的精致,能讓我的心簡單明凈。”“昆曲的唱腔、配樂、動作反映了古代人的雅致的生活方式,讓我感覺與他們的距離并不遙遠。”(王劍虹《昆曲觀眾青春化態勢日益顯著》,《新民晚報》2011年5月26日)正因昆曲與現實間的距離很大,反成了當代觀眾尤其是青年觀眾喜愛的理由。
三是昆曲比地方劇種的變化更緩慢。傳統的藝文在穩定性中蘊含發展性,這點早已被古人所認知,所謂“世之腔調凡三十年一變”自不待說,所謂“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意為主流體裁隨時代變化而演化,舊體裁的創作盡管已無法企及鼎盛期的高度,但也在因時而變,根據時代、社會和受眾的需求適當地調整和變化。學者劉禎認為,戲曲具有“不變中的變化”(劉禎《傳統非遺如何活在當下》,《解放日報》2012年10月7日第4版)的性質,盡管戲曲的巔峰期早已過去,但依然具備變化的內在要求和外在能力。與地方劇種比,昆曲變化的緩慢度與細微度更甚,尤以音樂唱腔、程式動作最甚。
寂寞期
上昆的四十年,一大半處于傳統文化的寂寞期。上昆艱難地熬過了這段時期,還很好地利用了這段時期。
從本質看,對古典美的維護與發揚光大,基本等同于對古典美與時代性間距離的維護與發揚光大,這一工作注定了須以寂寞為代價。無論環境冷熱與否,于己有利與否,昆曲都須與當代始終保持必要距離,即擁有“骨子里的寂寞”,唯有如此,才是真正的昆曲。現在看來,上昆最有效率的工作和最重要的收獲,絕大多數也就是出現在這一段寂寞期里的。
首先是各類劇目的發掘、整理和創造。傳統大戲方面,《邯鄲記》《紫釵記》《南柯記》先后“復原”,與《牡丹亭》形成了“臨川四夢”演出系列,成為目前海內外商演的“搶手貨”。全本《長生殿》和“復原”《景陽鐘》《琵琶記》同樣從折子戲的基礎上,結合劇本和創編而成,功德有口皆碑;原創大戲方面,《血手記》《貴人魔影》《司馬相如》《班昭》《川上吟》在不同時期顯示了上昆的原創力,獲得了應有的藝術地位和影響,將在當代昆劇史上留下重要的筆畫;折子戲方面,上昆與兄弟劇團同樣搶救、整理、演出了一批瀕臨失傳的文武折子戲劇目;小劇場戲曲方面,《傷逝》《夫的人》《椅子》等作品創意鮮明,態度嚴謹,并不是將昆曲作為現代理念的某種表達工具,而是以昆為主,為昆曲表達現代理念探索了某些可能性。
作為昆曲藝術性的基礎與保障,文學性在接受審美中往往滯后于藝術性,但在創造審美中則常常領先于藝術性。學者薛若琳認為,“昆曲的興與衰都和劇本有關”,“劇本對于昆曲的重要性怎么強調也不過分”(《昆曲的興與衰都和劇本有關》,《文匯報》2015年4月30日第11版)。的確,當代昆曲的復蘇與復興之所以領先于許多地方戲曲劇種,最主要的原因便是其高度的文學性為技藝的呈現提供了基礎與保障,吸引了文化水平普遍提高、文化自信快速反彈的青年觀眾群體。
其二是各類人才得到穩定、延續和發展。經過時間的淘洗和多年的努力,上昆目前的人才結構合理,行當配置穩定,演藝風格延續,事業獲得發展。具體而言,經俞振飛和傳字輩調教的昆大班、昆二班有許多成了名家,至今活躍在創編、導演、演出及教育的一線;昆三班、昆四班正值盛年,人才濟濟,其中不少演員擁有了得大獎、成名家的代表作;昆五班初出茅廬,他們手握高學歷,心藏好愿景,正躍躍欲試地在劇目和行當上全面接班,與師長和學長共同呈現“幾生幾代幾雙人”的良好人才格局。
其三是演出市場得到恢復、充實和拓展。上昆修復了劇團的專屬劇場,拉回了大批老觀眾,鞏固并開辟了市內外劇場,吸引了大量新觀眾。最重要的是劇目建設與舞臺呈現,上昆忠實承繼傳統,卻非一味復古,而是以本體為前提,以今人為標的,對傳統劇目和表現形式做了審慎而又細微的變化,及時聽取專家和觀眾的意見并加以改善,很好地處理了文化傳承與藝術創造的辯證關系。為滿足觀眾不同層次的審美需要,上昆為《牡丹亭》設計了全本、典藏、校園、反串等多個演出版,為全本《長生殿》配置了精華版,小劇場演出則介于傳統性和實驗性之間,吸引了大批青年觀眾走近昆曲,進而接觸并喜愛傳統昆曲。再老的戲也不是演給古人看的,而是演給今人看的。
總之,上昆在寂寞期中堅持了傳統藝術應有的文化自覺,遵循了昆曲本體的發展規律,維護了昆曲的古典美,發揚光大了昆曲的生命力。“最難耐的是寂寞,最難拋的是榮華。從來學問欺富貴,真文章在孤燈下”(羅懷臻《班昭》),需要寂寞的,豈止是學問和文章。應該注意的是,物質皮相的寂寞與精神本質的寂寞固然互相聯系、互為影響,但絕不是同樣的東西。進入新世紀后,昆曲在物質層面的皮相寂寞逐漸消退、基本消除,但在精神層面的本質寂寞依然存在、永遠存在。學者周明認為:“戲曲在本質上屬于古代藝術,其總體審美特征和演出形式并未發生本質的變化,與當代環境格格不入。”(周明《戲曲+網絡的狂歡與尷尬》,《福建藝術》2017年第2期)與地方劇種相比,昆曲在這一點上最為明顯,這恰恰是其在當代生存和發展的原因。因此,昆曲在任何時空下都須維護和發揚光大“骨子里的寂寞”,這對現下演出檔期排滿,粉絲數十萬人,全年票房超過千萬元的上昆而言,倒成了一個呼之欲出的考驗。
百戲至理
若能始終維護和發揚光大昆曲的“骨子里的寂寞”,我們勢必發現當下“昆曲熱”的脆弱與“昆曲學”的逼仄。昆山腔經魏良輔的再創造和梁辰魚的新貢獻后,在“曲”的藝術技巧上達到了高度成熟,在“劇”的文學質地上完成了由俗趨雅,最終成為文人藝術,對創造者和欣賞者均有了很高的文學性要求。觀察當代昆曲觀眾,文化底蘊不夠深,藝術修養不夠高,特別是一些出于從眾心態或沖動心理的年輕人群,對他們之于昆曲的理解力、熱愛度及持續性,不可作過于樂觀的考量與判斷。今后,上昆一方面要更多地重視“劇目的文化釋出”與“舞臺的技藝呈現”相匹配,同時推行演出形式的“分眾營銷”,適度嘗試運用現代媒介吸引觀眾,另一方面要有意地拉開形式創新與傳統演出的距離,以避免萬一形式創新失敗所導致的對觀眾的誤導和對本體的損害。
“昆曲學”的逼仄,一直存在,至今存在。從現當代始,昆曲有了“百戲之祖”之名實,但限于劇目和表演技藝層面,理論研究層面并不包括其中。這并不是昆曲的理論研究不深、學術成果不豐,而是過“深”過“獨”,未從特殊性研究走向普遍性觀照,達到“百戲至理”的高度與廣度。回顧古代戲曲理論,雅部甚豐,花部幾無,南戲之后基本都以昆曲為研究對象。當然,許多研究成果是從文人興味出發的,具有自然的普遍意味,但可惜隱而不顯,又無人挖掘。現當代的昆曲史學、劇學、曲學理論和評論,與昆曲藝術實踐之間脫節較大,存在“宏觀易見、微觀難顯”的關系,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予以打通。學者劉厚生認為,無論戲曲處于什么狀態,“忽視理論研究都是最危險的事”(劉厚生《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戲曲怎么辦》,《中國藝術報》2013年4月15日),對昆曲而言,理論研究若不能向創造和接受審美釋出和轉化,也是一件危險的事。
當代昆曲成為“百戲至理”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似有愈來愈強之勢——不僅在劇藝理論和教育體系之中,更在當代戲曲整體演變的趨勢之中。當所有戲曲劇種的“非遺”身份已經確立并快速走向了城市化,其創造和接受審美的雅化勢成必然。于是,昆曲由俗向雅的歷史經驗及其進入當代的理論新成果,至少可以成為其他戲曲劇種的參考或對照。其間,上昆尤應將四十年來在劇目、人才、市場等方面的實踐,自覺、主動地進入評論和理論研究的視野,與磨練技藝、整理老戲、創排新作予以同等的重視和投入。這也是上昆為當代昆曲擁有和發揚光大“骨子里的寂寞”的一個重要內容。
上昆可以營造評論氛圍、培養學者興趣、提供研究興趣的相關意識,并力所能及地付諸行動。一方面,應像尊重老藝術家一樣地尊重老學者,使他們的思想和觀點能以深入淺出的方式傳達給昆曲演員和觀眾;另一方面,應像關愛年輕演員那樣關愛年輕學者,特別為年輕的文科學子提供審美機會和研究材料,吸引他們自覺地生發對當代昆曲的審美興趣乃至研究興趣。值得一提的是,在當代培養昆曲觀眾的工作固然很必要、很重要,但觀眾是有限的。古典美的生命力和“骨子里的寂寞”,注定了昆曲的文人化和小眾化。無限制、無標的地培養缺乏古典美或不愿文人化的昆曲觀眾,其效果可能適得其反。而在具有較強的古典美氣息、較深的文人化色彩的觀眾中吸引潛在的昆曲學者,是更必要、更重要的,有一個規律不可不知——具有深刻思想、獨到見解和廣泛影響的戲曲學者,往往出現在戲曲的絕對鼎盛期或相對繁榮期,而他們也是戲曲最好的觀眾。今后,上昆可先以豐富的劇目和精湛的演出,再以昆曲歷史文化的展示和推送,導引年輕的文科學子自發從事當代昆曲的實踐性研究,尤其對諸如古今昆曲人文屬性的養成與演變、乾嘉傳統與當代人文精神的關系、昆曲演藝流派產生的可能性及利弊得失、昆曲實驗劇場的目的及方向等課題,可開些沙龍,做些討論,寫些文章,一邊拉近昆曲理論研究與當代創造和接受審美的關系,一邊用自身的藝術實踐成果及經驗,避免年輕學者有可能出現的誤解和誤判,一邊使自己在當代昆曲盛世中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可謂一舉數得。最重要的,是將昆曲的技術藝術傳播,通過學者之手向文化精神傳播實現轉化。
斷壁殘垣已是歷史。姹紫嫣紅觀后,徑是上昆和當代昆曲的新景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