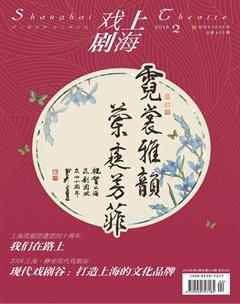讓傳統音樂文化在創新中重現活力
李學峰

一出淮劇《忠烈門》的演出,重又開啟了海派淮劇在滬上新一輪的“淮劇熱”,給眾多淮劇癡迷者品足了濃濃的“淮腔土味”,再現了淮劇久違了的鄉音。同時,也讓一個涉足作曲領地不深的我,在該劇音樂唱腔設計中嘗盡了甜頭,體味到淮劇傳統音樂深厚的魅力,并從中悟出戲曲音樂的創作必須順應時代的發展而作揚棄傳承、創新發展的本質意義。
淮劇,本是源于兩淮地帶原生的且具有鮮明個性色彩的地方戲曲劇種。它的質樸、粗獷構成了它全部音樂的基調。然而,近百年來,淮劇躋身上海都市文化生態環境中,漸趨自然形成了一種帶有海派意味的文化觀念和藝術創新的思想體系。正因如此,如何捏準《忠烈門》的音樂定位,使其既堅守淮劇劇種音樂的本體和個性化風格,又在“都市淮劇三部曲 ”(《金龍與蜉蝣》《西楚霸王》《千古韓非》)音樂創作成功經驗基礎上,求得更加開放的格局和創新的風貌,便成了我首要面對的思考。
長期的藝術實踐,使我愈加意會到好的音樂聲腔,展示的是藝術美質,表述的是內在情感,傳遞的是精神力量。順著這個理念,我把自己對淮劇音樂未來走向的所思所想,全部轉化在《忠烈門》的音樂創作之中,試從兩個方面予以呈現。
一、定好基調,選取最典型的音樂語言,彰顯劇種的獨特風韻。在以【自由調】為主構建的音樂框架下,力求突破傳統唱腔旋法的單一,對淮劇聲腔中多個主調性曲牌布局模式作出創新性的融合和拓展,使整出劇目的音樂色調具有當代意味的轉換。如在《噩耗》一折戲中,面對金沙灘一場惡戰后的慘景,我為佘太君最先設計了一段可撼動人們心靈的【大悲調】。極度寬廣與舒展的緩板大腔,在一組華彩炫技的長過門引奏下,進入如歌如泣地深情傾訴。慢詠中,那無盡憂傷的旋律線條,恰切地抒發了佘太君此時失兒又失夫的凄美悲情,其情味之深,足以讓觀眾獲得巨大的審美快感。繼之,在《掛帥》一折戲里,我為佘太君的唱段重又換上了一曲深沉的【拉調】曲牌,連同隨后將要轉接的【馬派自由調】,同以慢板、平板、快板等不同板式的多重疊加,喚起一股高昂激揚的音樂氣勢,映襯起佘太君相守十八年翹盼孫兒凱旋的女性柔情,以及誓為大宋甘灑熱血的浩然正氣。再有,當全劇發展到最為頂點的《夜襲》一折戲時,我選擇將【淮調】與【馬派自由調】兩者不同色調且又同具爆發力的曲牌置于一折,任其交織、互融與傳承;尤其是在創腔過程中,發展起那帶有傳統起板程式的散起高唱與“清板”吟唱,那連續遞進四句不同腔型的渾然連唱、那抒情和激越相交融的旋線鋪陳,最大限度地加劇了音樂情感的沖擊力和能量,從而增強了觀眾對《忠烈門》劇音樂的感知和認同。而曲中對于傳統“起板鑼鼓”和“三番譜點”程式的化用,尤顯音韻生動,接近燃點。
《忠烈門》的創演,其反響超出了我們的預想。從觀眾的贊許聲中,自感我對《忠烈門》音樂的建構,既有對文化傳統的繼承,亦有對現時代音樂語言新的審美探索。這種求美求新的探索,即使是很小步伐的跨越,但在一定程度上卻表明了延續民族音樂文化血脈、重視對劇種傳統音樂精華的汲取和傳承,依然是戲曲音樂創作所必須遵循的一大原則。
二、強化演唱,竭力從演唱品質的高度,匯同演員用最精粹的旋律、最華美的聲音來解讀劇情、解讀人物。
提及演唱,人們對淮劇演員的期待,不只是以聲悅人,而更多地在企求以情潤腔,潤而生味。說得再直接些,這“味”,則是淮劇演唱中的一條潛在的生命線。《忠烈門》中佘太君的扮演者景蘭英,是淮劇“徐派”(徐桂芳)的傳承人。她噪音寬厚,音色純正,善以充滿激情、以唱見長的表演形成自己的風格。借助表演者扎實的演唱功力,我曾有意識地將淮劇“徐派”在演唱上所慣用的吐字、運腔、氣口,乃至多有音程大跳和上下滑音與回滑音的呈現方式,注進佘太君人物的腔體之中。這樣,使原本充滿抒情氣質的流派聲腔,通過演員人聲音色多彩性的變化與表達,變得更有張力,顯出景蘭英所塑造的佘太君人物音樂形象越發清新流暢,剛勁豪邁、韻味十足。再則,景蘭英以良好的心理狀態投入演唱的二度創造,一改以往過于著重唱腔華麗的輕柔唱法,唱出了【大悲調】的幽咽婉轉,唱出了【拉調】的纏綿深沉,唱出了【淮調】的雄渾粗獷,唱出了【馬派自由調】的剛勁豪放,進而以多種元素的調和,完現了傳統“徐派”演唱韻味的蒼勁樸實,挺拔激越,給《忠烈門》的音樂聲腔增添了一抹亮麗的色彩,也給上海淮劇舞臺塑造了一個錚錚傲骨的佘太君的人物形象。
扮演楊老令公的演員張闖的演唱,聲聲入耳,句句動情,那保有聲腔原色的真聲詠唱,那兼有花臉和老生的潤腔技巧,將一曲起伏跌宕“追風戰騎”的【悲調】,唱得入骨三分,通體透涼,可謂唱者聲淚俱下,聞者潸然落淚。人物那借情抒懷的報國之心,在演員的演唱中盡顯無遺。而扮演楊四郎的演員趙國輝,在原本已拓展了的【自由調】旋線上,糅合了【悲調】的音樂元素,融合了梁氏(梁偉平)演唱風格的行腔走勢,更把人物追溯十八載前前后后懺悔之情推至極點,從而使本具豐富表現力的淮劇主體曲牌被演唱得更為細膩傳神,更富有層次和感染力。
總之,回望《忠烈門》音樂創作的前前后后,給了我太多太多的教益,仿佛把我重又推回到步入音樂之門的原點,找到了我夢寐追尋淮劇的真正方向。面對這一活態傳承下的當代藝術樣態,我明白了上海淮劇團重排經典意義之所在。我愿以此為起點,踏實工作,不斷求索,為有效地推動海派淮劇沿著多元的路徑發展,繼續獻上一個音樂人的綿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