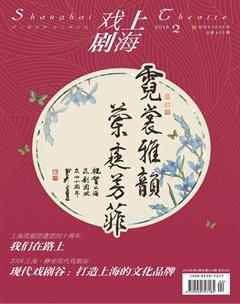蔡伯喈的兩難
徐雯怡


上海昆劇團又新排《琵琶記》,小生黎安主演蔡伯喈一角。很早就聽說了他對這個角色非常感興趣,誠然,黎安是個做事情十分認真的演員,即便如此,他對蔡伯喈的執念也確實讓人頗為費解,更何況蔡伯喈還是一塊不太好啃的硬骨頭。
在我看來,“蔡伯喈”的難度有三。其一在于人物塑造,蔡伯喈是有名的“渣男”。在新戲創作中,建立觀眾的新意識容易,扭轉觀眾的固有意識卻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其二在于劇本,在很長時間的舞臺演繹中,趙五娘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在新作與舊作的視角轉換之間,難免容易有喧賓奪主的危險。其三在于傳承,《琵琶記》在原作中雖是雙線交叉結構,但在昆劇舞臺上堪堪只剩下趙五娘線下的《吃糠》《描容·別墳》《掃松》等幾出,而蔡伯喈的支線則幾乎只能流傳于曲詞曲調之中。這樣的現狀,在給“重塑蔡伯喈”帶來意義和價值的同時也帶來了相應的傳承難度。
從想唱到想演
黎安說,年數越久,想演蔡伯喈的欲望就越強烈;唱過的曲子越多,對《琵琶記》中的唱段就越想念。《琵琶記》的《辭朝》《琴訴荷池》中都有很多好聽的唱段,放任其在一旁荒蕪,黎安心中不忍。
于是,他將此意愿傳達給了團領導,本來只是想著讓他們同意排一個小劇場的昆劇,就演《南浦》《辭朝》《賞荷》《盤夫》這四折,卻沒想到這一提議引起了領導的重視。在他們的支持下,小戲變成了大戲,一個人的心愿變成了一個團的心愿。為了此戲能夠更好地呈現在舞臺上,時任上海市戲曲中心的總裁張鳴和上海昆劇團的團長谷好好親自前往泉州,邀請了著名劇作家王仁杰動筆改編,而導演的人選由于排練時間的沖突一拖再拖,最后由黎安提議邀請了從英國皇家戲劇學院學成歸來的王歡兼任本劇的導演和舞美。王歡的加入,給這個團隊注入了新的活力。
雖然排戲的初衷是源于對唱腔的癡迷,但在對《琵琶記》心心念念的日子里,黎安找到了自己在這部戲里真正想表達的東西——不是對宋元南戲《趙貞女蔡二郎》中“棄親背婦,最終被暴雷劈死”的負心漢的譴責,也不是對元代高明筆下所謂“全忠全孝”的道德楷模的旌揚,而是對忠孝兩難的思考和兩代關系中情與理的矛盾。
第一折《南浦》里就顯示出了這樣的矛盾。這矛盾一方面來自父母的責任與私愿——既擔心孩子離家又不想耽誤孩子的前程;另一方面則來自兒子蔡伯喈的責任與私愿——既難舍父母嬌妻,但對功名仍舊存在向往。兩相僵持之下父母總是先做出妥協,逼兒子收拾行囊上京趕考,兒子半推半就地離開家,剩下的日子里父母就只能自己守著自己,守著空切切的盼望,伴著空虛的日子殷殷望著兒子榮歸故里光耀門楣。離家的兒子心中也未必不想著父母,只是一旦出了家門就有太多的身不由己。
子欲養而親不待,一個“孝”字難煞了兩代人。兩代間的愛都是矛盾的,已漸入中年的黎安更能感受到其中的五味雜陳。在他看來《琵琶記》里講的故事并沒有老去,它在現代社會反而顯得更加普遍。黎安說:“《琵琶記》中蔡伯喈這個人內心對忠孝兩難的矛盾和我這個年紀所看到的社會現象很像。在現代社會中,父母望子成龍,總想著把孩子送出國、出人頭地,但其實父母的內心是十分矛盾的。比方我父母都在上海,但我們也不一定一周能見一次,更何況那些孩子在國外的留守家長呢?父母想見孩子,卻又害怕打擾孩子;孩子也不是不想見父母,只是工作、自己的家庭方方面面都需要顧及,沒有那么多時間分給父母。現代社會已經進入老齡社會了,我看到有太多的老人身邊都沒有子女,我覺得這就是這個戲對當下的價值,它可以引起我們對孝道的思考。”
編劇王仁杰的筆
落在了對蔡伯喈兩難的描摹上
在我看來,忠孝兩難的背后是一個因為懦弱而在痛苦中掙扎的蔡伯喈。如果他是王十朋,他便也早早選擇了辭官回鄉;如果他是王魁,他也就早早選擇了錦繡前程;偏偏他是蔡伯喈,一個不徹底的利己主義者,一個不全然的忘恩負義人,他的猶豫讓他在道德和私欲的天平間搖擺,他享受不到任何的快樂。
這一版《琵琶記》是一個有趣的劇本,它雙線交叉的結構帶來了完全不同的兩種人生狀態,不僅是“糠與米”的不同,還是悲情與悲劇的不同。判斷悲情與悲劇,取決于人物是否對命運擁有選擇權。不論是陳留的饑荒還是公婆的去世趙五娘都沒有選擇的權利,在命運的推搡下,她只能在困境中堅持自己的原則前行。但蔡伯喈不同,他一開始就可以選擇留在家中,他一開始就可以選擇辭官回家,他一開始就可以選擇向牛小姐說出實情……人生的選擇權都放在他的手心,可他或是虛弱抵抗后服軟或是因為懼怕索性放棄了選擇。這些因為懦弱而在欲望和道德之間的搖擺趙五娘卻沒有,她只需要完成丈夫囑托并找到丈夫這一個目標,想著目標前行就好了。趙五娘有人情,但蔡伯喈有人性。
編劇王仁杰看到了蔡伯喈身上的現代性,于是他的筆落在了對蔡伯喈兩難的描摹上。原著中有《強就鸞凰》一出,主要描寫了蔡伯喈特殊的不快樂。宮花帽簇、鼓樂齊鳴,很是一番熱鬧景象,但蔡伯喈卻一下哭一下笑。他“喜書中今日,有女如玉”的快樂還沒到一刻,就因想到“高堂孤獨”立馬又憂愁了起來,前刻發自內心的快樂瞬間在此刻變成了令他愧疚的罪惡之源。
在王仁杰的改編中,這種不快樂被貫穿在一整部戲里。為了讓蔡伯喈成為主角,王仁杰讓趙五娘的生活以夢的形式出現在蔡伯喈的世界里。蔡伯喈和牛小姐成親時,趙五娘在吃糠;蔡伯喈與牛小姐賞荷時,趙五娘在用羅裙包土筑墳,安葬雙親。在蔡伯喈進京的日子里,家鄉的一切像影子一樣跟著他,這是蔡伯喈內心深處對自己的道德譴責。他心里想自己遲早要回去,卻還沒想清楚遲早這個詞是多遲亦或是多早,他雖說也是在京城里成家立業了,卻還是異鄉人那樣格格不入,于是在與牛小姐情投意合的日子里,他短暫的快樂每每都伴隨著無法逃離的苦痛。他只知道選擇傷人,孰不知不選擇傷人更深。最后,趙五娘包土筑墳的夢逼得他講出了一直以來想講的話,可是蔡伯喈眼中天大的事,在牛小姐看來只不過是一頓撒嬌罷了。于是,失去了父母的生命,蔡伯喈從此活在比之前更大的道德陰影中了。其實蔡伯喈撕掉了主角光環,也不過是一個可悲的普通人。
要到水里去踩一踩
“這個戲怎么還在排?”從2017年下半年上昆巡演回來后開始排練《辭朝》算起,《琵琶記》劇組進排練場的時間耗費了一年多,而這句話是主創們在創排《琵琶記》的過程中聽到最多的。的確,這樣大的時間成本投入對現在排戲而言很少見。
《琵琶記》并非是一部對原作的顛覆之作,整部作品以蔡伯喈作為主要視角來闡發《琵琶記》的劇情,并穿插趙五娘幾段經典折子,因此,老戲的身段不用全然廢除,仍可以有許多借鑒保留之處。然而易也于此、難也于此,一年多時間內,他們把大量的時間都放在了研究對舞臺上老調度的取與舍上。《孝順歌》句句都是精華,但演出時間上不允許完全呈現,要怎么刪減?《賞荷》與《中秋望月》都好,要如何取舍?《行路》中身段頗多,要怎樣刪繁入簡?這些都是擺在演員和導演面前的問題,在新劇本的基礎上,他們的新表達也顯得困難重重。在戲曲創作中,最難的永遠不是以舊換新,而是修舊如舊。
黎安說:“在排《蔡伯喈》的過程中,我們能感受到每一個老的調度都有它存在的價值和理由。我們對傳統不能只是盲目地遵從,最起碼要做到思考后繼承,說得形象些,我們只有自己到水里去踩一踩,才能知道水有多深,才能知道接下來要怎么走。” 從2017年底的第一場排練開始,排練場的劇本就都寫滿了演員們自己的解讀,無論是導演還是演員都在盡自己的能力參與到排練的過程中來。黎安認為,這一年多的時間與其說是在創作,不如說是在學習。前人留下來的是多珍貴的東西,只有輪到自己設計創造了,體會才愈發深刻起來。盡管如此,他們仍然在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