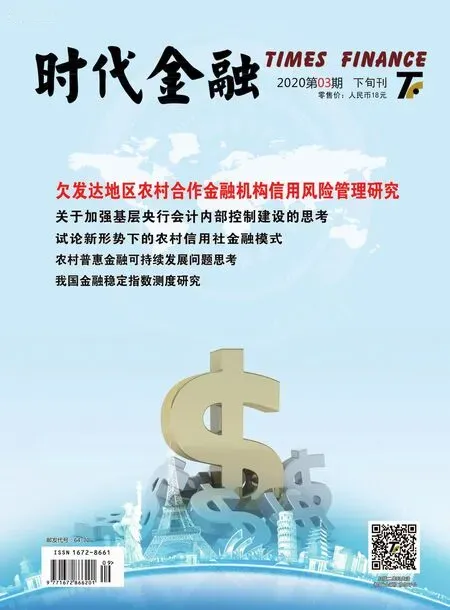中國省級區域金融集聚程度評價


【摘要】本文通過選取16個有代表性的金融指標,構建了區域金融集聚水平的評價體系,并采用因子分析法計算出十二五時期31個省(市、區)的金融集聚水平綜合得分及排名,進而對我國省級區域的金融集聚程度做出評價。研究表明我國各省金融集聚水平比較穩定,金融集聚程度空間差異較大,呈現東高西低的梯度分布特點。
【關鍵詞】金融集聚 因子分析法
一、引言
2015年“一帶一路”戰略進入全面實施階段,這為各省(市、區)金融業的發展帶來了重大機遇,同時也對各省(市、區)金融業服務提出了更加多樣化的需求。由于我國各省域間金融供給層面有著較大差異,存在著明顯的金融產業集聚現象,而且金融集聚對地區經濟的發展[1]、東部中部地區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2]以及新型城鎮化的發展[3]都有著明顯的支持促進作用,因此有必要對我國省級區域的金融集聚程度重新做出評價。
二、文獻綜述
金融集聚的定義目前沒有達成共識,簡言之就是金融產業、金融資源與地域條件協調綜合的時空動態過程以及所產生金融密集程度高于周邊平均水平的匯聚結果[4]。對于金融集聚程度的衡量方法,主要分為尋找代理變量和構建指標體系兩大類。例如:任英華等(2010)[5]選擇區位熵系數代表區域金融集聚程度,進而分析了金融集聚的影響因素及空間溢出效應。李靜等(2014)則構建了包含保險市場、信貸市場、信托市場、證券市場四個層次的指標體系。鄧薇等(2015)[7]構建了包含金融規模、金融機構、金融人才三個一級指標的評價指標體系,并采用縱橫向拉開檔次法我國各省2005~2010年的金融集聚程度做出了評價。馮林等(2016)[8]建立了包含金融資源、金融機構、金融產值三個層次的指標評價體系,并使用熵值法對山東90個縣的金融集聚水平做出了評價。
三、構建評價指標體系
指標的選取直接關系到評價結果的準確性,因此本文本著審慎、全面、可量化原則,借鑒現有研究中的相關金融指標,選取了金融增加值、銀行業存款余額、銀行業貸款余額等8個代表金融規模的指標,之后又添加了代表金融業資本投入規模的固定資產投資額指標。同時,考慮到金融密度本身就是對金融集聚程度的度量,因此添加了單位面積金融機構營業網點機構數、單位面積證券公司營業部數、單位面積年末上市公司數、保險密度、保險深度等5個密度指標,作為規模指標的補充。最終得到表2-1所列的金融集聚程度指標評價體系。該指標體系分成金融業總體規模、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4個準則層和16個指標層。
四、實證分析及評價
本文使用SPASS22統計軟件對2011~2015年31個省(市、區)的面板數據逐年進行因子分析,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金融年鑒》、wind數據庫及《中國區域金融運行報告》。以2015年為例,首先對原始數據做適應性檢驗,KMO的值為0.808,Bartlett球形檢驗的卡方值為976.359,伴隨概率為0,說明原始數據存在公共因子,適合做因子分析。之后提取公因子,不斷調試后決定提取3個公因子,其累計方差貢獻率達到88.894%,提取了原始數據的大部分信息,并對初始因子進行正交旋轉,得到表3-1的因子載荷矩陣。
由表3-1知,第一公因子在金融業增加值、金融業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銀行業金融機構各項存款余額、銀行業金融機構各項貸款余額、金融機構營業網點資產總額、保險收入、保險賠付等指標上載荷較高,于是可以把F1命名為金融規模因子,第二公因子在單位面積金融機構營業網點機構數、單位面積證券公司營業部數、單位面積年末上市公司數等指標上載荷較高,于是可以把F2命名為金融密度因子,第三公因子在當年國內(A股)籌資額、當年國內債券籌資額、保險密度、保險深度等指標上載荷較高,于是可以把F3命名為證券業與保險業發展因子。之后,求出因子得分函數如下:
其中X1*,X2*,…,X3*是原變量標準化后的數據。
利用公因子及其方差貢獻率占比可以計算綜合得分,分別計算出2010~2015年各省(市、區)的金融集聚水平綜合得分及排名,如表3-2。
從時間維度來看,我國各省金融集聚排名比較穩定,最大序差僅為4,說明我國各省(市、區)金融集聚水平都比較穩定。其中北京、河北、遼寧、江蘇、浙江、山東、河南、海南、四川、西藏、青海、寧夏排名五年內保持不變。吉林、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廣東、貴州、陜西、甘肅排名小幅上升。天津、山西、內蒙古、上海、重慶、云南、新疆排名出現小幅下降。
從空間分布來看,如圖3-1,我國金融集聚呈現東高西低的梯度分布與集群分布特點,各個地區存在較大差異。東部沿海地區金融集聚程度最高,其中北京、上海、廣東、浙江、山東在十二五期間均居前6位。具體來看,東部沿海地區金融集聚水平最高的三個區域為環渤海經濟圈、長三角經濟圈、珠三角經濟圈。環渤海經濟圈路網密集、礦產資源與海洋資源豐富、科研院所及科技人員數量眾多,為金融集聚提夠了充足的人力資本、技術資本與物質資本。長三角經濟圈區域第三產業占比較大、經濟發展水平最高,由此產生對金融服務的巨大需求,進而引起金融資源的高度集聚。珠三角經濟圈信息通訊設施完善,實際利用外資水平很高,有利于金融資源的空間聚集與流動。成渝地區與中部6省金融集聚水平僅次于東部沿海。成渝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良好、人力資源豐富,中部地區湖北與河南兩省地區生產總值較高、交通便利,因此獲得相對較高的金融集聚水平。相比之下,西北地區、東北地區與青藏地區的金融集聚水平則相對較低。
五、結論與建議
我國各省金融發展水平比較穩定,金融集聚程度空間差異較大,馬太效應明顯,呈現東高西低的梯度分布特點,環渤海經濟圈、長三角經濟圈、珠三角經濟圈、武漢經濟圈、鄭州經濟圈、成渝地區金融集聚程度相對較高,呈現集群分布特點。通過本文對金融集聚的評價分析之后,提出如下建議。
(一)充分發揮金融集聚的空間溢出效應
金融集聚對省域經濟的增長有著顯著地空間溢出效應[9],應努力加強省級區域間金融交流與合作。例如從空間分布來看,北部沿海地區、東部沿海地區、南部沿海區金融集聚程度都非常高,可以向西帶動黃河中游地區、長江中游地區金融業的發展,進而促進中部地區能源、水稻、奶業、汽車生產等基地的建設。大西南地區,四川、重慶金融基礎最好,可以嘗試建成兩個西部金融中心,輻射云南、貴州、廣西、西藏等省金融業。
(二)重視保險業發展
在金融規模因子F1上,保險收入指標X13與保險賠付指標X14有著很高的載荷,在證券業與保險業發展因子F3上,保險密度指標X15與保險深度指標X16同樣有個較大載荷,說明保險業的發展規模對金融規模因子及保險業發展因子都有著很大的影響,同時金融規模因子、保險業發展因子又與金融集聚程度指標密切相關,因此努力激活保險業的發展潛力,可以提高金融集聚水平,進而促進省域經濟的發展。
(三)合理布局金融網點
金融密度因子F2對金融集聚程度指標有著25.398%的貢獻度,作用也不應忽視。目前東部地區網點過于密集,而中西部地區則相對較少。如果能夠合理依托金融資源布局金融網點,不僅可以降低金融企業成本,還可以提升金融集聚水平。因此,各金融企業應該充分收集各地城市規劃、人口流動等信息,做到統一規劃、科學選址。
參考文獻
[1]李標,宋長旭,吳賈.創新驅動下金融集聚與區域經濟增長[J].財經科學,2016,(01):88-99.
[2]于斌斌.金融集聚促進了產業結構升級嗎:空間溢出的視角——基于中國城市動態空間面板模型的分析[J].國際金融研究,2017,(02): 12-23.
[3]王周偉,柳閆.金融集聚對新型城鎮化支持作用的空間網絡分解[J].上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02):45-55.
[4]劉軍,黃解宇,曹利軍.金融集聚影響實體經濟機制研究[J].管理世界,2007,(04):152-153.
[5]任英華,徐玲,游萬海.金融集聚影響因素空間計量模型及其應用[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0,(05):104-115.
[6]李靜,白江.我國地區金融集聚水平的測度[J].求是學刊,2014,(04):52-58.
[7]鄧薇,呂勇斌,趙瓊.區域金融集聚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與實證分析[J].統計與決策,2015,(19):153-155.
[8]馮林,劉華軍,宋建林.基于熵權TOPSIS法的縣域金融集聚評價研究——以山東省為例[J].山東財經大學學報,2016,(02):1-9.
[9]孫志紅,王亞青.金融集聚對區域經濟增長的空間溢出效應研究——基于西北五省數據[J].審計與經濟研究,2017,(02):108-118.
作者簡介:王斐(1989-),男,漢族,山東濰坊人,中國海洋大學經濟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國際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