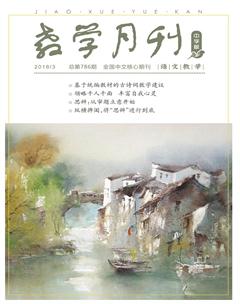《斑紋》教學(xué)札記
有人說,像周曉楓《斑紋》這樣的美文,教師不教倒好,一教反而會壞了學(xué)生的胃口。一些閱讀鑒賞能力高的學(xué)生,也許在自讀中確實(shí)能有“悠然心會,收獲多多”的感覺,但大部分學(xué)生還是屬于“燈不點(diǎn)不亮,話不說不明”的吧。語文課堂上,教師的“點(diǎn)燈”之責(zé)不能荒廢。
筆者一貫信奉“識其人”“親其人”能更好地引發(fā)學(xué)生“讀其文”的興趣。所以筆者總是喜歡讓學(xué)生先認(rèn)識課文作者的模樣,再來介紹課文作者的生平及其創(chuàng)作情況。
上《斑紋》,筆者先用多媒體課件展示了周曉楓的系列照片。
“啊,是女的!”學(xué)生感嘆。
學(xué)生竟不知道周曉楓是女性,看來用照片展示一番還是很有必要的。從學(xué)生的反應(yīng)中可以看出,學(xué)生并沒有苛求作家一定得是美女、帥哥。筆者說了句:“《斑紋》的作者周曉楓也許貌不過中人之姿,算不上大美女,但絕對是位大才女。不靠臉蛋、身材吃飯,靠才學(xué)吃飯的人,才是有大本事的人。美貌是天生的,才學(xué)是后天努力取得的,讓咱們多關(guān)注后天的努力。”蘇步青說:“老夫愛作婆心語。”當(dāng)語文教師的,除了做“經(jīng)師”,不能忘了還得做“人師”。
學(xué)生對周曉楓比較陌生,作者介紹不能省:
周曉楓,1969年6月生于北京。1992年畢業(yè)于山東大學(xué)中文系,在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做過8年兒童文學(xué)編輯,2000年調(diào)入北京出版社,從事雜志編輯工作。一直從事散文寫作,代表作品有《它們》《鳥群》《圣誕節(jié)的零點(diǎn)》《斑紋》《馬戲與雜技》《幼兒園》《黑童話》《你的身體是個(gè)仙境》等。出版了個(gè)人散文集《上帝的隱語》《鳥群》《收藏——時(shí)光的魔法書》和《斑紋——獸皮上的地圖》。曾獲馮牧文學(xué)獎(jiǎng)、冰心散文獎(jiǎng)、十月文學(xué)獎(jiǎng)、人民文學(xué)獎(jiǎng)等獎(jiǎng)項(xiàng)。周曉楓是張藝謀團(tuán)隊(duì)的文學(xué)策劃,擔(dān)任了電影《三槍拍案驚奇》《山楂樹之戀》《金陵十三釵》《歸來》等的文學(xué)策劃。
當(dāng)亮出以上內(nèi)容時(shí),學(xué)生最感興趣的是最后那塊,周曉楓竟然還是張大導(dǎo)演的文學(xué)策劃!他們對周曉楓的喜愛指數(shù)大增。
課前學(xué)生已作了充分的預(yù)習(xí)。《斑紋》妙詞繁富,值得記憶積累的詞語很多。讀完一篇文章,多識幾個(gè)字,是很重要的一環(huán)。記得阿城的《孩子王》小說中,在那個(gè)連教科書都發(fā)不起的年代,那位叫“老桿兒”的老師,就讓學(xué)生讀字典,抄字典,教學(xué)效果也不賴。字詞是構(gòu)建語言大廈的磚瓦,詞語的積累,在高中階段依然不能輕忽。高考的前三道題目,考的不就是詞語的識記和運(yùn)用嗎?拿下前三題,高考就有戲。既然高考繞不過去,平時(shí)教學(xué)有點(diǎn)高考意識自屬應(yīng)當(dāng)。
《斑紋》中的下列詞語,很值得認(rèn)一認(rèn),讀一讀,記一記。
逶迤 斑斕 螺旋 輪廓 匍匐 伺機(jī) 慵懶
銜接 蝰蛇 蟒皮 嗜好 蓑鲉 鰭葉 鷹隼
暈眩 青睞 鐫刻 綴滿 婆娑 凝眸 柵欄
裸露 精湛 偏袒 強(qiáng)悍 醞釀 螫針 蠱惑
皰疹 頹敗 妊娠 犁鏵
辨音正字記誦后,鑒賞該從哪兒入手呢?
有一次,在上《南州六月荔枝丹》和《景泰藍(lán)的制作》時(shí),“說明順序”“說明方法”“說明語言”已講得很多很細(xì),筆者不想在《斑紋》中再面面俱到地講這些東西。但《斑紋》的內(nèi)容實(shí)在太過豐饒,學(xué)生很容易走進(jìn)迷宮,只見富麗魅惑,卻找不到出路。把此文的構(gòu)思特點(diǎn)、寫作思路理一理很有必要,所以“說明順序”還是要說上一說。《斑紋》的最大特色是在語言,這塊要引導(dǎo)學(xué)生好好領(lǐng)略。
葉開在《這才是中國最好的語文書》一書的自序《怎樣開始愉快的閱讀》中說:“在閱讀中感受優(yōu)秀作品的特殊趣味,是學(xué)習(xí)的重要組成部分。但中小學(xué)教育更多地做著‘尋章摘句老雕蟲的工作——摘抄好詞好句,歸納中心思想,總結(jié)段落大意。在測驗(yàn)和考試中,則用標(biāo)準(zhǔn)答案來限制學(xué)生的想象力,抹殺他們的閱讀興趣。在青少年階段,有吸引力的閱讀非常重要。”千篇一律,每文必分段,每段必歸納,這確實(shí)枯燥乏味,容易倒人胃口。積極引導(dǎo)學(xué)生作課外閱讀,筆者也十分贊成,但如果學(xué)生只是泛泛地作課外閱讀,往往耗時(shí)多,太散漫,見效慢。課內(nèi)抓住一些典型文本,以分段歸納的形式,指點(diǎn)學(xué)生分析歸納的技法還是不可或缺的。課外閱讀之后,作些摘錄識記,進(jìn)行語言積累,也屬必要。
課堂上,筆者先讓學(xué)生標(biāo)出《斑紋》全文的14個(gè)自然段,然后讓學(xué)生嘗試著給全文分一分大段。多數(shù)學(xué)生都將全文分成三段,每段的段意概括也基本正確,但在第二大段該從何處開始和在何處結(jié)束這兩個(gè)問題上存在較多分歧。有的認(rèn)為第一大段是第1至第5自然段,有的認(rèn)為是第1至第6自然段;有人認(rèn)為第二大段是第5至第9自然段,有的認(rèn)為是第5至第10自然段,還有的認(rèn)為是第6至第11自然段。
劃分段落,歸納段意,在教學(xué)中往往是比較枯燥的環(huán)節(jié),現(xiàn)在有些過分注意“人文性”的教師常常不愿意讓學(xué)生干分段的活兒。但概括提煉能力是語文學(xué)習(xí)中極為重要的能力,這種能力不足,學(xué)生的閱讀能力、應(yīng)考能力都無從談起。在語文學(xué)習(xí)能力中,能把薄書讀厚,把短文讀長,反映出的是一種高水平的聯(lián)類想象能力;而能把厚書讀薄,把長文讀短,反映出的則是一種十分可貴的提煉概括能力。平時(shí)如果不拿一些典型文本訓(xùn)練學(xué)生的分段概括能力,學(xué)生的閱讀鑒賞能力與寫作能力都會受到嚴(yán)重影響。在高考寫作中,經(jīng)常會有考生出現(xiàn)審題偏差的現(xiàn)象,審題一著不慎,寫作就會滿盤皆輸。作文審題能力的低下,與抽象概括能力的訓(xùn)練不足是大有關(guān)聯(lián)的。
怎樣分段,分段的依據(jù)是什么,怎樣概括提煉段意,教師要教給學(xué)生方法和技巧。
筆者讓學(xué)生認(rèn)真研讀第6自然段的內(nèi)容,然后再來探討,此段是應(yīng)該跟上歸入第一大段呢,還是應(yīng)該跟下歸入第二大段?認(rèn)真研讀后,學(xué)生覺得,第6自然段雖然提及蛇的斑紋,但更多的篇幅已是敘寫蓑鲉的斑紋,而且此段中的最后一句“多數(shù)動物不像蓑鲉的興趣那樣折中,它們只選其一:要么斑紋,要么斑塊,要么斑點(diǎn)”,已經(jīng)很明顯地帶有“啟下”性質(zhì),與后面的段落銜接非常緊密。因此,第6自然段應(yīng)歸入第二大段中。
再讓學(xué)生認(rèn)真研習(xí)第8、9自然段,學(xué)生發(fā)現(xiàn),這兩段講的都是捕食者與被捕食者的特點(diǎn)及兩者的關(guān)系,這兩段自然不能分開。至于第10自然段,學(xué)生研讀后發(fā)現(xiàn),它依然如前面的幾段,在敘寫“其他動物”(包括最高級動物人類)身上的斑紋。有鑒于此,這一段應(yīng)歸入第二大段。而第11自然段,已經(jīng)是在講“大地”等非動物的斑紋,因此,不應(yīng)歸入第二大段。
段意的提煉概括,一般有三種方法:
1.襲用原文詞句歸納提煉:有些段落有中心句,抓住了中心句,就能很好地提煉出段落大意。
2.借用原文有關(guān)詞句,再加自己的語言提煉概括。
3.原文沒有可直接襲用的現(xiàn)成詞句,必須綜合歸納段落內(nèi)容,完全用自己的語言概括。
對于《斑紋》一文的三個(gè)大段的段意概括,主要運(yùn)用第三種方法進(jìn)行整理歸納,概括提煉如下:
第一段:寫蛇的斑紋,并介紹了蛇的一些生活習(xí)性以及與蛇有關(guān)的一些文化。
第二段:介紹和描繪其他動物、昆蟲及人類身上的斑紋。
第三段:從更大范圍上介紹和描繪大地上的動植物、人類日常生活和心靈世界以及宇宙空間的斑紋。
有效的識記就是合理的編碼。如何給歸納出來的這些知識進(jìn)行合理甚或巧妙的編碼,筆者動了點(diǎn)腦筋。課前,筆者在黑板上橫向等距離畫了五個(gè)由小到大的半圓,這下派上用場了。筆者問學(xué)生,黑板上的圖案像什么,原以為學(xué)生都會回答像聲波,想不到不少學(xué)生說像Wi-Fi圖案。這一說,還真像。只不過筆者畫的半圓是橫向的,而Wi-Fi圖案的半圓是縱向的。反正挺好玩,學(xué)生喜歡。筆者說高二時(shí)老師曾用這種圖案概括過一篇文章的思路,那篇文章就是“必修三”中墨子的《非攻》。筆者想來個(gè)溫故知新,于是抽了幾名學(xué)生,讓學(xué)生來說說《非攻》的寫作思路,并在黑板上的四個(gè)半圓內(nèi)填上合適的詞語。想不到學(xué)生都想不起《非攻》的內(nèi)容了。又是趕進(jìn)度、忙應(yīng)試惹的禍。上“必修三”時(shí),各班因?yàn)槊τ趯Ω对驴迹忌系么掖颐γΓ寣W(xué)生誦讀記憶的時(shí)間實(shí)在太少。現(xiàn)在筆者所執(zhí)教的兩個(gè)班也難免此弊。只得抽出點(diǎn)時(shí)間,幫助學(xué)生喚醒記憶。于是點(diǎn)著黑板上的半圓,筆者將《非攻》的寫作思路梳理了一遍:
竊人桃李—攘人犬豕雞豚—入欄廄取人牛馬—?dú)⑷嗽截洝ㄐ⊥怠型怠蟊I)
以上內(nèi)容一說,《非攻》的一條由小到大的寫作思路立現(xiàn)。
同理,《斑紋》也可以用此圖案概括其寫作思路和說明順序,不過只用三個(gè)半圓就夠了:
蛇的斑紋—其他動物、昆蟲及人類的斑紋—宇宙萬物的斑紋
這下,《斑紋》的寫作思路和說明順序就生動直觀地展現(xiàn)在學(xué)生面前:從小到大,由點(diǎn)到面,由實(shí)到虛。
理清了寫作思路和說明順序,最重要的就是品咂文中錦繡斑斕的語言了。《斑紋》全篇,語句可圈可點(diǎn)之處太多,筆者采取了以點(diǎn)帶面、舉一反三之法予以解決。
筆者選了第1、2自然段,讓學(xué)生體會比喻、擬人手法的妙用,選第10自然段,讓學(xué)生品味排比的韻味,選第8自然段,讓學(xué)生體察記敘、描寫、說明、議論等多種表達(dá)方式綜合運(yùn)用的奇妙。有了這四段的閱讀體驗(yàn),其余的段落就讓學(xué)生自行舉一反三地研讀。在判斷修辭、審讀表達(dá)方式的過程中,學(xué)生會犯一些迷糊。比如第10自然段,就有不少學(xué)生判斷不出此段用得最典型最普遍的排比修辭手法。這下啟發(fā)誘導(dǎo)的功夫就得用上了,讓學(xué)生仔細(xì)審讀段內(nèi)的語句結(jié)構(gòu)特點(diǎn),學(xué)生才發(fā)現(xiàn),此段主要是由一個(gè)由多個(gè)偏正結(jié)構(gòu)詞語構(gòu)成的句群加一個(gè)由多個(gè)主謂句構(gòu)成的句群組合而成的。三個(gè)或三個(gè)以上結(jié)構(gòu)相同或相近的詞語或句子構(gòu)成的句群構(gòu)成排比句,明乎這些,學(xué)生對修辭的判斷就會更精準(zhǔn)些。
附:語文特級教師肖培東老師的評價(jià)
紹興一中聽《斑紋》教學(xué)
孫紹振老師用“審智散文和線性的開放結(jié)構(gòu)”來解說:“《斑紋》是一篇散文,但沒有抒情敘事,如果以抒情敘事的眼光來看,就看不懂了。文章似乎是說理的,但更像是在說明,有點(diǎn)像說明文,可是以說明文的眼光來看也不恰當(dāng)。因?yàn)檫@篇文章的說明并不是客觀的,而是相當(dāng)主觀的;其主觀又并非情感性的,因而它不屬于審美的。”太深了,《斑紋》!
這樣一想,這篇文章,教師肯定教得費(fèi)力。
陳益林老師教《斑紋》,主要是理清寫作思路和語言品咂,我覺得很是聰明。“蛇—其他動物—大地、人類、宇宙。”“從小到大,由實(shí)到虛。”在語文品味的時(shí)候,陳老師認(rèn)為,《斑紋》全篇,語句可圈可點(diǎn)之處太多,只能采取以點(diǎn)帶面、舉一反三之法予以解決。這是很安全的教學(xué),也是很智慧的教學(xué)。陳老師避開了大段的哲理句子。這些句子不是不能說,而是根本說不盡、說不清。上《斑紋》,最好就是“窺一斑見全豹”,甚至見不了全豹也沒關(guān)系,在作者詭異的描述前,也許感知就是進(jìn)步。
我會怎么上?我得好好想想。
我肯定講不好《斑紋》,因?yàn)槲也涣私膺@樣的詭異:“由于距離的遙遠(yuǎn),在神眼里,我們,不過是一些斑點(diǎn)。”有點(diǎn)虛無,甚至有點(diǎn)幻滅,但屬于虛而非無,幻而未滅。這種斑紋,只值得皈依,而無法宣講。你不要逼我深刻,我也無法立馬深刻。周曉楓的語言警句太多,智慧的密度太大,我讀起來總會有大腦缺氧的感覺。
既然講不完“斑紋”,我就講“斑點(diǎn)”吧。文章太長,斑紋太多,課時(shí)太短,那么就從“蛇”突破,以窺全文,以感悟作者之理。文章描繪了形形色色的斑紋,敘述了大自然與人類社會許多奇妙的現(xiàn)象,其中對蛇的斑紋寫得最為詳細(xì),并也密布作者的哲理警句。語文課,或者說一堂語文課,本來就不可能解決所有,教學(xué)只是個(gè)起點(diǎn),課堂以后的閱讀才是最關(guān)鍵的路程。
(責(zé)任編輯:李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