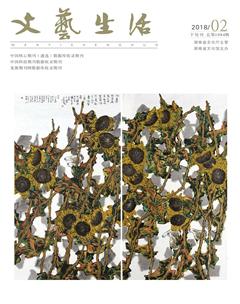從蘇珊·桑塔格對萊妮·里芬斯塔爾作品的評價討論藝術(shù)接受的倫理
周莉娟
摘要:蘇珊·桑塔格無疑是認同萊妮·里芬斯塔爾的審美的,但在寫下《論風(fēng)格》后十年,桑塔格還在反思自己對里芬斯塔爾作品的“無法抗拒”,并再寫下《迷人的法西斯主義》。本文考察這一過程,希望借此討論一種接受藝術(shù)的方式。
關(guān)鍵詞:法西斯美學(xué);紀錄片;藝術(shù)接受
中圖分類號:J9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8)06-0034-01
一、里芬斯塔爾的人造真實
后來關(guān)于里芬斯塔爾的故事里總是少不了她的“投機”,她慣于編故事:在納粹執(zhí)政時代回避幫助過自己的猶太人;在納粹倒臺后否認與納粹的關(guān)系;拍紀錄片也不忌諱編造,并稱之為對作品的苛求:
“若結(jié)果還是不理想,她便要求大家重新來過——即使在奧運會上(男子撐桿跳的選手就為她一次又一次‘飾演了自己先前的比賽)。”
“……鋪張的發(fā)揮……大張旗鼓地展開拍攝。”
但因此,里芬斯塔爾與納粹合作的紀錄片卻在譴責(zé)納粹聲音最大的年代,被譽為了偉大的影片:
“把萊妮·里芬斯塔爾的《意志的勝利》和《奧林匹亞》稱為杰作,并不是在以美學(xué)的寬容來掩蓋納粹的宣傳。其中存在著納粹宣傳,但也存在著我們難以割舍的別的東西。”
二、桑塔格與里芬斯塔爾的共識
(一)藝術(shù)是表現(xiàn)的
里芬斯塔爾與納粹政府合作的藝術(shù)被認為是法西斯審美的完美表征,在桑塔格(和大多數(shù)批評家)看來,納粹的審美/價值觀是這樣的:
“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一個主要的譴責(zé)就是他們是都市的、知性的,是破壞性的、起腐蝕作用的‘批評精神的擁有者。……將頭腦凌駕于心靈之上、將個人凌駕于集體之上、將理智凌駕于情感之上。……自封的‘文明本身是褻瀆者。”
而“里芬斯塔爾這兩部影片(在納粹藝術(shù)家的作品中別具一格)展現(xiàn)了靈氣、優(yōu)美和感性的復(fù)雜動態(tài)……”,從桑塔格的論述中可見,她也相信藝術(shù)是在表現(xiàn)先于藝術(shù)、并超越理智的存在,且認同藝術(shù)偏離“中立”的合法性。表現(xiàn)總是不完備、有噪音,表現(xiàn)過程中(相對于絕對對象)的偏離就形成了風(fēng)格。
“……一旦我們的言論、動作、舉止或物品展現(xiàn)出某種與我們在現(xiàn)實世界中最直接、有用、無感覺的表達和存在模式相偏離的因素,那么,我們就把它們看作是擁有一種‘風(fēng)格,把它們看做既是自主的,又是表征的。”
(二)藝術(shù)是引誘
因為在認同形式之美上的一些共識,桑塔格關(guān)注了里芬斯塔爾,這大概就是桑塔格說的“引誘”:“現(xiàn)在重要的是恢復(fù)我們的感覺,我們必須學(xué)會去更多地看,更多地聽,更多地感覺。”而正好,“納粹藝術(shù)的魅力也許在于它簡單、形象,是感性的而非智性的;它讓人擺脫了現(xiàn)代主義藝術(shù)那種費勁才能理解的種種復(fù)雜性而感到一身輕松。”
在《論風(fēng)格》之后,桑塔格一直反思自己被里芬斯塔爾的作品的形式美所引誘的機理及其與“道德”的關(guān)系,于是我們看到在《迷人的法西斯主義》中,她從更深的層面分析了法西斯的“美”,描述了法西斯審美(尤其是其政權(quán)倒臺后)與虐戀文化的顯著關(guān)聯(lián),為自己的被引誘找到更深入人類本性的理由:
“討論法西斯主義歷史的課程,和討論神秘主義(包括吸血鬼迷信)的課程一起成為一所所大學(xué)課堂里聽課人數(shù)最多的科目”
“現(xiàn)在,人人都能看到一份總的劇本提綱。顏色是黑色,材料是皮革,誘惑是美,正當性是真誠,目標是高潮,幻想是死亡。”
桑塔格對里芬斯塔爾的經(jīng)年的欣賞和批評展示出接受藝術(shù)作品的最穩(wěn)妥的方式——努力讓感官接受引誘,也努力求知和反思。
三、藝術(shù)與法外
道德和法律被默認為是歷史的,藝術(shù)被默認為是永恒的。在《論風(fēng)格》的前幾頁,桑塔格描述一般倫理中的罪行如何通過藝術(shù)作品而被認可,里芬斯塔爾的作品是她的一個例子,后來她也提到政治家是如何利用這種慣例。各種形態(tài)的社會中幾乎都有一般社會懲罰豁免權(quán)的少數(shù)人:藝術(shù)家,政治家,巫,先知,或者各種其他稱呼。
而觀眾或大眾的責(zé)任,應(yīng)是在這些得到豁免權(quán)的小群體面前,在自己難以割舍的或不能忍受的存在面前,持續(xù)求知和反思。而藝術(shù)如果有什么教育功能的話,就是提供各種難以割舍和不能忍受的東西,讓我們有機會一遍遍在自己的欣喜或憤怒中練習(xí)如何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