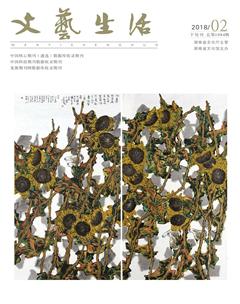論早期城市劇場的公共性
孫曉雪
摘要:劇場是西方文化史上最具穩定性的建筑形態,不僅為觀眾提供了在劇場中觀演的主要空間,同時也為市民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公共活動空間,與集市、競技場一同承載了早期城市市民聚集的核心功能。
關鍵詞:劇院劇場;城市劇院
中圖分類號:J6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8)06-0146-02
一、前言
從2007年國家大劇院的建成和投入使用開始,以我國劇場建設為引領的文化產業發展在積極文化政策的支持下,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各地大型劇院以平均每年10家的速度快速建設,國有文化集團頻現大手筆制作,社會資本投巨資興建秀場、主題公園,全國每年舉辦的大型演出數量更是超過以往。但在成績的背后,作為研究者的我們也有義務關注到新建劇院的經營難題、大型項目的票房尷尬、文化地產的真實動機以及它們對表演藝術生存空間帶來的擠壓,而劇場觀念模糊不清與劇場功能的定位偏差則是這些問題產生的重要原因。
劇場是西方文化史上最具穩定性的建筑形態。在城市化的進程中,宮殿、凱旋門等建筑逐漸被工廠、火車站等替代,而誕生于希臘古典時期的劇場作為功能性公共建筑與市場一樣被保留了下來,并逐漸傳播和影響到世界其他地區的表演藝術空間建設與運營。表演藝術與其他文化表現形式相比,“現場性,是其極為重要的特性。從作品的傳播來看,除演員與觀眾要素外,物理空間是現場演出的實現不能脫離的必要條件。就藝術創作而言,空間設置也是作者、表演者思想表達的重要手段,特別是當代戲劇將觀眾的角色在藝術創作過程中進行重新定位之后,這個數量龐大的主體為作品帶入的是其不能分割的當下社會與文化經驗。劇場本身構成了觀眾戲劇體驗的一個必要的環節。作為表演藝術創作和傳播的基礎空間和物理媒介,劇場則是“演出產業”、“演藝經紀”存在和發展的基石。
而隨著近些年西方商業劇場運行觀念的引入,很多由政府資助的公立劇院也開始進行商業化運營轉向,大量“現場娛樂”產品也開始大量涌入劇場,不僅混淆了觀眾的試聽,同時也嚴重地擠壓了傳統嚴肅表演藝術、特別是我國本土表演藝術作品的生存空間,更使得作為公共文化設施重要組成部分的公立劇院出現了一定程度的身份危機,在“公立”與“商業”、“藝術”與“市場”之間游移搖擺,喪失了劇場的根本屬性,關于劇場的身份屬性研究成為了一種必要。
英文“劇場”一詞“Theatre”源于希臘語“theatron”,意為“一個觀看的場所”(a place for looking)。因此該詞在英文中最初使用時具有“場所”(a place)以及“一種特殊的感覺知覺形式”(to a particular form of sense perception)的雙重意味。
隨著劇場理論與實踐的發展,其含義得到了進一步的擴充,包含以下四個層面的意義:(1)觀演建筑的主要類型之一:(2)兩種以劇場為核心的活動(觀演和表演):(3)戲劇表演藝術機構:(4)最為狹義的表述,一種表演藝術形式。但無論是作為觀演場所還是藝術形式,劇場在形成之初作為市民公共活動空間的特征卻被保留至今。
盡管學界對于古希臘劇場的建筑細節長期意見不一,但關于劇場在城市中的位置卻并無爭論。作為一個集合演員與觀眾的公共物理空間,劇場看臺以樂池為核心呈扇形分布,不僅為觀眾提供了在劇場中觀演的主要空間,同時也為市民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公共活動空間,與集市、競技場一同承載了早期城市市民聚集的核心功能。古希臘歷史及地理學家帕薩尼亞斯在對當時城市的記載中無一例外地對各城市的劇場進行了大量描述,直至今天,我們還可以從當時城市遺址中看到劇場的痕跡,可見其在當時城市布局中的重要地位。
二、古典時期
古典時期的希臘劇場看臺通常由木結構支撐,由于承重限制,其在觀眾數量達到上限是容易產生安全問題,加之希臘城邦并不向羅馬城市擁有充足的財富、勞動力以及拱頂建造技術限制,絕大多數古希臘城市將劇場選址于能夠為觀眾提供天然看臺的緩坡或能為樂池提供三面封閉的洼地上。正是由于古希臘劇場的這一特點,與后期的其他劇場相比,其在城市中的位置并不固定。但作為一個“觀看”的場所,劇場中看臺的方位設置卻在科林斯、普里恩、艾菲索斯等許多城市中卻體現了出了一定的共同特征,即建筑符號另一層面的內涵——觀眾在看臺上看到的不限于表演空間,還包含了壯觀的下城景觀、城墻以及遠處的平原或海洋。如同羅蘭·巴特對于埃菲爾鐵塔的描述,這種模式的劇場設計同樣承擔了雙重的功能:一是,成為了一定意義上的文化紀念碑,二是為表演者提供了宏偉的天然布景和人工景觀。
極少數情況下,劇場被建造于衛城底部作為連接衛城與下城中心的集會中心——集市的紐帶。也有歷史學家認為集市本身就是早期戲劇的主要表演場所,但從佩加蒙的城市布局(圖1)來看,情況更傾向于前者。在雅典的案例中,劇院的選址還與酒神崇拜有關,地形、交通以及宗教傳統共同決定了狄奧尼索斯劇場的選址,與集市、衛城、神殿以及競技場共同構成了城市的主要組成部分。
三、希臘化和羅馬時期
希臘化時期劇場建筑的選址逐漸脫離了地形條件的限制,主要由城市布局中與其他關聯要素的關系決定。獨體房屋(Skene House)與觀眾席(Auditorium)的發展緊密關聯,得益于羅馬在承重墻與穹頂方面的技術進步,劇場幾乎可以選址于任何足以承重的地形上。盡管關于龐培以及其后羅馬城市中的永久性劇場選址條件,考古與歷史界長期存在著熱烈的爭論,但是可以達成共識的是,地形已不再是關鍵要素。盡管有著很多適合采用希臘方式建造劇院的地形,但從結果上來看,所有永久性劇院都選擇建造于平坦地勢上,集中于類似于我們今天常說的“劇院聚集區一戰神廣場。
羅馬帝國時期的城市的布局通常呈嚴整的幾何形態,從提姆加德遺址、都靈、奧斯塔的情況看,經常稱軸線穿越中心或一側的矩形形態。劇場對于羅馬城市而言具有與希臘城市一樣的重要位置,但選址不受地形影響,通常位于城市的一角或靠近主要城門的城市邊沿地帶,作為城市布局中的一個重要元素被安置于主要節點處。
四、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
在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將劇場空間視為公共紀念建筑的觀念是整體缺失的。直至巴洛克時期,類似觀念才在城市規劃中再次出現。盡管第一批后古典時期的公共劇院在城市規劃中的地位方面與文藝復興早期的王公大廳(princely halls)以及改良的演藝空間相比更加接近古典時期的劇場,但這些劇場在當時所扮演的社會角色卻發生了改變。
古希臘與羅馬時期的公共劇院作為主要的市民紀念物在城市文本中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與之相反,巴黎和倫敦的第一批劇院則更多建設于危險與模糊的城市邊緣位置。該時期劇場被置于城市邊緣的原因并不向希臘劇場基于地形因素的考量,而是由于劇場自身社會角色的模糊不清和被邊緣化。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在以倫敦為代表的城市里劇場的選址要刻意回避各方面的沖突。盡管戲劇表演與城市文化生活的核心緊密相連,但卻被市政官方拒之千里之外,議會拒絕將劇場作為合法構成納入城市規劃。
對于絕大多數市政當局來說,其對待流動劇團的臨時性表演場所與當地劇團的永久性場館的態度是截然不同的,對于前者,他們是非常寬容的,然而一旦劇團試圖通過建立永久性劇場的方式在城市結構中為自己的身份尋求合法性依據,政府的態度就會發生根本性的轉變。
在文藝復興時期,僅Confrerie de la Passion一家劇團在皇家法令的特許下在巴黎商業中心附近找到了一家不太起眼的建筑作為演出場所。而第一批倫敦劇團由于沒有皇家的支持,則無法在永久劇院選址方面對抗市政當局的壓力,只能視情況在市場管理范圍外的任何地方見縫插針,吸引步行范圍內的觀眾人群,從而形成了該時期劇場運行的一個固定模式。
貫穿整個文藝復興時期,公共劇場在英國社會文化中處于“邊緣化”的位置,這也反映在了其邊緣性的城市位置上,盡管其存續完全依賴于城市,然而地理位置上看,卻從來沒能真正成為城市的一部份。劇場成為了城市布局中的一個尷尬不見,盡管在城市生活中發揮著獨立、特殊的作用,但卻沒能成為肯尼斯·林奇(Kenneth Lynch)意義上的具有話語權的城市地標,直到300年之后,才作為建筑在倫敦的城市規劃中取得了自身的合法性地位。同時期其他地區的劇院雖然數量不多,但選址情況優于倫敦,與巴黎更為類似,遺憾的是均未對城市布局產生過重要影響。即便在優良地段,劇場也更多地是躲藏在狹窄的街道里還不是該地區的地標。直至十七世紀末十八世紀早期,歐洲大陸公共劇院與城市的關系才逐漸發生改善,從一個隱蔽的居所逐漸上升到城市文本中的顯要部門,地位比肩古典時期的希臘劇場,重新開啟了從王宮劇院向公共劇場發展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