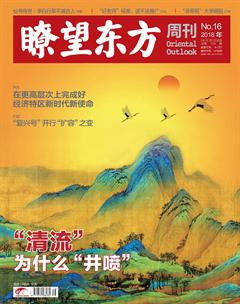文化類節(jié)目“曲高和眾”的邏輯
李璇 高雪梅
2013年以來,《漢字英雄》《中華好故事》《中國成語大會》等節(jié)目,讓表現(xiàn)傳統(tǒng)文化的電視節(jié)目,漸漸走入了人們的視野。
2017年,隨著《中國詩詞大會2》《見字如面》《朗讀者》等“現(xiàn)象級”節(jié)目的熱播,蓄積已久的文化類節(jié)目才真正獲得了大眾的關(guān)注,在熒屏內(nèi)外帶動了“文字熱”“詩詞熱”“朗讀熱”的興起。
2018年,《國家寶藏》《經(jīng)典詠流傳》《非凡匠心2》《傳承中國》《信·中國》等節(jié)目依然表現(xiàn)搶眼,在繼續(xù)帶動社會話題熱度的同時,也讓文化類節(jié)目從數(shù)量和質(zhì)量上實(shí)現(xiàn)了井噴式的爆發(fā)。
文化類節(jié)目,究竟為何而“火”?
“中華文化基因”的原創(chuàng)表達(dá)
不少媒體將2017年稱為“文化類節(jié)目元年”。
2017年1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wù)院辦公廳印發(fā)了《關(guān)于實(shí)施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傳承發(fā)展工程的意見》,要求“實(shí)施中華文化電視傳播工程”,“組織創(chuàng)作生產(chǎn)一批傳承中華文化基因、具有大眾親和力的節(jié)目欄目”。
也是在這一年里,幾檔原創(chuàng)類文化綜藝“引爆”了熒屏。
《朗讀者》采用“訪談+朗讀”的模式以情動人,在美文中展現(xiàn)朗讀者的個人生命體驗(yàn);《中國詩詞大會2》憑借新設(shè)立的“飛花令”環(huán)節(jié),讓古典詩詞“飛”進(jìn)了觀眾的心中。
連環(huán)效應(yīng)之下,朗讀類、詩詞類節(jié)目如雨后春筍般涌現(xiàn)出來。但由于這類節(jié)目具備一定的觀看門檻,在大量同質(zhì)節(jié)目的“輪番轟炸”之后,如何在傳統(tǒng)文化的寶庫中找到新的生發(fā)點(diǎn)、探索文化類節(jié)目更多的可能性,成為了擺在電視人面前的挑戰(zhàn)。
2017年7月,國家有關(guān)部門下發(fā)《關(guān)于把電視上星綜合頻道辦成講導(dǎo)向、有文化的傳播平臺的通知》,提出“要堅(jiān)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挖掘利用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jìn)文化資源,結(jié)合新的時代特點(diǎn)和實(shí)踐要求,制作播出更多有思想深度、精神高度、文化厚度的文化類節(jié)目”。
政策的扶持、節(jié)目更新的實(shí)際需要,為文化類節(jié)目在題材范疇、結(jié)構(gòu)形式和創(chuàng)作理念上的進(jìn)一步突破提供了契機(jī)。
2017年年底開始,《國家寶藏》在中央電視臺綜藝頻道首播,這檔旨在講述文物故事的文博探索類節(jié)目一經(jīng)播出,便迅速變身“網(wǎng)紅”,得到了大批觀眾的“自來水”推薦。這檔節(jié)目通過融合演播室綜藝、紀(jì)錄片、真人秀等多種藝術(shù)形式,以生動鮮活的方式,將27件文物的“前世今生”展現(xiàn)在觀眾面前。
而2018年春節(jié)期間播出的《經(jīng)典詠流傳》,以“和詩以歌”的方式,將詩詞與流行音樂相結(jié)合,在開播次日便取得了9.3分的豆瓣評分。
知名作家梁曉聲這樣評價(jià)節(jié)目在形式上的新意:“相比以記憶和賞析為主的文化節(jié)目,《經(jīng)典詠流傳》更上一層樓,將音樂和文學(xué)、傳統(tǒng)和時尚、欣賞和鑒賞都進(jìn)行了高度統(tǒng)一,為現(xiàn)代文明追本溯源,樹立文化自信,展現(xiàn)的是一種更加高遠(yuǎn)的格局、更趨飽滿的融合、更具創(chuàng)新的重構(gòu)。”
與娛樂性的綜藝節(jié)目相較,文化類節(jié)目重在傳承“中華文化基因”,這離不開中國獨(dú)有的文化資源。因此,節(jié)目從性質(zhì)上便有著先在的原創(chuàng)性。文化類節(jié)目的崛起,也意味著國產(chǎn)綜藝節(jié)目找到了自主創(chuàng)新的一種方向。
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4月,九檔中國原創(chuàng)節(jié)目在戛納春季電視節(jié)主舞臺上集體亮相,在這九檔節(jié)目中,包括《國家寶藏》《朗讀者》《經(jīng)典詠流傳》在內(nèi)的文化類節(jié)目占據(jù)了相當(dāng)?shù)臄?shù)量。
在中國原創(chuàng)節(jié)目走出國門的歷程中,文化類節(jié)目已經(jīng)寫下了重要的一筆。
“高而不冷”
“曲高和寡”,是很多觀眾對文化類節(jié)目的第一印象。
如何讓看似“高冷”的文化類節(jié)目“高而不冷”“曲高和眾”,是文化類節(jié)目取得成功的關(guān)鍵,也是觀眾能否在節(jié)目中感受到傳統(tǒng)文化魅力,進(jìn)而產(chǎn)生參與感和共鳴的基礎(chǔ)。
2017年以來,隨著文化類節(jié)目的爆發(fā)式增長,其表現(xiàn)形式也日益豐富,發(fā)展出文化情感類、文博探索類、文化益智類、文化真人秀等類別。而詩詞歌賦、國寶非遺、戲劇戲曲、名人家書等內(nèi)容,也作為內(nèi)核填充進(jìn)了節(jié)目的架構(gòu)中。
形式與內(nèi)容的雙重拓展,讓文化類節(jié)目的趣味性、可看性大為增強(qiáng)。
《國家寶藏》每一期都設(shè)置了“小劇場”環(huán)節(jié),由明星演繹文物的“前世傳奇”,其中不乏幽默趣致的段落,如乾隆皇帝因“農(nóng)家樂”審美頻頻遭遇“吐槽”、小吏“喜”上演秦國版《今日說法》等,都讓觀眾會心一笑,增強(qiáng)了觀賞興趣。
京劇文化傳承節(jié)目《傳承中國》為還原戲劇情境,將錄影棚打造成具備梨園特色的“傳承社”;在京劇唱段上,為照顧觀眾的欣賞口味,選取了《貴妃醉酒》《四郎探母》等普及度較高的選段。
《非凡匠心2》以講述匠人故事為核心,深入匠人的故鄉(xiāng),將探尋匠藝的過程融入當(dāng)?shù)氐娘L(fēng)土人情之中,還原了匠人的鮮活個性與傳奇人生。
在《非凡匠心2》總導(dǎo)演彭婉笛看來,文化類節(jié)目的趣味性,離不開文化性的滋養(yǎng)生發(fā)。
“如果把節(jié)目比作河流,那么河底是文化性的部分,河中的魚和水草則是趣味性的部分,趣味性是不能游離于文化性之外的。”彭婉笛向《瞭望東方周刊》說。
《國家寶藏》總導(dǎo)演兼制片人于蕾也向《瞭望東方周刊》透露,每件文物背后的故事,都是最貼近文物價(jià)值的。
“很多人都以為喜的故事經(jīng)過了大量的藝術(shù)加工,其實(shí)這段故事反而是最接近史料的。被觀眾戲稱為‘今日說法的著詩問答的形式,在云夢睡虎地秦簡中本身就是存在的。”于蕾說。
越來越多電視制作人意識到,對于文化類節(jié)目而言,增添節(jié)目的趣味性,并不意味著要脫離節(jié)目的文化訴求、落入過度娛樂的泥沼,而是要在浩如煙海的文化資源中挖掘出新的趣味,讓文化本身變得有意思起來。
他們發(fā)現(xiàn),自帶“流量”的明星嘉賓、聲光舞美的現(xiàn)代技術(shù)固然吸睛,但唯有源遠(yuǎn)流長的中華文化,才是文化類節(jié)目從“一枝獨(dú)秀”發(fā)展到“春色滿園”的內(nèi)在源泉。
向年輕觀眾傾斜
梁曉聲曾這樣評價(jià)文化與思想之間的關(guān)系:“文化不是供人欣賞的所謂優(yōu)雅文藝,或是供人娛樂的所謂通俗文藝,文化從來就和思想緊密相連。當(dāng)我們逐步告別了物質(zhì)匱乏的時代之后,更要用有格調(diào)、有營養(yǎng)的精神食糧喂飽大眾尤其是年輕一代的靈魂。”
這兩年來“井噴式”爆發(fā)的文化類節(jié)目,也在向年輕觀眾傾斜。
據(jù)于蕾回憶,制作《國家寶藏》節(jié)目的初衷,便是要吸引年輕觀眾的關(guān)注:“我們從來不缺少高收視的節(jié)目,但是我們?nèi)鄙俚氖悄軌蛭贻p人的、能夠創(chuàng)造話題的節(jié)目。”
《國家寶藏》播出后,節(jié)目組以一種圓滿的方式實(shí)現(xiàn)了初心。有數(shù)據(jù)調(diào)查公司為節(jié)目組提供了《國家寶藏》的受眾數(shù)據(jù):其主體人群中, 20~25歲的年輕人最多,15~20歲的青少年緊隨其后。
在年輕人扎堆的嗶哩嗶哩視頻網(wǎng)站上,于蕾曾仔細(xì)觀察過《國家寶藏》節(jié)目的彈幕,并得出了這樣的結(jié)論:孩子們看得實(shí)在是太仔細(xì)了。
“在《千里江山圖》播放的時候,主持人還在與嘉賓訪談,彈幕里卻都在說‘快看,后面的水波紋在動,他們真是注意到了所有細(xì)節(jié),就像在批改作業(yè)一樣,一幀一幀地過。”
《國家寶藏》并非是唯一一檔與年輕人群體互動頻繁的文化類節(jié)目。
在《傳承中國》制片人田川眼中,戲曲傳承類節(jié)目的主要受眾群體并非是懂戲的中老年人和票友,而是年輕人:“我們就是在慢慢培養(yǎng)觀眾,沒準(zhǔn)某個有趣的內(nèi)容會讓他們覺得,京劇還真不錯,想繼續(xù)了解。那我們就成功了。”
而《非凡匠心2》的制作團(tuán)隊(duì)本身就是由“85后”“90后”構(gòu)成。
“由年輕人來做這個節(jié)目,能夠帶來不一樣的視角,讓看似古老的事物變得鮮活起來,與年輕觀眾的聯(lián)系也能更緊密。”《非凡匠心2》制作人毛嘉說。
事實(shí)上,年輕人群體在文化類節(jié)目的制作與傳播中,都發(fā)揮著重要的作用。
“文化類節(jié)目在年輕人群體中掀起的巨大反響,讓我們非常興奮地看到,年輕一代對傳統(tǒng)文化有一種強(qiáng)烈的‘渴望和‘自豪,這反過來又刺激創(chuàng)作團(tuán)隊(duì)不斷探索親近年輕人的路徑和技巧,讓他們自然而然被吸引和喚起,發(fā)自肺腑地認(rèn)同傳統(tǒng)文化的美好、深刻和震撼。”中國傳媒大學(xué)電視與新聞學(xué)院院長、教授高曉虹告訴《瞭望東方周刊》。
從傳播到傳承
不少人都留意到,在《經(jīng)典詠流傳》這檔節(jié)目里,場內(nèi)觀眾都佩戴著一個心形裝置,這個裝置能夠讓觀眾即興“點(diǎn)亮”,大屏?xí)⑺屑t心匯聚在一起,寓意著對經(jīng)典流傳激情的累積;而場外觀眾則可以通過微信“搖一搖”,不斷疊加“心動指數(shù)”。
在中國社科院世界傳媒研究中心秘書長、副研究員冷凇看來,這個原創(chuàng)裝置“將觀眾的‘心動做了一種驚喜感、懸念感、儀式感合一的外化呈現(xiàn)”,加強(qiáng)了節(jié)目的互動性,“使得每一首歌曲都有不低于千萬人次的人群進(jìn)行跨屏交互,實(shí)現(xiàn)了媒介的融合創(chuàng)新”。
媒介的融合創(chuàng)新,為大眾參與文化類節(jié)目的傳播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在線上與線下、大屏與小屏之間,每個人都可以是文化的傳播者。
而從“傳播”到“傳承”,除了媒介的融合創(chuàng)新,文化類節(jié)目還在情感的表達(dá)上實(shí)現(xiàn)了今古相通——通過挖掘傳統(tǒng)文化的當(dāng)代價(jià)值,尋找到與現(xiàn)代觀眾的生活相契合的內(nèi)容。
高曉虹這樣分析《經(jīng)典詠流傳》中歌曲所蘊(yùn)含的情感價(jià)值:“《明日歌》里的惜時如金、《苔》里的平凡怒放、《定風(fēng)波》里的曠達(dá)豁然、《來甦·秋思》里的鄉(xiāng)愁、《鵲橋仙》里的愛情……從過去到現(xiàn)在,人們對美好的向往,對家國的情懷,對生命的敬畏都是精神共通的。”
在《見字如面》第一季中,演員何冰曾朗讀了一封題為《我自家連一條棉褲也沒有》的信,這封信是郁達(dá)夫在1924年冬天寫給沈從文的。在信中,已經(jīng)成名的文學(xué)家郁達(dá)夫熱心地為“北漂”青年沈從文找出路、想辦法,鼓勵他奮力前行。
通過《見字如面》的傳播,近百年前的一封信被人們所知悉。而這段不為大眾所知的文壇掌故中蘊(yùn)含著的情感力量也穿透了歲月,讓當(dāng)代為夢想拼搏的人們心有戚戚、產(chǎn)生共鳴。
當(dāng)文化類節(jié)目有了情感,也就有了溫度,有了溫度,才能有故事。
《國家寶藏》中的“今生故事”,將文物與現(xiàn)代生活聯(lián)系了起來,通過考古工作者、博物館工作人員、志愿者、大學(xué)教師等現(xiàn)代講述者的講述,文物的當(dāng)代價(jià)值也呼之欲出。
“為什么是‘前世今生?就是要告訴大家,這個文物在今天還有著非常大的時代意義,而且它不會停止在今天,它的生命還將延續(xù)后世千年。”于蕾說。
中國教育科學(xué)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直言:“只有讓傳統(tǒng)文化融入到我們的現(xiàn)實(shí)生活中,才能讓傳統(tǒng)文化常駐。”
而文化類節(jié)目,為傳統(tǒng)文化融入現(xiàn)實(shí)生活,提供了情感的窗口和探尋當(dāng)代意義的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