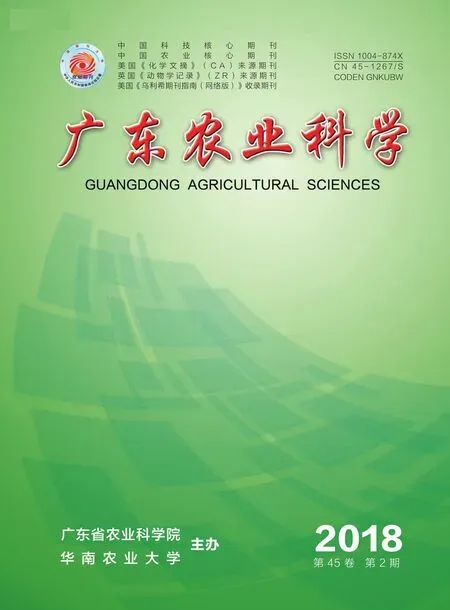1993—2013年珠海市生態承載力及生態足跡分析
謝 婕,唐以杰,林耿璇,伍瑞枝,龔玉蓮
(廣東第二師范學院生物與食品工程學院,廣東 廣州 510303)
可持續發展的定量測度是人類對自然利用程度方面的重要研究內容。20世紀90年代,加拿大環境經濟學家 William[1]和 Wackernage[2]提出一種基于生物物理量的度量評價可持續發展程度的概念和方法——生態足跡 (Ecological Footprint,EF)[3],生態足跡是指要維持一個人、地區、國家的生存所需要的或者指能夠容納人類所排放的廢物、具有生物生產力的地域面積,即能夠持續地提供資源或消納廢物、具有生物生產力的地域空間[4]。生態足跡是一種基于社會經濟代謝的非貨幣化生態系統評估工具,它能夠識別人類施加于生態系統的壓力和系統所處的狀態,并服務于自然資本管理決策和調整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5]。從2008年開始,世界自然基金會用“生態足跡”這個工具來衡量人類對資源環境的需求。近些年來,在一些學者的努力下,生態足跡理論已發展較為成熟,被廣泛應用于測算世界、國家或地區的生態足跡[6-7]。我國許多學者對不同地區的生態足跡進行研究,但研究區域多為省際上的[8-11],且多集中在西部區域[12-13],有關珠海市生態承載力的研究比較少,且多為某一年的靜態研究,如王娜[14]對珠海市2007年的生態足跡與生態承載力做了相關研究;李輝等[15]計算了珠海市2000、2005、2010、2012年4個時間點的生態承載力;陳棟為等[16]計算了珠海市2007年水資源生態足跡;李翔等[17]使用了改良的生態足跡方法計算了2002年珠海的生態足跡和水資源生態足跡。目前對珠海市生態足跡長期變化的動態研究尚未見報道。珠海市的發展以創建生態城市為主,研究其長期的生態足跡變化,對了解生態城市建設過程對環境的影響有重大意義。本研究通過分析珠海市近20年的生態足跡動態變化,評估珠海市人類活動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并根據生態足跡變化的規律,預測珠海市生態發展的可持續性。
1 材料與方法
1.1 研究區概況
珠海市位于廣東省珠江口西岸,因珠江在此入海而得名。珠海市氣候宜人,東夏季風交替明顯,終年氣溫較高,年、日溫差小,屬南亞熱帶與熱帶過渡型海洋性氣候;全市太陽能豐富,熱量充足,2013年日照時數1 910.8 h,降雨量2 884.9 mm,平均氣溫23.0℃[18]。珠海市東與香港隔海相望,南與澳門陸地相連,西鄰新會、臺山,北與中山接壤,下轄香洲、斗門、金灣3個行政區。截至2013年末,土地面積為1 724.32 km2,1993—2013年期間年常住人口由75.54萬人增加到158.65萬人,人口增加顯著,按照《中國中小城市發展報告(2010)》提出的城市劃分標準,珠海屬于大型城市。珠海市是全國五大經濟特區之一,共有8個國家一類口岸,是僅次于深圳的中國第二大口岸城市。自建立經濟特區以來,珠海市一直在保護生態與發展經濟之間尋求平衡,摸索前進。隨著改革開放戰略的全面實施,珠海市的建設重心轉移到了經濟領域,從而帶動經濟的高速增長,地區生產總值逐年上升,1978—2013年GDP年均增長13.5%(《珠海統計年鑒》),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生態環境也在發展中不斷改善。
1.2 數據來源
為了提高數據的可靠性,本研究將《珠海統計年鑒》《廣東統計年鑒》《廣州統計年鑒》等統計年鑒的數據與珠海市統計信息網、廣州市統計信息網等相關網站上所得的相關數據進行相互驗證,并根據生態足跡模型綜合法,計算珠海市生態足跡的各項關鍵參數。由于珠海市從2003年起無農業人口,故本研究所用的人口數據為珠海市各年的年平均常住人口總數,各類生物性產品消費量及珠海市的森林面積等數據均來自1993—2013年《珠海統計年鑒》和《珠海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并借鑒曹淑艷等[19]的方法進行校正。在計算水電生態容量時,由于未能找到水電的供電量,故用耗電量來代替供電量,再根據廣東省電網火電、水電的比例算出水電供電量。對于本研究計算用到的各種生物產品的全球平均產量,則主要參照文獻[4]中的數據,并以周濤等[20]的方法作參考。全國人均生態承載力和全球人均生態承載力數據來自全球生態足跡網[21]。
1.3 研究方法
1.3.1 生態承載力 有關計算采用WWF在2006年提出的等價因子,分別為:可耕地和建成地為2.21、森林和化石能源地為1.34、牧草地為0.49、水域為0.36[4]。為了保持生物多樣性及其可持續發展,人類必須保留12% 的土地面積用于生物多樣性保護,因此,計算生態承載力時要扣除這部分生產性用地面積。生態承載力EC的計算公式如下:

式中,j = 1、2、3、4時分別代表可耕地、牧草地、森林和水域(hm2),N為人口數,ec為人均生態承載力(hm2),aj為人均生態生產性土地面積(hm2),rj為均衡因子,yj為產量因子。
1.3.2 生態足跡 可耕地平均產量調整因子、全球平均產量、能地比及等量化因子,完成生態足跡模型的本地化[4],然后對1993—2013年珠海市的生態足跡EF進行計算,計算公式如下:

式中,N為人口數,ef為人均生態足跡,α為均衡因子,i為消費項目類型,ai為人均i種消費項目折算的生態生產性面積,pi為i種消費品的平均生產能力,ci為i種消費品的人均年消費量。一個地區的生態足跡還可以通過貿易途徑實現跨越地區界限的轉換,但由于沒有找到連續20年的貿易數據,故本研究在計算珠海市的生態足跡時沒有將其計算在內。
1.3.3 生態盈虧 生態盈虧計算公式為:

當EC>EF,表現為生態盈余ER;當EC<EF,表現為生態赤字ED。
根據珠海市1993—2013年近20年生態赤字數據,使用最小二乘法生成最小平方擬合的線性趨勢線公式,預測生態赤字變化趨勢。
2 結果與分析
2.1 1993—2013年珠海市生態承載力變化

圖1 1993—2013年珠海市生態承載力組成
由圖1可見,珠海市1993—2013年的生態承載力在20年間呈現較大波動,1999年以前呈現上升趨勢,1999—2006年呈下降趨勢,扣除12%用于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土地面積后,2006年總生態容量最低,為207 947.1911 hm2,2006—2013年期間又逐步上升,總體呈現“升-降-升”的馬鞍型曲線。生態承載力的結構組成中,可耕地所占比例最大,其次為森林和水域,草地所占比例最小。20年來,可耕地所占比例呈下降趨勢,森林所占比例變化不大,水域所占比例逐年上升。總生態承載力呈現這種波動態勢主要是可耕地與水域變化所引起。20世紀90年代以來,珠海市的第一產業比重就持續下降,第二產業則高速發展,在90年代后期,工業跨入加速發展時期,而房地產業也急速發展,大量農田被用來興建樓宇,導致可耕地逐漸減少。但由于珠海市地處珠江三角洲,水資源豐富,在近20年的生產建設中,水產養殖業興盛發展,故水域生態生產性土地面積在20年來不斷增加。
由圖2可知,1993—2013年珠海市人均生態承載力呈現不斷下降的趨勢,從1993年的0.2795 hm2,下降到2007年最低為0.1431 hm2,之后稍回升至2013年的0.1544 hm2,近20年間,人均生態承載力下降44.76%。人均生態承載力在2007年以前一直呈下降態勢,2007—2013年間有很小幅度的微量上升,這與人口數量的變化有關,珠海市近20年常住人口數量持續增長,20年間增長1倍多,但2006年后總生態承載力的增長速率大于人口增長速率,故2007年后人均生態承載力轉為緩慢上升。

圖2 1993—2013年珠海市與全國、全球人均生態承載力比較
與全國、全球人均生態承載力比較,發現珠海市人均生態承載力處于較低位置,遠遠低于全國和全球水平,說明珠海市具有城市生態環境的特點,即生態承載力較弱。
2.2 1993—2013年珠海市生態足跡變化
由圖3可見,1993—2003年珠海市生態足跡持續動態提高,2003年達到了最大值、為752 688.0249 hm2,之后逐年減少,偶有回升,但總體下行,2013年降至630 081.1731 hm2,比2003年減少16.29%。生態足跡的組成中,化石能源地和建成地占較大比例,其次是可耕地和森林草地,水域的比例最小,具有典型城市生態足跡的特征。2003年前,珠海市生態足跡波動居高的原因在于經濟發展的需要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會消耗的化石能源量大大增加。后期由于珠海市政府比較重視生態環保問題,特別是近些年來連續確立一系列有關科學發展的措施,2002年全面推廣使用汽油、柴油清凈劑,成為廣東省首個使用環保節能汽油、柴油的試點城市,并啟動“生態家園”十年植樹工程,建設“城市森林”;大力推進高產、優質、低耗的新型工業化,在2003年積極實施“環境強市”戰略,由于城市環境綜合整治進展順利,被評為“國際改善人居環境最佳范例獎”[22]。珠海市的一系列生態建設動作,體現在2003年之后,化石能源地和建成地的生態足跡開始減少,并影響總生態足跡的減少;而由于近年來經濟發展迅速,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生活消費需求也有所改變,對動物類食品的需求提高到一定程度后趨于穩定,體現在草地生態足跡先增加后穩定。上述主要生態足跡結構變化趨勢及其變化因素決定了2003年后珠海市生態足跡呈現下降趨勢。

圖3 1993—2013年珠海市生態足跡組成
由圖4可知,1993—2013年珠海市人均生態足跡總體呈現下降趨勢,1993年為0.6496 hm2,上升至1994年為0.7138 hm2,之后幾年呈下降趨勢,偶有回升但起伏不大,2012年下降到最低為0.3961 hm2。說明在經濟發展的同時,珠海市對資源的消耗逐漸減少,或者是對其利用率得到了提高,城市人民的生產消費習慣逐漸改變,人均資源的消耗逐漸減少,珠海市的整體生態文明素質得到提高。同時通過對珠海市人口的數據分析可得,珠海市的人口數量逐年增長,但總生態足跡保持在一定范圍內波動,故人均生態足跡呈下降趨勢。

圖4 1993—2013年珠海市與全國、全球人均生態足跡比較
與全國、全球同期人均生態足跡比較發現,珠海市的人均生態足跡處于較低位置,遠遠低于全國和全球平均水平。說明珠海城市的發展屬于對資源低消耗的類型,或珠海市對環境資源的利用率較高。近20年間,珠海市注重生態發展,升級改造傳統行業,實施清潔生產,嚴格控制產業類型及其開發強度,使得整個生態環境大大改善,城市生態發展較好。珠海城市的發展,對資源的消耗較低,對生態環境的依賴較小。
2.3 1993—2013年珠海市生態盈虧變化
根據珠海市1993—2013年的生態承載力和生態足跡,計算得到該市生態盈虧均為負數,即表現為生態赤字(圖5)。由圖5可知,珠海市1993—2013年的生態承載力先降后升,生態足跡則先升后降,生態盈虧表現為赤字,也呈現先升后降的趨勢。說明珠海市總體的生態承載力在下降一段時間后,開始緩慢回升,環境朝著好的方向改變,但總的生態足跡波動變化,說明珠海城市發展對環境資源的消耗隨著時間有不同變化。

圖5 1993—2013年珠海市生態承載力、生態足跡及生態盈虧變化
由圖6可見,珠海市1993—2013年的人均生態承載力和人均生態足跡均呈現下降趨勢,并且由于人均生態足跡下降幅度更大,故人均生態赤字呈現縮小趨勢。人均生態足跡的下降,說明珠海市對環境資源的人均消耗減少,顯示了城市不斷朝著綠色、可持續方向發展。根據生態赤字區的劃分[23],珠海市的生態盈虧皆處于輕度生態赤字區(0.1<ED≤0.5)。說明珠海市的生態赤字比較輕微,且有逐漸減少的趨勢,生態環境趨向于不斷改善。

圖6 1993—2013年珠海市人均生態承載力、人均生態足跡及人均生態盈虧變化
2.4 生態赤字趨勢預測
根據珠海市1993—2013年生態赤字數據,使用最小二乘法得到生態赤字趨勢公式:y =0.0085x - 17.343,經計算,約到2040年,珠海市能消除赤字,實現生態平衡,并朝生態盈余方向發展。

圖7 1993—2013年珠海市人均生態赤字變化趨勢
3 結論與討論
珠海市自建立經濟特區后,不斷摸索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之間的平衡點,圍繞城市、經濟與生態三大核心要素建設生態型城市。近年來,通過對原有產業進行生態化改造,嚴格限制高污染、高消耗類型產業及其開發強度,大力發展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的項目,減少資源環境的消耗和污染物排放,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從而推動城市發展,走出一條特色鮮明的可持續發展道路。
本研究發現,珠海市具備城市生態生態承載力較低的特點,1993—2013年的人均生態承載力出現總體下降的趨勢,說明隨著人口翻倍增加,人均生態承載力迅速減少,人口增長對環境資源的消耗增大。而后期由于珠海市注重城市生態建設,使得生態承載力在下降一段時間后緩慢回升,2003年后,生態承載力增加速度超過人口增長速度,人均生態承載力也稍微回升。
珠海市生態足跡則遠遠低于全國和全球水平,以2003年為界,前10年珠海市生態足跡持續動態提高,2003年達到了最高值之后逐年減少,至2013年比2003年減少16.29%,大致形成一條先升后降的曲線。說明珠海市從2003年之后對于生態環境與經濟之間的關系進行了調整,在發展經濟的同時減少生態足跡的產生,逐步向可持續發展轉變。人均生態足跡則持續波動下降,且下降幅度較大,人均生態足跡的下降說明珠海市對環境資源的人均消耗減少,顯示了城市人民生態文明素質不斷提高。
珠海市近20年的生態盈虧皆處于赤字狀態,人均生態赤字在0.2428~0.4484 hm2之間波動,處于輕度生態赤字區,這20年間雖然有波動,但總體呈現逐漸減少的趨勢,說明珠海市的生態赤字比較輕微,且逐漸減少,城市生態環境趨向不斷改善。根據生態赤字曲線趨勢計算,生態赤字預計在2040年完全消除,城市生態實現平衡發展。
參考文獻:
[1]William E R.Ecological footprints and appropriated carrying capacity :what urban economics leaves out[J].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1992,4(2):121-130.
[2]Wackernagel M,William E R.Our ecological footprint:Reducing human impact on the earth[M].Gabriola Island,New Society Publishers,1996
[3]Rees W,Wackernagel M.Urban ecological footprints:why cities cannot be sustainable and they are a key to sustainability[J].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Review,1996,16(4/6):223-248.
[4]謝鴻宇,王羚酈,陳賢生.生態足跡評價模型的改進與應用[M].廣州:化學工業出版社,2008.
[5]劉某承.中國生態足跡的時間動態與空間格局[M].北京:化學工業出版社,2014.
[6]Haberl H,Erb K H,Krausmann F.How to calculate and interpret ecological footprints for long periods of time:the case of Australia 1926-1995[J].Ecological Economics,2001,38(1):25-45.
[7]Bagliani M,Galli A,Niccolucci V,et al.Ecological footprints analysis applied to a subnational Area:the case of the Province of Siena(Italy)[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2008,86(2):354-364.
[8]馬彩虹,趙晶.基于足跡家族的青海省資源環境壓力定量評估[J].應用生態學報,2016,27(4):1248-1256.
[9]楊屹,加濤.21世紀以來陜西生態足跡和承載力變化[J].生態學報,2015,35(24):7987-7997.
[10]卞子浩,趙永華,王曉峰,等.陜西省生態足跡及其驅動力[J].生態學雜志,2016,35(5):1316-1322.
[11]余勇,舒建英.1997—2004年四川省生態足跡動態變化研究[J].安徽農業科學,2007,35(29):9318-9319.
[12]姬艷梅,王小文,梁寶翠,等.陜北地區土地利用與生態承載力動態變化分析[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1,21(S1):271-274.
[13]陳東景,徐中民,程國棟,等.中國西北地區的生態足跡[J].冰川凍土,2001,23(2):164-169.
[14]王娜.基于生態足跡的城市容量分析—— 以珠海市為例[J].陜西林業科技,2007,(1):26-30.
[15]李輝,闞興龍.珠海市生態足跡動態演變與生態經濟系統評估[J].資源開發與市場,2014,30(11):1329-1304.
[16]陳棟為,陳曉宏,孔蘭.基于生態足跡法的區域水資源生態承載力計算與評價—— 以珠海市為例[J].生態環境學報,2009,18(6):2224-2229.
[17]李翔,舒儉民.改良生態足跡法在珠海的應用[J].環境科學研究,2007,20(3):148-151.
[18]珠海市統計局公眾網[EB/OL].http://www.stats-zh.gov.cn/tjsj/tjnj/.2016-12-15.
[19]曹淑艷,謝高地,陳文輝,等.中國主要農產品生產的生態足跡研究[J].自然資源學報,2014,29(8):1336-1344.
[20]周濤,王云鵬,龔健周,等.生態足跡的模型修正與方法改進[J].生態學報,2015,35(14):4592-4603.
[21]全球生態足跡網[EB/OL].http://www.footprintnetwork.org/public data,2016-12-16.
[22]楊晶,金晶,吳泗宗.珠三角地區城市化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的動態耦合分析—— 以珠海市為例[J].地域研究與開發,2013,32(5):105-108.
[23]謝高地,魯春霞,甄霖,等.生態赤字下非再生資源對生態空間的替代作用[J].資源科學,2006,28(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