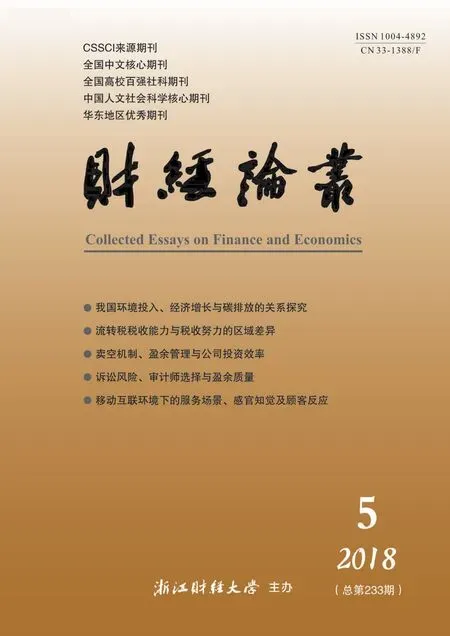賣空機制、盈余管理與公司投資效率
袁 鯤,武梓楊
(廣東財經大學金融學院,廣東 廣州 510320)
一、引 言
隨著我國股票市場制度的不斷完善,證券監管部門開始引入以融券業務為主要內容的賣空機制。2010年3月我國資本市場正式放開賣空管制,投資者可以對市場上90只股票進行融券賣空,這標志著我國單邊交易市場的正式結束。隨后,可賣空的標的股票數量不斷擴大,從2010年至2014年底,在經歷四次擴容之后,可賣空標的股票數量達到900只。融券業務彌補了我國證券信用交易體制的空白,使得投資者不僅可以在股價上漲中獲利,也可以受益于股價下跌。
企業投資決策深受信息不對稱和代理問題等因素的困擾。在信息不對稱與代理問題突出的企業中,管理層在制定投資決策時首先考慮的是自身利益,投資決策往往與公司價值最大化目標相違背。賣空機制的引入,市場多方和空方兩類投資者相互較量,對公司管理者行為形成積極的外部約束。作為一種外部的市場監督,賣空機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公司的盈余管理,從而進一步提高公司的投資效率。
在獲利動機的驅使下,專業的賣空投資者擁有比其他外部投資者更敏捷的洞察力,更容易發現財務狀況存在問題的公司,特別是那些嚴重盈余管理的公司,進而選定這些公司作為賣空操作的標的。賣空力量加大后,公司股價隨之大幅下降,導致管理層的預期收益嚴重受損,對管理層的盈余管理行為起到一定的懲罰效用。正因為如此,賣空機制有助于提高公司會計信息質量,緩解公司與外部投資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
放松賣空管制之后,對于業績不好的公司,即使管理層為了實現利潤目標積極進行盈余管理,公司股價也會更及時融入負面消息。賣空機制對于公司利空消息的這種價格發現功能,使得問題公司的股價大幅下跌,嚴重損害中小投資者,甚至是控股股東的利益,促使公司股東實施對管理層的有效監督,有助于緩解公司股東和管理層之間的代理問題,減少管理層投資過度、撇脂等機會主義行為。
本文的主要貢獻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影響投資效率的因素有很多,如管理層權利、會計穩健性、融資約束等,本文試圖從賣空機制這樣一個新視角研究融券業務引入對公司投資效率的影響;第二,如果賣空機制對公司投資效率產生了影響,那么其內在的生成機理是什么?本文探討了賣空機制影響公司投資效率的盈余管理渠道,豐富了賣空機制對公司微觀行為影響的相關文獻;第三,賣空機制有可能對公司管理層行為形成剛性的外部約束,本文探討了賣空機制與公司內部治理對于提高公司投資效率的相互替代效應。
二、 文獻綜述與研究假設
(一)賣空機制與盈余管理
投資者對股票內在價值的認識往往存在異質信念,但因賣空機制的缺位,股票價格主要反映了樂觀投資者的情緒,而悲觀投資者的情緒無法充分反映到股價中,最終導致股票價格的高估。Miller(1977)、Desai 等(2002)等基于美國股票市場的研究表明,賣空約束水平較高的公司,其股票的異常收益顯著為正[1][2]。Bris 等(2007)基于46個國家證券市場數據,發現在允許賣空或者賣空約束條件較少的國家,負面信息能夠更快地反映在股票價格中,而在賣空約束程度較高或者限制賣空的國家,股票價格更多的情況下被高估[3]。李科等(2014)利用自然實驗研究了賣空管制對中國股票市場的影響,發現放松賣空管制可以抑制過度虛高的股價,從而提高市場的定價效率[4]。
股票定價效率的提高得益于賣空投資者對利益的追逐。大量研究表明,賣空投資者通過挖掘各種被公司隱藏的不利信息,如業績虧損、盈余重述、財務丑聞、信用評級下降等,早于其他外部投資者賣空公司股票,從下跌的股價中獲取收益[5][6][7]。Karpoff(2010)發現,在賣空相對自由的美國資本市場,“壞消息”公布前19個月公司被賣空的頭寸就會顯著上升,并且“壞消息”越嚴重,公司被賣空頭寸越多。從這個角度來看,賣空投資者的行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預測公司經營狀況和公司股價未來走勢的能力[8]。
賣空機制可以降低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客觀上會對公司治理產生重大影響。由于投資者的賣空行為,公司管理層進行盈余操縱時將受到嚴重的市場懲罰。Massa 等(2013)、Fang 等(2016)等發現賣空行為引起的股價下跌導致管理層利益受損的程度遠遠大于法律法規對管理層的處罰程度。放松賣空管制之后,在市場懲罰和股東監管的雙重作用下,財務舞弊的公司被發現的概率大大增加,盈余管理風險加大,管理層在權衡利弊后會弱化盈余操縱的動機,公司的盈余質量隨之提高[9][10]。陳暉麗和劉峰(2014)發現,融資融券具有治理效應,即融資融券對盈余管理存在顯著的約束作用[11]。由此,提出以下假設:
H1:放松賣空管制可以抑制公司的盈余管理。
(二)盈余管理與投資效率
企業的盈余管理行為降低了企業會計信息質量,加劇了企業與投資者之間以及股東與管理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資本市場摩擦變得更為嚴重,企業的投資效率也隨之降低。Leuz 和 Verrecchia(2000)、Bushman 和 Smith(2001)等發現,高質量的會計信息,通過提高公司資產的流動性有效緩解了投資不足[12][13]。Biddle 和 Hilary(2006)、Biddle 等(2009)、Beatty 等(2010)等發現財務信息質量與公司的投資效率顯著正相關,財務信息質量越高,投資現金流敏感性越低,公司面臨的融資約束越小[14][15][16]。
高質量的財務信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緩解管理層和股東之間的代理問題,對管理層的過度投資行為進行約束。企業股東與管理層之間委托代理問題的存在,有可能促使管理層基于帝國構建行為,對凈現值小于零的項目進行投資,以獲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17][18]。Hope 和 Thomas(2008)發現高質量財務信息及時披露的一個重要功能是為股東提供監控管理者操縱盈余的依據,從而緩解企業的過度投資[19]。周春梅(2009)、劉慧龍等(2014)研究結果表明,在企業代理問題嚴重的情況下,盈余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公司的投資效率,而盈余質量的改善能夠通過降低代理成本間接促進上市公司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20][21]。
綜上所述,放松賣空管制之后,投資者可以通過做空標的股票表達對標的公司不看好的意愿。一旦投資者發現公司存在較為嚴重的盈余操縱行為,他們會選擇賣空股票導致股價下跌,也正是股票下跌反過來約束了管理層的自利行為,盈余管理水平得以降低。在此基礎上,本文認為,放松賣空管制之后,一方面,隨著公司盈余管理水平的降低與會計信息質量的提高,有助于外部投資者了解公司的財務狀況和盈利能力,減少投資者與公司之間的信息不對稱,降低公司的融資成本,緩解公司的投資不足;另一方面,問題公司股價大幅下跌損害了股東的利益,促使公司股東實施對管理層的有效監督,有助于緩和股東與管理層之間的代理沖突,抑制公司的過度投資。由此,提出以下假設:
H2:放松賣空管制可以提高公司的投資效率。
H3:盈余管理水平是賣空機制影響投資效率的中介變量。
(三)公司治理質量與投資效率
在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背景下,股東與管理層、大股東與小股東之間的利益分歧往往導致管理層進行非效率投資決策[22][23]。大量文獻也表明公司治理水平越高,其投資效率也越高。Aggarwal和 Samwick(2006)、Richardson(2006)等發現完善的公司治理機制能夠提高公司的投資效率,如有效的薪資激勵措施、較高比例的外部董事與機構投資者持股等[24][25]。張會麗和陸正飛(2012)發現完善的公司治理機制能夠顯著降低子公司過度持現所導致的效率損失[26]。方紅星和金玉娜(2014)將非效率投資劃分為意愿性非效率投資和操作性非效率投資,發現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能夠明顯抑制公司的意愿性非效率投資[27]。
以上分析表明,賣空機制與公司治理水平之間可能存在相互替代效應。因此,當考察賣空機制對公司投資效率的影響時,必須考慮公司治理水平的異質性。也就是說,如果公司治理機制較為完善,其本身的投資效率就很高,賣空機制對其投資效率的影響可能并不明顯;相反,如果公司治理水平較低,賣空機制對投資效率的影響可能會較為顯著。由此,提出以下假設:
H4:相對于公司治理水平較高的公司,放松賣空管制對治理水平較低公司的投資效率影響更為顯著。
三、變量選擇與實證模型
(一)變量選擇
1.投資效率
本文借鑒Richardson(2006)、劉慧龍等(2015)估計投資效率[25][21],如式(1),用該模型殘差的絕對值表示投資效率:
Investi,t=α0+α1Investi,t-1+α2Levi,t-1+α3Cashi,t-1+α4Sizei,t-1+α5Returni,t-1+
α6Growthi,t-1+α7Agei,t-1+εi,t
(1)
其中,Invest表示新增投資,即(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其他長期資產所支付的現金-處置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其他資產所收到的現金凈額)/總資產;Lev表示資產負債率;Cash為(貨幣資金+交易性金融資產)/總資產;Size表示公司規模,對總資產取對數;Return表示復權之后的年度股票收益率;Growth表示公司的投資機會,用營業收入增長率表示;Age為公司上市年齡的對數值。
分行業、分年度對式(1)回歸,得到的殘差如果大于零,表明公司過度投資;如果小于零,表明公司投資不足。對殘差取絕對值表示非效率投資的程度,記為Absinvest,其值越大,表示公司的投資效率越低。
2.盈余管理水平
本文參考陳暉麗和劉峰(2014)、Kothari 等(2005)等經上年度業績調整修正的Jones模型估計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11][28],具體模型如下:
(2)
其中,TA表示總應計利潤,即營業利潤-經營活動現金凈流量;A表示公司總資產;dREV表示公司本年度與上年度主營業務收入的差額;dREC表示公司本年度與上年度應收賬款的差額;PPE表示公司固定資產總額,即固定資產凈額+工程物資+在建工程+固定資產清理。
分行業、分年度對式(2)回歸,如果得到的殘差大于零,表明公司存在向上的應計項目盈余管理;如果小于零,表明公司存在向下的應計項目盈余管理。對殘差取絕對值,記為Absda,表示盈余管理程度,其值越大,盈余管理程度越高。
3.公司治理質量
參考方紅星和金玉娜(2013),從激勵、監督及控股權性質等方面選取表征公司治理質量的指標[27],分別是:第二大至第十大股東持股集中度(Top10);監事會規模(Nsuper);董事會規模(Nboard);董事會持股比例(Rboard);監事持股比例(Rsuper);高管持股比例(Rgg);機構持股比例(Rjg);是否發行B股或H股啞變量ABH,發行則ABH取1,否則取0;總經理和董事長是否合一啞變量JD,若合一取1,否則取0;控股權性質啞變量CS,若為國有控股,則CS取1,否則取0。進一步參考白重恩等(2005)、張會麗和陸正飛(2012)等,對上述十個指標進行主成分分析[29][26],根據主成分對應的特征值大小或對總方差的貢獻度,選取前三大主成分,按照其在總方差中的權重構建一個綜合指標,作為公司治理質量的代理指標Govern。Govern值越大,說明公司治理水平越高。
4.其它控制變量
進一步直接控制影響投資效率的公司特征變量,分別是第二大到第十大股東持股集中度(Top10)、獨立董事比例(Indir)、董事會規模(Nboard)等3個公司治理指標和自由現金流量(FCF)、銷售收入增長率(Growth)、總資產周轉率(ATR)、公司規模(Size)、財務杠桿(Lev)等5個財務特征指標。
(二)實證模型
1.賣空機制與投資效率模型。借鑒褚劍和方軍雄(2016),針對假設1運用雙重差分模型[30],如式(3):
Absinvesti,t=α0+α1Shorti+α2Shorti*Posti,t+∑controlvariablesi,t+εi,t
(3)
其中,Short表示可賣空股票的啞變量,即進入融資融券標的名單的股票,如果是,則為1,否則為0;Short*Post表示可賣空股票進入融資融券標的名單之后的啞變量,如果是,則為1,否則為0。根據雙重差分模型,式(3)Short試圖控制可賣空股票與不可賣空股票之間的個體差異。如果放松賣空管制提高了公司的投資效率,則預期Short*Post的系數α2顯著為負。
2.盈余管理渠道存在性檢驗的中介效應模型。借鑒程新生等(2012)、溫忠麟等(2004),對假設2進行檢驗[31][32],如式(4)、(5)、(6)所示:
Absdai,t=χ0+χ1Shorti+χ2Shorti*Posti,t+∑controlvariablesi,t+εi,t
(4)
Absinvesti,t=β0+β1Absdai,t+∑controlvariablesi,t+εi,t
(5)
Absinvesti,t=α0+α1Shorti+α2Shorti*Posti,t+β1Absdai,t+∑controlvariablesi,t+εi,t
(6)
其中,式(4)用于檢驗賣空機制是否降低了公司的盈余管理,如果是,可以預期Short*Post系數χ2顯著小于0;式(5)用于檢驗盈余管理對公司投資效率的影響,公司盈余管理水平越高,可以預期公司非效率投資程度越大,Absda的系數β1顯著為正;式(6)同時將賣空機制啞變量Short*Post及盈余管理變量Absda引入投資效率方程中。如果盈余管理水平是賣空機制對公司投資效率影響的中介變量,可以預計,式(4)雙重差分項Short*Post系數χ2顯著為負,同時式(5)Absda系數β1顯著為正。
在此基礎上,可以進一步推斷,如果式(6)中Short*Post系數α2仍然顯著為負,則說明盈余管理水平不是賣空機制對公司投資效率影響的完全中介變量;若Short*Post系數α2不再顯著,則說明盈余管理水平是賣空機制對公司投資效率影響的完全中介變量。
3.公司治理水平對賣空機制異質性影響的檢驗。借鑒靳慶魯等(2015)對假設4進行檢驗[33],如式(7)所示:
Absinvesti,t=α0+α1Shorti+α2Shorti*Posti,t+α3DGi,t*Shorti*Posti,t+
∑controlvariablesi,t+εi,t
(7)
其中,DG為表征公司治理質量的啞變量,如果公司治理水平低于當年度樣本公司治理水平均值,則DG=1,表明公司治理水平較低;若高于當年度樣本公司治理水平均值,則DG=0,表明公司治理水平較高。如果假設4成立,即相對于公司治理水平較高的公司,放松賣空管制對治理水平較低公司投資效率的影響較明顯,可以預期三重差分項的系數α3顯著為負。
四、實證檢驗及結果分析
(一)數據來源
自2010年3月31日融資融券制度正式在我國啟動,經歷了五年內的四次大規模擴容,截至2015年12月31日,可融資融券的標的股票由最初的90只擴增到900只,目前已達到上市公司總量的近三分之一。具體情況如表1所示。

表1 我國融資融券交易標的股票擴容情況
融資融券候選標的股票必須符合滬深兩個交易所《融資融券交易實施細則》中標的股票的規定條件,并按照加權評價指標從大到小排序。這些條件包括上市期限、流通市值、股東人數、換手率、漲跌幅、波動性等方面,加權評價指標包括流通市值與成交金額兩個指標。總之,滿足以上條件的股票具有規模大、流動性好、波動性較小、交易正常等特點。
為了使得樣本數據具有代表性,本文選取2006年12月3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所有A股上市公司為樣本,將在此期間進入融資融券名單的滬、深A股作為實驗組,未進入該名單的滬、深A股作為控制組。由于投資效率和盈余管理代理變量計算的需要,實際樣本期間為2007年12月3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根據慣例,剔除ST、金融行業、資產負債率超過100%及資產增長率超過100%的公司(后者可能經歷了較大規模的并購),最終得到1744家樣本公司,其中融資融券標的公司642家。為了避免異常值的影響,對所有連續變量按照1%的標準進行了Winsor縮尾處理。本文數據來自CSMAR數據庫和WIND數據庫,融資融券各批次公司名單分別來自滬深交易所網站。
(二)主要變量描述性統計分析
表2為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從表2中可以看出,樣本A股公司的平均非效率投資程度Absinvest為0.139,標準差為0.166;盈余管理水平Absda的平均數為0.075,標準差為0.078,由此推測樣本公司的投資效率與盈余管理水平均存在較大差異。進一步按照是否可賣空進行分組,可以賣空樣本數量為3913,不可賣空樣本數量為5162,虛擬變量Short的平均數為0.431。本文所關注的是,除了規模Size之外,兩組樣本大部分變量的統計量沒有顯著的差異,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文未提供分組統計。這一方面印證了融資融券樣本的選擇標準,即以流通市值與成交金額為主要的納入條件;另一方面,由于兩組股票的Absinvest與Absda事前并不存在明顯的差異,可以推斷在后文計量分析中,啞變量Short并不顯著。

表2 主要變量描述性統計(N=9075)
(三)實證結果
公司之間可能存在不隨時間而變的個體效應,且Hausman檢驗均以1%的水平拒絕了不可觀測因素是隨機效應的原假設,對式(3)、(4)采用固定效應模型,估計結果如表3。表3模型(1)、(4)只包含雙重差分變量;模型(2)、(5)與模型(3)、(6)的區別在于后者控制了年度與行業效應。
從表3中可以看出,在模型(1)~(3)中,雙重差分變量Short*Post均在0.01的水平下顯著為負,在控制年度效應和行業效應之后,主要變量Short*Post的系數為-0.0245。這說明,放松賣空管制可以抑制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與假設H1相符。同時,在模型(4)~(6)中,雙重差分變量Short*Post在0.05的水平下均顯著為負,這表明,放松賣空管制在一定程度上約束了公司管理層的投資行為,緩解了過度投資或投資不足,與假設H2相符。
以上分析不僅驗證了陳暉麗和劉峰(2014)的研究結論[11],即融資融券制度具有公司治理效應,而且也初步揭示了可能存在的放松賣空管制提高投資效率的盈余管理渠道效應,即盈余管理水平是賣空機制影響投資效率的中間變量。
為了進一步證明放松賣空管制提高投資效率的盈余管理渠道效應,同樣采用固定效應模型對式(5)、(6)進行檢驗,結果如表4模型(1)~(4)。模型(1)、(2)中Absda系數顯著為正,說明盈余管理水平越高的公司,非效率投資程度越大。這表明,引入賣空機制可以降低企業的盈余管理水平,從而進一步緩解企業的非效率投資程度。那么,盈余管理的這種中介效應是否是賣空機制緩解企業非效率投資的唯一渠道?同時將盈余管理水平Absda和賣空機制交乘項Short*Post引入非效率投資方程式(6)中,得到表4模型(3)、(4)。以模型(4)為例,盈余管理水平Absda的系數在0.05的水平下顯著為正,即0.0292;同時賣空機制交乘項Short*Post系數在0.05的水平下顯著為負,即-0.0114,表明盈余管理水平是賣空機制與公司投資效率之間的中間變量,但可能還存在賣空機制緩解公司非投資效率的其他渠道。上述結果支持了假設H3,而且也說明盈余管理渠道在賣空機制緩解公司非效率投資過程中僅僅承擔了部分中介效應。
為了驗證假設H4,對式(7)進行檢驗,主要考察公司治理水平與賣空機制之間是否存在相互替代效應,采用固定效應模型進行估計,結果如表4中模型(5)~(6)。與假設4預期一致的是,交乘項Post*Short*DG系數在0.01的水平下均顯著為負,其中模型(6)中該變量的系數為-0.0168,這表明,相對于公司治理水平較高的公司,放松賣空管制對于公司治理水平較低公司的投資效率影響更大,假設H4得到了驗證。

表3 放松賣空管制對投資效率與盈余管理的影響(N=9075)
注:括號內為在公司層面 cluster 采用 robust 估計的標準誤;*** 、** 、*分別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顯著。

表4 放松賣空管制的盈余管理中介效應檢驗(N=9075)
續表

變量Abinvest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模型(5)模型(6)Top10-05790???-05867???-05679???(01689)(01698)(01704)Size-00062-00049-00035(00069)(00069)(00071)Lev-01868-01869-01862(01464)(01464)(01465)FCF-00007-00006-00004(00008)(00008)(00008)Indir-01348??-01326??-01323??(00586)(00582)(00582)Nboard-00027-00026-00028(00021)(00021)(00021)Growth-00024-00026-00022(00053)(00052)(00054)ATR000680006800125(00089)(00089)(00090)Constant01364???04505??01722???04228??01759???03908??(00012)(01814)(00014)(01792)(00009)(01795)年度NYNYNY行業NYNYNYAdj.R2000310594101146059440113405937
注:括號內為在公司層面 cluster 采用 robust 估計的標準誤;*** 、** 、*分別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顯著。
(四)穩健性分析
為了測試研究結果的穩健性,進行如下檢驗:(1)雙重差分的平行趨勢假設檢驗。盈余管理水平與融資融券標的股票納入的主要遴選標準——成交金額、換手率、流通市值之間均不存在顯著的相關性;投資效率與成交金額不存在顯著的相關性,與換手率、總市值之間雖存在相關性,但是其符號相反。此外,以第一批納入的融資融券標的股票與從未納入的非融資融券標的股票構建測試樣本,實證表明,樣本調整前兩類股票的投資效率沒有顯著的差異。(2)對于融資融券樣本調整事件年度,設置啞變量Post=0。(3)去掉融資融券事件年度的當年數據。(4)關于式(1)、(2)中投資效率與盈余管理水平估計,控制年度與行業效應。(5)由于融資融券前處理組與控制組之間的公司特征存在一定的差異,這些差異可能會造成處理組和控制組存在明顯的差異,從而降低雙重差分模型估計的有效性。為此,采用傾向性評分匹配PSM方法構建一對一配對樣本。具體程序如下:針對每一家可賣空公司——處理組公司,按照流通市值占比、成交金額占比、公司年齡、年份和行業等指標,運用logistic回歸得到每個觀察值的傾向性得分,在不可賣空公司——控制組公司中選取一家配對公司。(6)為了控制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在選取配對公司時進一步考慮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選擇與處理組公司進入可賣空標的名單前盈余管理程度最接近的控制組公司作為配對公司進行檢驗。上述穩健性測試結果顯示,本文研究結論依然成立。
五、結 論
針對我國證券市場引入融資融券交易制度這一特殊的自然實驗,本文基于2006~2015年A股市場數據,通過建立雙重差分模型比較可賣空公司與不可賣空公司以及可賣空公司賣空時點前后的投資效率,研究了賣空機制對公司投資效率的影響及其傳導機制。本文發現,賣空機制抑制了公司管理層的盈余管理行為;會計信息質量的提高,有助于緩解公司所面臨的信息不對稱與委托代理問題,進而提高公司的投資效率。本文認為,賣空機制通過抑制公司的盈余管理行為提高了公司的投資效率,但盈余管理僅僅在賣空機制緩解公司非效率投資過程中承擔了部分中介效應,還可能存在賣空機制緩解公司非投資效率的其他渠道。此外,相對于公司治理水平較高的公司,放松賣空管制對于公司治理水平較低公司的投資效率影響較大。因此,本文也認為,公司治理質量與賣空機制之間存在替代效應。
參考文獻:
[1] Miller E. Risk, Uncertainty, and Divergence of Opinion[J]. Journal of Finance, 1977,32 (4),pp.1151-1168.
[2] Desai H.K., Ramesh S., Thiagarajan R., Balachandran B. V.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Information Role of Short Interest in the Nasdaq Market[J]. Journal of Finance, 2002, 57(5),pp. 2263-2287.
[3] Bris A., Goetzmann W., Zhu N. Efficiency and the Bear: Short Sales and Markets Around the World[J]. Journal of Finance, 2007, 62(3),pp.1029-1079.
[4] 李科,徐龍炳,朱偉燁. 賣空限制與股票錯誤定價——融資融券制度的證據[J]. 經濟研究,2014,(10):165-178.
[5] Diamond D. W., Verrecchina R. E. Constraints on Short Selling and Asset Price Adjustment to Private Information[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87,18(2),pp.277-311.
[6] Akbas F., Boehmer E., Erturk B., Sorescu S. Don’t Shoot the Messenger: Short Interest, Returns, and Fundamental[Z]. Working Paper, Availble at SSRN: http://ssrn.com/abstract=2216919,2010.
[7] Hirshleifer D., Teoh S. H., Yu J. J. Short Arbitrage, Return Asymmetry, and the Accrual Anomaly[J].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11,24(7),pp.2429-2461.
[8] Karpoff J. M. , Lou X. Short Sellers and Financial Misconduct[J]. Journal of Finance, 2010,65(5),pp.1879-1913.
[9] Massa M., Zhang B., Zhang H. The Invisible Hand of Short Selling: Does Short Selling Discipline Earnings Manipulation[J].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13,28(6),pp.1701-1736.
[10] Fang V. W., Huang A., Karpoff J. Short Selling and Earnings Management: A Controlled Experiment[J]. Journal of Finance, 2016,71(3),pp.1251-1294.
[11] 陳暉麗,劉峰. 融資融券的治理效應研究——基于公司盈余管理的視角[J]. 會計研究,2014,(9):45-52.
[12] Leuz C., Verrecchia R.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Increased Disclosure[J]. Journal of Accouting Research, 2000,38(5),pp.91-124.
[13] Bushman R. M.,Smith A. J. Financial Accounting Information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01,32(1/3),pp.237-333.
[14] Biddle G., Hilary G. Accounting Quality and Firm Level Capital Investment[J].The Accounting Review, 2006,81(5),pp.963-982.
[15] Biddle G. , Hilary G., Verdi R. How does Financial Reporting Quality Relate to Investment Efficiency?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09,48(2/3),pp.112-131.
[16] Beatty A., Liao S.,Weber J. The Effect of Private Information and Monitoring on the Role of Accounting Quality in Investment Decisions[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2010,27(1),pp.17-47.
[17] Jensen M. C., Meckling W.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J]. Journal of Finance Economics,1976, 3(4),pp.305-360.
[18] Jensen M. C.The Modern Industrial Revolution, Exit, and the Failure of Internal Control Systems[J]. Journal of Finance,1993,48(3),pp.831-880.
[19] Hope O., Thomas W.Managerial Empire Building and Firm Disclosure[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2008,46(3),pp.591-626.
[20] 周春梅. 盈余質量對資本配置效率的影響及作用機理[J]. 南開管理評論,2009,(5):109-117.
[21] 劉慧龍,王成方,吳聯生. 決策權配置、盈余管理與投資效率[J]. 經濟研究,2014,(8):93-106.
[22] Billett M. T., Garfinkel J. A., Jiang Y. The Influence of Governance on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a Hazard Model[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1,102(3),pp.643-670.
[23] Giroud X., Mueller H. Does Corporate Governance Matter in Competitive Industries[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0,95(3),pp.312-331.
[24] Aggarwal R. K., Samwick A. A. Empire Builders and Shirkers: Investment, Firm Performance, and Managerial Incentives[J].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2006,12(3),pp.489-515.
[25] Richardson S. Over-investment of Free Cash Flow[J].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2006,11(2),pp.159-189.
[26] 張會麗,陸正飛. 現金分布、公司治理與過度投資——基于我國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的現金持有狀況的考察[J]. 管理世界,2012,(3):141-150.
[27] 方紅星,金玉娜. 公司治理、內部控制與非效率投資:理論分析與經驗證據[J]. 會計研究,2013,(7):63-69.
[28] Kothari S. P., Leone A. J., Wasley C. E. Performance Matched Discretionary Accrual Measure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05 ,39(1),pp.163-197.
[29] 白重恩,劉俏,陸洲,等.中國上市公司治理結構的實證研究[J].經濟研究,2005,(2):81-91.
[30] 褚劍,方軍雄.中國式融資融券制度安排與股價崩盤風險的惡化[J].經濟研究, 2016, (5): 143-158.
[31] 程新生,譚有超,劉建梅. 非財務信息、外部融資與投資效率——基于外部制度約束的研究[J]. 管理世界,2012,(7):137-150.
[32] 溫忠麟,張雷,侯杰泰,等. 中介效應檢驗程序及其應用[J]. 心理學報,2004,(5):614-640.
[33] 靳慶魯,侯青川,李剛,等.放松賣空管制、公司投資決策與期權價值[J]. 經濟研究,2015, (10):7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