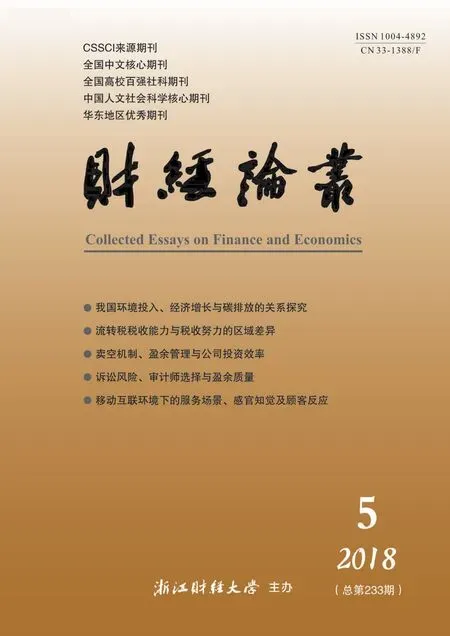基于扎根理論的科技人才流動阻滯因素及作用機理研究
——以企業與高校科技人才雙向流動為例
吳道友1,程佳琳2
(浙江財經大學工商管理學院,浙江 杭州 310018 )
一、引 言
科技人才是具有專業知識或專門技能,從事科學技術創新活動,承擔科技創新任務的主體[1]。科技人才的合理有序流動,對于人力資源與物質資源的優化配置,推動生產力的發展至關重要[2]。企業是培育創新產業的重要載體與構筑現代創新體系的中堅力量,高校是國家創新體系的主力軍,是開展科學研究的重要陣地[3]。促使企業與高校科技人才的雙向流動,有助于帶動彼此知識、信息與技術的交流,發揮企業與高校科技人才的雙向輻射作用,激發我國科技人才流動體系的活力[3]。
當前,我國科技人才的流動并不暢通,存在諸多阻滯因素[4]。作為科技人才集聚地的高校和作為創新主體的企業間,科技人才的交流互動還很不充分,仍然停留在參觀交流、科技特派、項目合作等較淺層次,阻滯企業與高校科技人才雙向流動的相關因素未得到根本改變[5],科技人才的作用未能得到充分發揮,這也直接影響到我國科技創新體系的建設。
對于是否流動,科技人才是在分析各種內外部限制條件下做出的最優抉擇。本文以企業與高校科技人才的雙向流動為例,通過扎根理論的研究方法,探究阻滯其流動的內外部因素,并分析其內在機理,從而為暢通企業與高校科技人才雙向合理流動提供借鑒。
二、文獻回顧
(一)企業科技人才流動研究
在企業科技人才流動方面,國內學者聚焦于探究影響企業科技人才流動的因素。紀建悅(2008)從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進行分析,得出R&D經費和新技術企業凈利潤是推動企業科技人才在企業間流動的重要因素[6]。其他學者則針對某一具體地區或省份進行分析,如汪志紅等(2016)基于珠三角854家企業數據,證實企業性質、企業規模和企業所處的產業都會對企業科技人才的流動意愿產生影響[7];楊敏(2015)以福建省291家企業科技人才為研究對象,提出在產業轉移背景下,影響企業科技人才流動的因素包括轉移產業聚集度、轉移產業成熟度、企業激勵機制等[8]。劉航(2008)以南京市企業科技人才為研究對象,表明了報酬、福利待遇、新鮮感、單位發展前景等都會影響企業科技人才的流動[9]。
國外關于企業科技人才流動的研究集中于探究企業科技人才流動的影響因素以及減少企業科技人才自愿流動的措施。Alferaih(2017)構建了人才流動的理論模型,其認為組織規范、工作滿意度、組織承諾、人才參與、外部獎勵都會對企業科技人才的流動意愿產生影響[10];Anton和Sonja(2016)通過實證檢驗了人——組織匹配,心理契約會對企業科技人才的自愿流動行為產生影響[11];Al-Sharafi 和 Rajiani(2013)提出了領導實踐會通過影響工作滿意度進而對企業科技人才的流動意愿產生影響[12]。Liu(2011)認為工作嵌入和工作不安全都會對企業科技人才的流動意愿產生影響[13]。美國學者主張建立學徒制或制定人力資源政策(福利和薪酬政策)以減少企業科技人才的自愿流動[14][15][16]。
(二)高校科技人才流動研究
國內有關高校科技人才流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流動現狀和影響因素兩方面。丹聆(2017)認為當前高校科技人才在高校間的流動不合理,一方面阻滯了經濟欠發達地區科研、教育和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導致了人才的高消費和人力資源的浪費[17]。同時,高校科技人才在行業間的流動缺乏統一、規范的政策法規以及健全的社會保障制度與暢通的流動渠道[18]。面對當前情況,一些學者建議政府應完善高校科技人才的內部培養機制以及制定有利于行業間人才流動的政策法規,高校應放眼世界延攬一流人才[18]。
柳冰(2014)將影響高校科技人才流動的因素劃分為個人因素(年齡、思想觀念、教育背景、需求、成就)、組織管理因素(物質要素、學術氛圍、人際關系、校園文化建設、相關政策支持)和社會經濟因素三大類[19]。其中年齡顯著影響高校科技人才的流動意愿,45歲以下的科技人才比45歲以上的科技人才更傾向于流動[3]。外部環境因素與組織因素對科技人才流動的影響具有強弱之分,高校科技人才對組織環境的滿意度會潛在影響流動意愿,但影響力顯著弱于外部環境(地區和城市)[20]。其他的研究也證實報酬、高校聲望、科研績效、性別、資歷等均會對高校科技人才的流動產生重要的影響[21][22]。
國外有關高校科技人才流動的研究較為分散,有的學者致力于探討影響高校科技人才流動的因素,如個人屬性、制度特征、工作環境、工作滿意度等對高校科技人才流動意愿的影響[23]。有的學者對個體特征進行了細化,重點探究了性別因素對高校科技人才流動意愿的影響,如Xu(2008)研究表明當女性科技人才對研究資助、發展空間、科研環境不滿意時更有可能產生流動意愿[24];Tolbert(1995)通過數據分析表明女性科技人才在高校中所占的比例達到35%~40%時,流動率開始下降[25]。Ehrenberg等(1990)通過對二十年數據的分析,呈現了當前美國高校科技人才跨學科流動的比率[26]。Daniels等(1984)致力于探討高校科技人才流動所產生的影響,其認為流動對科技人才自身和高校都具有積極與消極兩方面的影響[27]。
(三)對現有研究的述評
從現有文獻看:(1)多數關于科技人才流動的研究主要通過設計調查問卷的方式,對科技人才展開大樣本的實證調查。從研究結論看,影響企業與高校科技人才流動的因素主要集中在社會與組織環境方面。(2)專門研究企業與高校科技人才雙向流動的文獻還很少見,以往的研究多將企業科技人才與高校科技人才作為兩個獨立主體,有關企業與高校科技人才的雙向流動問題還有待探究。(3)關于科技人才雙向流動阻滯效應的形成機理,現有的文獻大多缺乏深入研究。多數研究側重于考慮各獨立變量對科技人才流動的影響,很少精確刻畫企業與高校科技人才雙向流動的阻滯因素及其作用機理。
本研究在國內外相關研究的基礎上,專門針對企業與高校科技人才雙向流動問題進行研究,基于扎根理論探索企業與高校科技人才雙向流動的阻滯因素和作用機理,以期為促進企業與高校科技人才在科技創新體系中合理流動提供參考。
三、研究方法和數據來源
關于企業與高校科技人才雙向流動的阻滯因素,目前學術界還沒有深入的研究,從而缺乏成熟的測量量表。鑒于此,本研究采用扎根理論探索阻滯企業與高校科技人才雙向流動的因素。首先,對原始資料進行開放式編碼;其次,進行主軸性編碼發現和建立概念類屬間的各種聯系;最后,進行選擇性編碼連接核心范疇與其他范疇類屬[28]。
一般而言,扎根理論研究要求受訪者對研究問題有一定的理解和認識,所以在訪談之前,先與訪談對象約定時間,告知訪談主題,之后再與其進行訪談。依據科技人才的定義,根據理論飽和準則,選擇浙江省27位科技人才作為受訪對象,其中包括16位企業科技人才和11位高校科技人才。受訪者中男性占總人數的70.3%,女性占總人數的29.7%;年齡分為30歲以下,30~40歲,40~50歲及50歲以上,分別占總受訪人數的14.8%,29.7%,48.1%和7.4%;學歷本科及以下占14.8%,碩士占29.6%,博士占55.6%;職業主要包括高校教師、企業研發人員、企業管理人員,分別占總受訪人數的40.7%,33.4%和25.9%;受訪對象的專業分為管理學、計算機科學、機械電氣工程、經濟學以及其他專業,分別占比37%,11.1%,11.1%,7.5%和3.3%。
對每位訪談對象進行了40~50分鐘的訪談,在受訪者同意的條件下,我們對訪談進行了錄音,之后對錄音文件進行系統性整理,形成8萬余字的訪談原始記錄。并隨機選擇20份訪談記錄,通過扎根理論這一探索性的技術進行開放式編碼、主軸編碼及選擇性編碼,另外7份訪談記錄則用于理論飽和度檢驗。整個編碼過程對企業與高校科技人才雙向流動的阻滯因素不斷進行提煉與更新,直至達到飽和狀態。
四、范疇提煉和模型建構
(一)開放式編碼
本研究在開放式編碼中將原始資料打散,賦予其概念,然后以新的方式對概念進行重組和命名[29]。整個開放性編碼由3人共同完成,通過將錄音轉化成文字,一共得到560條原始語句及相應的初始概念,并進一步背對背編碼對初始概念進行了范疇化,即圍繞企業與高校科技人才雙向流動的阻滯因素,對初始概念進行分類和組合。由于3人都參與編碼過程,其中產生的分歧點經過了反復討論。
本研究提取訪談資料中涉及的各種企業與高校科技人才流動的阻滯因素,細致分析相關資料,最終歸納出概念并提取范疇。雖然企業與高校科技人才的雙向流動因流動路徑不同可分為企業科技人才向高校流動和高校科技人才向企業流動兩條路徑。不同流動路徑阻滯因素雖存在差異,但是通過分析訪談資料發現,被訪談者提到次數最多的因素共同阻滯科技人才在兩條路徑上的流動,因此,本研究提取兩條路徑共有的阻滯因素。在進行范疇化時,我們選擇重復頻率在3次以上的初始概念,并對每個范疇節選3條初始概念,以節省文章篇幅。初始概念和若干范疇如表1所示。

表1 開放式編碼范疇化
續表

范疇原始語句(初始概念)轉換成本A04在一個高校待久了之后,你會對這個地方充滿感情,如果去到一個和原先的環境有很大差異的地方,情感上比較失落,所以就不愿意實施流動行為,流動也只是想想而已(情感成本)。A09自己以前在科研這個領域已經有很多積累和鋪墊了,重新進入企業的話,企業與高校的差異大,往往會損失目前所在崗位上的積累,而造成財務上的損失。比如說去新的環境要重新學習、從基層做起(財政成本)。A13因為當時的時候可以從零開始,現在我已經在我所從事的領域上,我自己已經有一些成績,那么我現在去做企業,我對這個社會的貢獻不如我們現在繼續從事下去,我繼續從事下去,也許會在我從事的領域,根據我自己這個天賦的話有個更好的發展(程序成本)。流動風險A10流動是有風險的,如果你去新的崗位上做不好,很有可能被辭退,而原來的單位又回不去了(辭退風險)。A11老師長期做科研對企業經營這塊并不是很懂,缺乏對經營企業和創業的基本知識,失敗率是很高的。而企業科技人才也是這樣啊,叫他們發文章,估計失敗率也很高(失敗風險)A16想到要連根拔起,變動到一個工作環境、工作地點、工作內容差異很大的地方,不適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就選擇放棄。(不適應風險)
注:A** 表示第** 位受訪者原話中的代表性語句;每句話末尾括號中的詞語表示對該原始語句進行編碼得到的初始概念。
(二)主軸編碼
本研究發現和建立開放式編碼中抽取出來的概念類屬之間的各種聯系,并圍繞此種聯系對概念類屬進行分類[30]。根據不同范疇在概念層次上的聯結與邏輯關系,對開放式編碼中得到的8個范疇進行歸類,經過反復思考后將個人保守觀念與家庭保守觀念聯結為傳統保守觀念;將心理惰性與壓力感知聯結為負向心理情境;將引進差異與考評差異聯結為崗位考評差異;將轉換成本與流動風險聯結為潛在流動成本。各主范疇、開放式編碼范疇及關系內涵如表2所示。

表2 主軸編碼形成的主范疇
(三)選擇性編碼
本研究從主范疇中挖掘了核心范疇,分析核心范疇與其他主要范疇的聯結關系 ,并以“故事線”方式描繪行為現象和脈絡條件。完成“故事線”后實際上也就發展出新的實質理論構架,因此,選擇性編碼的關鍵在于“故事線”的描繪與構造[31]。本研究典型“故事線”如表3所示。

表3 主范疇的典型關系結構
本研究確定企業與高校科技人才雙向流動阻滯因素這一核心范疇,圍繞核心范疇的“故事線”可以概括為傳統保守觀念、負向心理情境對企業與高校科技人才的雙向流動意愿具有顯著的阻滯作用,崗位考評差異、潛在流動成本對企業與高校科技人才的雙向流動行為具有顯著的阻滯作用。在本文中,傳統保守觀念指科技人才及其家屬對流動懷疑式的評價與看法;負向心理情境是指科技人才由于安于現狀而產生的惰性心理以及面對流動而產生的壓力心理;崗位考評差異指企業與高校在科技人才聘用和考評方面存在的差異;潛在流動成本指科技人才在流動過程中產生的情感成本、財政成本、程序成本以及面臨的各種風險。以此“故事線”為基礎,本研究建構出企業與高校科技人才雙向流動的阻滯因素理論框架,稱之為“企業與高校科技人才雙向流動的阻滯因素模型”,如圖1所示。

圖1 企業與高校科技人才雙向流動阻滯因素模型
(四)理論飽和度檢驗
本研究用另外7份訪談記錄進行理論飽和度檢驗,對其依次進行開放式編碼、主軸式編碼和選擇式編碼,結果顯示,對于阻滯企業與高校科技人才雙向流動的四個主范疇(傳統保守觀念、負向心理情境、崗位考評差異、潛在流動成本),均沒有發現新的主范疇與路徑,四個主范疇也沒有形成新的構成因子。因此上述的“企業與高校科技人才雙向流動的阻滯因素模型”理論上是飽和的。
五、模型闡釋
通過以上編碼過程,企業與高校科技人才雙向流動的阻滯因素可以歸納為以下四個主范疇:傳統保守觀念、負向心理情境、崗位考評差異、潛在流動成本,但它們對企業與高校科技人才流動意愿和流動行為的作用機制是不一致的。
(一)負向心理情境與流動意愿
負向心理情境包括心理惰性和壓力感知兩個類屬。訪談中發現,企業與高校科技人才的流動意愿直接受到負向心理情境的影響,科技人才的心理惰性和壓力感知程度越高,科技人才就越不容易產生流動意愿。這可以從受訪者的一些代表性觀點看出來,如:“A04我已經習慣當前的工作狀態,是不會想到要去流動的”;“A12我之前換過工作,這中間壓力太大,所以我都不想再流動”;“A16一個人如果心已經老了,不愿嘗試新的東西,是不會想要去流動的”。當前一些研究也證實這一點,如:Seo(2011)證實心理惰性會對個體意愿產生影響[32],并且Lee(2005)表明較高水平的心理惰性不利于流動意愿的產生[33]。
(二)傳統保守觀念、負向心理情境與流動意愿
傳統保守觀念包括個人保守觀念與家庭保守觀念兩個類屬。訪談中發現,傳統保守觀念通過影響負向心理情境間接阻滯流動意愿的產生,即當企業與高校科技人才個人保守程度和所在家庭的保守程度較高時,更容易產生負向心理情境,從而阻滯科技人才產生流動意愿。許多受訪者都提到了這一點,如“A06父母都覺得穩定是最好的,如果轉換工作他們肯定會持反對意見,那樣家庭矛盾大,我壓力也大,所以還是沒有考慮過換工作的,尤其是跨度太大的工作”;“A11我個人來說比較保守,不想去追求一些新鮮的東西,日子過得安穩就好,所以沒有想過流動”;“A17我的太太并不怎么支持我換工作,她想要一種安穩、細水長流的生活,所以我就產生一種惰性,沒有想要出去闖闖的沖動”。許多研究也證實了這一點,韓淑娟(2017)的研究表明除了個體因素之外,家庭成員的觀念也會對流動個體的心理產生影響進而影響流動意愿[34];周皓(2004)認為現在越來越多的流動開始以家庭為單位進行流動,以保障婚姻的穩定性,因此家庭成員對待流動的態度對流動個體心理會產生顯著的影響進而影響流動意愿[35][36]。
(三)潛在流動成本與流動行為
潛在流動成本包括轉換成本和流動風險兩個類屬。訪談中發現,潛在流動成本直接阻滯企業與高校科技人才產生流動行為。在我們的訪談中,很多受訪者都反復強調這一點,如“A22我在這個單位待久之后,和同事之間的關系都不錯,即使想過流動一想到要離開這個社交網絡,我還是不愿意去實踐的”;“A12現在中國的保障體系都不完善,不像歐洲國家,換工作風險還是太大,所以只能想想”;“A27在原先的崗位上原始積累那么多,換個工作成本太大,雖然其他單位開出的條件還是挺好的,我也心動過,但也沒有行動”。流動成本理論也支持這一觀點,其認為流動過程中可能產生的成本是阻礙個體實施流動行為的關鍵因素[34]。其他學者也證實了流動成本嚴重阻滯科技人才的合理流動[37][38]。
(四)崗位考評差異、潛在流動成本與流動行為
崗位考評差異包括引進差異和考評差異兩個類屬。訪談中發現,崗位考評差異通過影響潛在流動成本間接阻滯流動行為的產生,即當企業與高校崗位考評差異越大時,潛在流動成本也就越高,從而阻滯企業與高校科技人才產生流動行為。這可以從被訪談者的一些代表性觀點看出來,如“A08高校更多考核的是科研和教學,企業主要是看經營業績的,理論和實踐脫軌太大,原先的東西用不上,換工作的成本太高,所以才會不選擇流動”;“A02企業與高校的工作要求相差太大,從前積累的一些經驗、能力什么的,換個工作大部分都用不上,這些都會阻礙我們流動”;“A15企業與高校的招聘要求是不一樣的,一個看學歷和科研,一個更看重經驗和能力,如果我在科研方面做了很多年更有優勢,企業經營那一塊我不怎么懂,失敗的風險是很大的,所以我應該不會去流動”。企業與高校在對科技人才的引進與考核要求方面存在較大差異的[39][40],這進一步會增大企業與高校科技人才雙向流動成本與風險,從而阻滯科技人才產生流動行為。
六、結論與展望
(一)研究結論
本研究運用扎根理論探索企業與高校科技人才雙向流動的阻滯因素及其作用機理,研究表明傳統保守觀念、負向心理情境、崗位考評差異及潛在流動成本這4類主范疇對企業與高校科技人才雙向流動有顯著的阻滯作用。其中,負向心理情境是阻滯科技人才產生流動意愿的直接因素,包括心理惰性和壓力感知兩個類屬;傳統保守觀念是阻滯科技人才產生流動意愿的間接因素,包括個人保守觀念與家庭保守觀念兩個類屬,其通過影響負向心理情境間接阻滯科技人才產生流動意愿;潛在流動成本是阻滯科技人才實施流動行為的直接因素,包括轉換成本與流動風險兩個類屬;崗位考評差異是阻滯科技人才實施流動行為的間接因素,包括引進差異與考評差異,其通過影響潛在流動成本間接阻滯科技人才實施流動行為。
在此基礎上,本文構建了“企業與高校科技人才雙向流動的阻滯因素模型”,該模型清晰地詮釋企業與高校科技人才雙向流動阻滯效應的形成機理,彌補了現有研究中的一些不足。現有研究大多考慮社會與組織情境因素對科技人才流動行為的影響,如張全同等(2012)認為檔案管理、戶籍制度、法律保護、經濟環境對科技人才流動產生較大的影響[41];Yan 等(2015)認為外部環境與組織因素對科技人才流動具有較大的影響[20]。Guagnano等學者于1995提出了態度—情境—行為理論,其認為行為的產生是由態度與情境兩方面共同決定的[42]。由此,本研究提出科技人才流動行為的產生由流動意愿與情境因素兩方面共同決定。本研究的具體理論貢獻如下:(1)本研究基于扎根理論將企業與高校科技人才流動結合起來進行研究,共同探討了企業與高校科技人才雙向流動阻滯效應的形成機理。(2)本研究除情境因素外,考慮了流動意愿對流動行為的影響,并進一步分析了阻滯流動意愿產生的作用機理。(3)本研究探索了傳統保守觀念、負向心理情境、崗位考評差異、潛在流動成本四個主范疇的形成機制和構成因子,其中除個體因素之外,家庭成員的觀念也會對流動個體的心理產生影響,進而影響流動意愿在現有研究中還沒有被重視。
(二)對策與建議
高校科技人才是我國實施科技創新戰略和實現經濟社會跨越式發展的關鍵性人力資源,促進高校和企業科技人才的雙向流動,有利于人才的優化配置。對經濟的發展能起到積極推動作用。本研究通過扎根分析,發現企業與高校科技人才雙向流動的阻滯因素主要包括負向心理情境、潛在流動成本、崗位考評差異、傳統保守觀念,為了促進企業與高校科技人才的雙向合理流動,本研究提出以下對策與建議:
其一,轉變科技人才的傳統保守觀念,降低科技人才的負向心理情境。在全社會營造創新創業的氛圍,轉變科技人才個人的傳統保守觀念。例如,大力倡導敢為人先、寬容失敗、崇尚創新、創業致富的價值導向,鼓勵科技人才創新創業;繼續推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在高校科技人才中貫徹落實,激發高校科技人才創新創業活力。同時,進一步深化職稱評審制度改革,試點將企業任職經歷作為高校評聘應用型科技人才的必要條件,并設立一定比例流動崗位,吸引具有創新實踐經驗的科技人才到高校兼職。最終,從心理惰性和壓力感知兩方面減弱負向心理情境,以提升企業與高校科技人才雙向流動意愿。
其二,縮小企業與高校的崗位考評差異,降低科技人才的潛在流動成本。把科研成果對經濟社會的影響納入高校科技人才評價的指標體系,將評價結果作為職稱晉升、崗位聘任、經費資助的重要依據;健全科技人才分類評價機制,發揮政府、市場、高校等多元評價作用,加快建立科學化、市場化的科技人才評價制度。同時,深入落實科技人才停薪留職政策,允許符合條件的高校科技人才帶著科研項目和成果、保留基本待遇到企業開展創新工作或創辦企業。此外,政府應加快人事檔案管理服務信息化建設,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減低科技人才的流動成本。
(三)研究不足與展望
本研究基于深度訪談,挖掘企業與高校科技人才雙向流動的阻滯因素,并構建企業與高校科技人才雙向流動的阻滯因素模型,彌補了現行研究將企業科技人才與高校科技人才作為兩個獨立主體進行研究的不足,研究結果對于以后開展類似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但本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例如,提出的4個阻滯因素,仍需要通過問卷研究進行檢驗,以確保維度結構的信度和效度;同時,不同阻滯因素對企業與高校科技人才雙向流動阻滯作用的強度,這些都需要進一步的深入研究。
參考文獻:
[1] 趙曙明,李乾文,張戌凡.創新型核心科技人才培養與政策環境研究——基于江蘇省625份問卷的實證分析[J]. 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12,49(3):49-57.
[2] 梁偉年.中國人才流動問題及對策研究[D]. 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4.
[3] 何潔,王灝晨,鄭曉瑛.高校科技人才流動意愿現況及相關因素分析[J]. 人口與發展,2014,20(3):24-32.
[4] 佚名.《“十三五”國家科技人才發展規劃》印發[J]. 中國人才,2017,(5):7.
[5] 吳道友,劉文獻.浙江省科技管理干部隊伍建設現狀及對策研究[J]. 產業與科技論壇,2012,(11):127-129.
[6] 紀建悅,朱彥濱.基于面板數據的我國科技人才流動動因研究[J]. 人口與經濟,2008,(5):32-37.
[7] 汪志紅,諶新民.珠三角地區中小型轉型升級企業人才結構、流動與開發[J]. 經濟管理,2016,(4):36-45.
[8] 楊敏,安增軍.產業轉移背景下科技人才流動模型研究——基于福建省的實證調研[J]. 東南學術,2015,(5):140-147.
[9] 劉航.南京企業科技人才流動影響因素分析及對策研究[D]. 南京:南京航空航天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
[10] Alferaih A. Developing a Conceptual Model to Measure Talent’s Turnover Intention in Tourism Organisations of Saudi Arabi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2017, 25(1),pp.2-23.
[11] Anton G., Sonja G. Intention to Quit as Precursor of Voluntary Turnover: Person-Organization Fit and the Psychological Contract-a Talent Management Quandary[J].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Labour Relations,2016,40(2),pp.55-76.
[12] Al-Sharafi H., Rajiani I. Leadership Practices and Talent Turnover: Study on Yemeni Organizations[J]. Business & Management Research,2013,2(3),pp.60-67.
[13] Liu R. The Mid-High-End Talent’s Job Embeddedness, Turnover Intention, and Cooperative Behavior: Job Insecurity as a Moderator[C].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nagement and Service Science, IEEE, 2011,pp.1-5.
[14] Karen J. Maintaining the Flow of Talent Through Apprenticeships[J]. Strategic Hr Review,2014,13(2),pp.424-425.
[15] Anonymous. Successful Mentoring Programs Reduce Turnover, Keep Talent[J]. Design Firm Management and Administration Report,2007,7(11),pp.1-3.
[16] Bryant P. C., Allen D. G. Compensation, Benefits and Employee Turnover HR Strategies for Retaining Top Talent[J]. Compensation & Benefits Review,2013,45(3),pp.171-175.
[17] 丹聆.為人才流動立規——高校人才誠信體系建設與高層次人才合理流動[J]. 中國高等教育,2017,(5):4-6.
[18] 生云龍,劉婉華.高校人才流動過程中的非理性問題研究[J]. 中國高教研究,2006,(2):35-38.
[19] 柳冰.影響高校科技人才流動的因素與激勵機制構建[J]. 中國高校科技,2014,(11):32-33.
[20] Yan G., Yue Y., Niu M. An Empirical Study of Faculty Mobility in China[J]. Higher Education,2015,69(4),pp.527-546.
[21] 劉進,沈紅.中國研究型大學教師流動:頻率、路徑與類型[J]. 復旦教育論壇,2014,12(1):42-48.
[22] 劉進,沈紅.大學教師流動影響因素研究的文獻述評——語義、歷史與當代考察[J]. 現代大學教育,2015,(3):78-85.
[23] Smart J. C. A Causal Model of Faculty Turnover Intentions[J]. Research in Higher Education,1990,31(5),pp.405-424.
[24] Xu Y. J. Gender Disparity in STEM Disciplines: A Study of Faculty Attrition and Turnover Intentions[J]. Research in Higher Education,2008,49(7),pp.607-624.
[25] Tolbert P. S., Simons T., Andrews A., et al. The Effects of Gender Composition in Academic Departments on Faculty Turnover[J]. Industrial & Labor Relations Review,1995,48(3),pp.562-579.
[26] Ehrenberg R., Kasper H., Rees D. Faculty Turnover at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alyses of AAUP data[J].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1990,10(1),pp.202-208.
[27] Daniels J. P., Shane H. M., Wall J. L. Faculty Turnover Within Academics: The Case of Business Professors[J]. Business Horizons,1984, 27(4),pp.70-74.
[28] 陳向明.扎根理論的思路和方法[J]. 教育研究與實驗,1999,(4):58-63.
[29] 費小冬.扎根理論研究方法論:要素、研究程序和評判標準[J]. 公共行政評論,2008,1(3):23-43.
[30] 賈旭東,譚新輝.經典扎根理論及其精神對中國管理研究的現實價值[J]. 管理學報,2010,7(5):656-665.
[31] 王建明,王俊豪.公眾低碳消費模式的影響因素模型與政府管制政策——基于扎根理論的一個探索性研究[J]. 管理世界,2011,(4):58-68
[32] Seo E. H.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Procrastination, Flow,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J]. Social Behavior & Personali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2011,39(2),pp.209-217.
[33] Eunju Lee. The Relationship of Motivation and Flow Experience to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 in University Students[J]. Journal of Genetic Psychology,2005,166(1),pp.5-15.
[34] 韓淑娟,顓慧玲,武漢祥.基于Order Probit模型的家庭化流動影響因素分析[J]. 經濟問題, 2017,(1):92-95.
[35] 周皓.中國人口遷移的家庭化趨勢及影響因素分析[J]. 人口研究, 2004,28(6):60-69.
[36] 陳衛,劉金菊.人口流動家庭化及其影響因素——以北京市為例[J]. 人口學刊,2012,(6):3-8.
[37] 李麗莉,張富國.高校創新型人才流動問題及對策研究[J]. 社會科學戰線,2011,(2):247-249.
[38] 夏茂林,馮文全.定期輪換制度下流動教師利益補償機制探討[J]. 教師教育研究,2011,(1):39-43.
[39] 殷凱,彭恬.高校教師績效考評的灰色關聯綜合測度[J]. 統計與決策.2017,(22):90-93.
[40] 王小琴.高科技企業科技人才評價與激勵[J]. 科研管理,2007,28(ZK):45-51.
[41] 張同全,高建麗.膠東半島科技型人才流動意愿[J]. 中國科技論壇,2012,(7):127-131.
[42] Guagnano G. A., Stern P. C., Dietz T. Influences on Attitude-Behavior Relationships: A Natural Experiment with Curbside Recycling[J]. Environment & Behavior,1995,27(5),pp.699-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