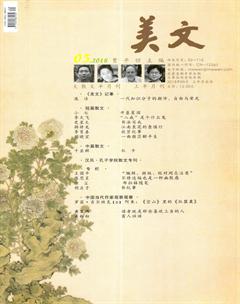看畫
穆濤
參話頭
齊景公問政于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論語·顏淵》
這句話,如果僅從字面上依文解義,會唐突孔子,會有“圣人不過如此”的直覺,一介只講忠孝的刻板腐儒而已。事實上這句話是沉甸甸的,話里有話,話外有聲,背后隱含著對齊景公入骨的批評。
齊景公是中國政治史里君主荒政卻悠然享國的極端個例,在位五十八年,上吃齊國數百年基業的“老本”,下有晏嬰等賢臣的輔佐。史書評價是“主昏于上,政清于下”,用老百姓的話說是“傻小子有傻福”。齊景公會吃會玩會享受生活,舒坦了一輩子,卻沒有留下一件政德之事。“齊景公有馬千駟(四千匹馬,指貪圖奢華),死之日,民無德稱焉”(《論語·季氏》)。這位君主在位時間長,兒子多,有記載的是六位,卻遲遲不立后嗣儲君。齊景公向孔子問政時的背景是這樣的:魯國發生臣逐君的動亂,孔子隨魯昭公到齊國政治避難,“昭公師敗,奔于齊…魯亂,孔子適齊”。(《史記·孔子世家》),“公孫于齊,次于陽州”。(《左傳·昭公二十五年》)魯昭公流亡齊國,住在次陽這個地方。這一年是公元前517年,孔子三十五歲,齊景公在位已經三十一年。孔子對癥下藥,用“君臣父子”八字方針闡述于國于家的政治主見,君臣是職業,君有君職,臣務臣業。父子是天德,父盡責任,子守本分。齊景公聽后只是嘴上叫好,卻沒有聽進去半個字,依舊我行我素。到了晚年,溺愛幼子“荼”,經常哄孩子玩游戲,也算父子情深,趴在地上,嘴里叼一根草繩、讓荼牽牛一樣走,甚至為此還磕掉一顆牙齒。彌留之際傳大位給幼主,卻是害了這孩子,引發諸子爭位賊臣弒君的禍亂。“齊陳乞弒其君茶”,“女忘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呼?”(《左傳·哀公六年》)。
齊景公的這些行為給后世的文學家預留了寫作的素材,“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魯迅·《自嘲》),“從來溺愛智逾昏,繼統如何亂弟昆。莫怨強臣與強冠,分明自己鑿兇門”(馮夢龍《東周列國志》)。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論語·八佾》
這一句與上一句的背景是聯系著的,“八佾舞”事件在前,魯昭公流亡齊國在后,均發生在公元前517年,記載見《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平子有異志”,季氏足季平子,魯國的執政大臣,君臣反目,刀兵互見,魯昭公兵敗被逐。佾是古代舞的規制名稱,每行八人,八佾是六十四人。古代的舞是政治待遇,天子八佾、諸侯六佾、大夫四佾,用現在的話講,季平子身為大夫,用八佾舞于庭,是嚴重超標。“將稀于襄公,萬者二人,其眾萬于李氏。”稀是大祭,魯昭公祭祀先君魯襄公。“萬”是舞名,跳萬舞的只有兩人,眾多的舞師都到季平子家里了。孔子講此事“不可忍”,指的是季平子的儹越反心。萬舞是古代祭祀傳統禮儀,自商代傳承下來的。《詩經·簡兮》這首詩對萬舞有生動豐富的描述。“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碩人俁俁,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孔子說,季平子在家里用這樣的舞蹈,不會有好果子吃的。這句評價是有大預感的,季平子反叛魯昭公后,他的家臣陽虎再反叛他,上梁不正下梁歪。
《論語》這部經書,是孔門弟子的課堂筆記摘要,自身是不成體系的。探究孔子的精神境界,既要把《論語》前后貫通著讀,還須下功夫參讀其它著作。比如第一句是講政治倫理的,文在《顏淵》一章,但在《季氏》一章里,孔子才把話講透徹。“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如果齊景公沒有那樣的行為,魯迅和馮夢龍也就無所議論了。封堵民眾之口的上策,是天子有好做為。再比如第二句講君臣倫理。君臣失睦是有潛伏期的,孔子在《易坤文言》中把這個道理說明白了,“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也,由辨之不早辨也”。
參話頭,是佛門里的話,指的是由一句話牽扯領悟出一堆東西,目的是找到厲害話的厲害之處。中國讀書人的老話叫“經史合參”,經是常道,是恒久不變的東西,是不動產。史是變數,是世道的玄機,是無常鬼。經與史參合著看,視角就立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