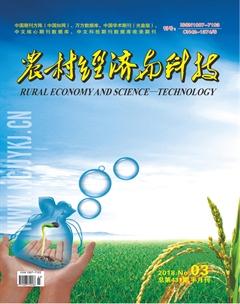淺析農村環境污染的刑法規制
陳禹衡
[摘要]農村環境污染日益嚴重,但是現有的污染環境罪在追責方面涵蓋的不夠全面,執法中存在無法可依的情況,不利于農村的環境保護。通過分析農村的環境污染來源,考慮到農村環境污染的分散性特點,討論其損害的法益,研究其刑法追責標準。借鑒美日等國對于污染環境的刑法規制,將土壤污染、水體污染、大氣污染、固體廢棄物污染納入到相關法律條文和司法解釋,使得污染環境罪的法律規制范圍更加全面,促進農村環境改善。
[關鍵詞]污染環境罪;農村環境污染;水體污染;大氣污染;固體廢棄物污染
[中圖分類號]D922.6 [文獻標識碼]A
1 引言
在科技和社會高度發展的今天,環境污染作為一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議題在不斷地被人提起,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社會輿論的關注重點在某種意義上更加偏向于城市和大型河流的環境污染,包括霧霾、流域型水體污染等。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們的身邊,農村的環境污染已經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由于農村的環境污染大多呈現污染源小、潛伏期長、污染情況密集等特點,在很多時候不為公眾所知悉,但是根據現有的數據顯示,農村的污染已經包括了水體污染、土壤污染、固體廢棄物污染、大氣污染等多種方面,可以說,農村已經成為了城市高速發展的垃圾填埋場,當年的綠水青山早已不復存在。
在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中,農村承受了城市發展所帶來的大量垃圾,包括固體廢棄物、大氣污染物、工業生產殘渣等。分析農村的環境污染問題,并且從污染環境罪的角度分析對于現有的環境污染的行為的規制,可以將污染環境的懲罰手段不僅僅局限在《環境保護法》、《大氣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海洋環境保護法》、《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等法律,從而以更加有效和嚴格的手段規制環境污染問題,才能真正做到“金山銀山不如綠水青山”。
2 農村污染源的定罪分析
污染環境罪原名是重大污染事故罪,在《刑法修正案(八)》出臺之前,只有較為嚴重的污染事故才符合重大污染事故罪的構成要件,這一點在該罪的罪名上得到了充分的體現。但是自從《刑法修正案(八)》頒布以來,充分地說明了國家對于環保領域的重視,從只有重大的環境污染事故,擴展到了污染環境這件事情本身,雖然依舊在條文中表明造成環境污染,后果嚴重,但是具有了具體的執行標準,便于辦案機關在實際操作過程中進行判斷。
對于農村污染源的刑事定罪,主要依據的由《關于辦理環境污染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和《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在這兩份主要文件中,前者對于農村地區的環境保護集中在了對于農田和林地的保護,分別是基本農田、防護林地、特殊用途林地五畝以上,其他農用地十畝以上,其他土地二十畝以上和林地五十立方米以上,幼樹二千五百株以上。后者則在其中第二條“致使基本農田、防護林地、特種用途林地五畝以上,其他農用地十畝以上,其它土地二十畝以上基本功能喪失或者遭受永久性破壞的”與第三條“致使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死亡五十立方米以上,或者幼樹死亡二千五百株以上的”,與農村污染環境息息相關。通過這兩個文件以清楚的判斷現階段對于農村環境污染的規制范圍主要集中在涉嫌污染基本農田、防護林地這些領域,集中規制土壤污染問題。對于水體、大氣、固體廢棄物的污染則沒有提及或者標準不明,但是現階段在農村地區存在著大量的對于河道、大氣的污染,以及固體廢棄物的大量堆積。這些污染物質對于農村環境的污染是相互交叉的而非割裂的。因此,探討其他污染物質對于農村環境的污染是否構成污染環境罪,以及定罪時的構成要件和依據,是具有現實意義的。
2.1 大氣污染分析
農村地區的大氣污染分為兩種:一種是主要集中在秋冬季節,主要原因是農作物的殘留根莖焚燒帶來的顆粒物污染;另一種是由于農村鄉鎮企業工業生產帶來的廢氣污染。對于這兩者產生的大氣污染是否構成污染環境罪,則具有相當大程度的爭議,按照《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中所要求的,則只有當造成公私財產30萬元以上損失、基本農田和林地受損、一人以上死亡或者造成傳染病爆發,才符合追訴標準。而在污染環境罪的犯罪客體方面,該罪將客體限制為了有放射性的、含傳染病病原體的廢物、有毒物質或者其他有害物質,因此可以將農村的秸稈燃燒產生的廢氣和工業廢氣劃歸為其他有害物質,符合犯罪的構成要件。
對于鄉鎮企業產生的工業廢氣污染,現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大氣污染防治法》對此做出了嚴格的規定,現有的法律條文已經明文規定對于工業生產產生的廢氣進行嚴格的審核和許可制度,設立了相應的排放總量控制和排污許可,除此以外,在現有的修正案中更是設立了重點領域和重點區域大氣污染防治,借以嚴格對于工礦企業的監管。農村地區鄉鎮企業現存的問題主要是監管和審核不夠嚴格,處以的罰款標準更是設立為一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這對于現有的鄉鎮企業的震懾力度是遠遠不夠的,而且因為沒有設立行政強制措施,則在實施過程中就更顯得單薄。在現實生活中,想達到《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中的要求,則更加困難,因為追訴標準其中并沒有涉及到造成空氣污染的相關后果。
對于農村地區的秸稈焚燒,現階段對于這種焚燒秸稈的行為,主要的處理依據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大氣污染防治法》中第四十一條第二款的規定:在人口集中地區、機場周圍、交通干線附近以及當地人民政府劃定的區域內露天焚燒秸稈、落葉等產生煙塵污染的物質的,由所在地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責令停止違法行為;情節嚴重的,可以處二百元以下罰款。該規定僅僅將對于焚燒秸稈造成的大氣污染的處罰限定為人口集中區、機場周圍、交通干線附近,僅僅在規定的領域進行規制明顯不能很好地對農村的大氣污染進行預防和處理。也不具有處罰力度。對于農村焚燒秸稈,我們應該清楚地認識到其不僅僅是造成大氣污染,因為污染是相互和循環的,焚燒秸稈所造成的大氣污染其中的粉塵和顆粒物必然會降落到土壤、林地、水體中,其中粉塵降落到水體中會導致飲用水污染,從而造成水體污染;粉塵降落到農田和林地中亦會造成阻礙樹木和農作物的生長,嚴重的會導致改變農田土壤的酸堿結構,從而符合了污染環境罪的立案標準的起訴規定。
2.2 水體污染分析
農村的水體污染現象,自從改革開放以來便日益嚴重,尤其是在鄉鎮企業發達的地區,以印染、紡織工業作為起步工業的鄉鎮,在完成資本原始積累的同時,也導致了農村水體污染的日益嚴重。以太湖地區為例,僅1997年周邊農村排放的TN達到6.4萬t,CODcr達到了18萬t,TP達到了1.2萬t。有鑒于此,對于農村地區的水體污染應該尤為重視,現階段對于農村水污染的規制主要集中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污染防治法》的第四章,對于向水體中排放各類有毒有害物質進行的規定。而在2013年兩高的《關于辦理環境污染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則將致使鄉鎮以上集中式飲水水源取水中斷12小時以上的,視為“嚴重污染環境”。但是值得爭議的是,在農村,將飼養禽類糞便產生的污水或者農業生產產生的污水排放到非飲用水源的自然水體中去,造成了水體不可逆的性質改變,是否可以構成污染環境罪?在現有的法條和法條解釋里,對于這一點并沒有詳細的規定,一方面這種行為并沒有構成飲用水水源的中斷,另一方面,這種行為也不符合立案追訴標準的相關規定。但是值得警醒的是,由于水體具有自由流動性,因此即使是現階段看來沒有具體影響的污染,在自然循環中也會造成相應的污染,水體在遭受污染之后,首先會隨著水量的蒸發導致有害物質到大氣中,除此以外,水體如果用于澆灌農田,也會導致基本農田和林地的污染,這種情況在農村屢見不鮮,2013年3月23日,新聞聯播的《中國水安全調查》中,就對河南新鄉利用造紙廠污水澆灌小麥一事做了披露。
對于水體污染流動和循環的情況,如果等到水體污染轉移到農田和林地之后再加以規制,則顯得過于滯后,因此對于農村水體環境污染突出的問題,最佳的解決方式就是將現有的《關于辦理環境污染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加以補充,制定合理的水體污染數據標準,將衡量水體質量的三個主要參數TP、TN、CODcr作為參考的標準量,將污染水體的犯罪行為刑事化,而非簡單地將其用治安管理處罰進行規制,單獨的《水污染防治法》雖然具有定位精準詳細的優勢,但是在刑法法條和司法解釋中不對水體污染加以規制會對農村小而分散的水體污染力不從心,法律效力大打折扣。
2.3 固體廢棄物污染
農村地區的固體廢棄物污染,伴隨著城鄉二元結構的形成而日益嚴重,除了農村自己的生活垃圾和鄉鎮企業的工業垃圾,農村地區的固體廢棄物很大一部分是承接城市地區的固體垃圾。現有的法條和司法解釋中,對于固體廢棄物造成的污染的規制僅僅局限于放射性廢物、危險廢物、含重金屬、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廢物,對于日常的固體廢物例如廚余垃圾等則并沒有規定,這些垃圾雖然看似危害不大,但是嚴重影響農村環境。一方面,這些垃圾構成了垃圾山、垃圾海“包圍”的村莊,造成大氣污染,甚至會誘發疾病,嚴重影響了農村的人居環境;另一方面,這些垃圾富含氮、磷等微量元素,對于環境的影響深遠,包括水體和土壤的富營養化,會對農作物的生產造成很大的影響。若等到產生具體影響的時候再進行追責,一是追訴時效很大可能已經過去,二是計算成本高昂,對于已經造成的影響無法彌補,從而不利于環境保護的預防性。在2013年的無錫跨境垃圾掩埋案中,犯罪人將上海的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掩埋到了無錫的鄉村,雖然這些垃圾本身含有污染物質較低,只能依照“致使公私財產損失三十萬以上”來定罪,這是存在司法漏洞的,正是因為沒有考慮到固體垃圾本身掩埋所造成的的損害,而將損害集中于財產損失,導致了定罪量刑不易,很多時候依靠治安管理處罰進行管制,威懾效力大大降低。
將固體廢棄物污染納入到污染環境罪的法條和司法解釋中去,有助于預防固體廢棄物污染造成的相應后果,應該根據垃圾分類制定相應的標準,不能僅僅將定罪目標局限在放射性廢物、危險廢物、含重金屬、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廢物,對于日常的生活垃圾等固體廢物,也應該加以重視,尤其是考慮到其對于水體、大氣、土壤循環的影響,則更應該重視細化固體垃圾的定罪指標,防止農村地區成為城市的“垃圾填埋場”。
3 農村環境污染的條文借鑒與完善
在環境污染的法律條文修訂方面,日本的立法模式是以單行特別環境刑法為基礎的多元化模式,是集實體法與程序法為一體的特別立法形式,包括單行刑法、附屬刑法、刑法典等70余種模式,包括公害救濟法、公害控制法、公害防治事業法這三大體系,目的明確,涵蓋全面。在對于農村環境污染的刑事追責方面,用單行刑法加以明確規定,例如《關于廢棄物處理及清掃法》,就有對于固體廢棄物污染的刑事追責。在污染刑事追責方面,設立了《日本國憲法》和《公害對策基本法》,作為環境污染追責的指導性法源。
美國對于環境污染的追責問題,因為其法律體制與我國不同,因此沒有設立單獨的污染環境罪,而是依靠聯邦法、州法、地方條例來進行三級規制,涉及120多部法律,其中對于噪聲、殺蟲劑、固體廢棄物等都納入了法律規制的范疇。但是其對于環境的刑事追責方面則沒有明確的規定,只是將刑事處罰手段當做最后的防線加以使用。
面對現階段的農村環境污染的刑法規制問題,應該清楚地認識到對于農村環境污染的監管不足以及刑事追責方面的缺失。在現階段為了加強對農村環境污染的監管,而不是局限于城市和生態保護區,應該嚴格細化農村環境污染的刑事追責。根據法經濟學的觀點,對于環境污染的追責目的不能僅僅局限于彌補環境污染所造成的經濟損失,而是應該重視環境污染對于人民生活環境和身體健康的影響,相應習總書記“既要金山銀山,又要綠水青山”的號召,不能僅僅用經濟損失考慮環境污染的代價,要將眼光長遠地考慮到對于農村環境的未來影響。有鑒于此,加強對于農村污染的監管,當務之急就是要補充污染環境罪的法律條文和司法解釋,將其細化,使得對于農村環境污染的懲治有法可依。
第一,將空氣污染指標納入到刑事追訴的條件中,考慮到農村空氣污染的分散化,主要是集中在秋季收割季節,但同時這些秸稈的焚燒,也必然會導致農村地區空氣質量短時間內的急劇惡化,甚至會導致城市地區PM2.5升高。一方面,應該擴大對于控制焚燒秸稈的面積,不僅僅只管轄人口集中地區、機場周圍、交通干線附近,更應該將鄉村等地域納入監管,大氣污染是流動而且循環的,在農村這種空曠的地區,分散式的污染如果不能嚴格制止會迅速轉化成全局式的污染,從而造成大面積污染,所以應該進行全面無死角的監控;另一方面,應該加大對于農村秸稈焚燒的處罰,處罰的力度不能僅僅用經濟處罰,可以進行治安管理處罰,對于情節嚴重的可以進行刑事處罰,從而增加對于農村大氣環境污染行為的震懾力,將分散式的大氣污染扼殺在萌芽狀態。
第二,將水體污染的入罪條件擴大,現有的法律文件中,將水體污染的追責條件限制為“致使鄉鎮以上集中式飲水水源取水中斷12小時以上的”,這就將該罪的損害法益限制為對于社會公共秩序的影響。但是水體的污染除了對于社會公共秩序有影響之外,對于環境也有不可逆的影響,因為水體在自然循環中作為重要的一部分,水體污染自然會導致土壤、大氣的相關污染。設立水體污染監管指標,主要的檢測指標就是TP、TN、CODcr,這三個指標可以較為客觀的反映水體的污染情況。將水體檢測指數納入到追責條件中,有助于將水體污染的處罰限制在開始階段,阻止其向其他方面擴散。
第三,將固體廢棄物污染的監管納入到入罪條件中,固體廢棄物的監管一直是環境污染監管的盲區,且固體廢棄物的定義遠遠大于廢渣的定義,固體廢棄物包括城市和農村的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等,除了富含有機物會導致水體富營養化外,還會改變土壤的組成結構,導致農田被破壞和侵占。有鑒于此,應該將過量堆積固體廢棄物也納入污染環境罪的追責事由之中,設立合理的堆積體積指數,督促其快速地處理固體廢棄物,而不是一堆了之,任由其對環境造成破壞。
4 結語
我國現階段經濟發展迅速,農村地區作為城鄉發展二元結構的薄弱地區,在過去三十年里承擔了相當大的生態壓力,環境污染形勢異常嚴峻。面對這種困境,首先是將類似于日本《公害對策基本法》的《環境保護法》拔高到環境保護的基本法的地位,配合刑法中的污染環境罪增加其震懾效力。其次,要補充污染環境罪的刑事追責條件,尤其是補充關于大氣污染、水體污染、固體廢棄物污染的刑事追責,將其細致化、刑事化,增加其處罰力度,從多角度控制農村環境污染問題。最后,通過司法解釋的內容來隨時更新農村環境的保護方向。只有充分認識農村環境污染的嚴峻性,完善污染環境罪的追責制度,促使污染環境的追責行為有法可依,以便更好地保護農村環境,永葆“綠水青山”。
[參考文獻]
[1] 李榮剛,夏源陵,吳安之,等.江蘇太湖地區水污染物及其向水體的排放量[J]. 湖泊科學,2000(02):147-153.
[2] 閆艷.無錫中院公布首份環境資源審判白皮書[N].中國環境報,2017-03-22.
[3] 陳英慧,關鳳榮.中日環境犯罪問題比較[J]. 河北法學,2009,27(12):42-45.
[4] 王坤.我國環境刑事立法研究[D].哈爾濱:東北林業大學,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