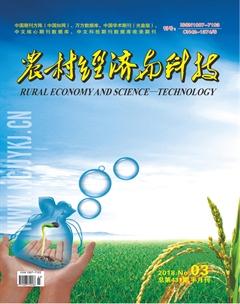從一起典型案件談林權歷史性糾紛案件的法律與政策適用
劉恒
[摘要] 集體林地、林權是集體所有制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有關人民政府及司法機關在處理林權歷史性糾紛的相關案件中,既要正確適用當前有效的法律政策,也要正確適用歷史性政策、法令的內在精神,從而對案件作出公平合理的處理。
[關鍵詞]林權歷史性糾紛,法律與政策適用
[中圖分類號]F307.21 [文獻標識碼]A
林地、林權是集體所有制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森林法明確規定,國家所有的和集體所有的森林、林木和林地,個人所有的林木和使用的林地,由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登記造冊,發放證書,確認所有權或使用權。
產權制度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石,保護產權是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必然要求,這是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中所明確的政策精神,有關人民政府及司法機關在處理相關案件中,既要正確適用當前有效的法律與政策,也要正確適用歷史性政策、法令的內在精神,從而對案件作出公平合理的實體處理結論。
1 案例簡介
浙江省某縣A村與B村之間有一名為“牛山”之地,被當地政府因建設火電廠而征用。B村以牛山之林系其村民所植為由,要求將林木及征地補償款歸于該村;A村則主張該山系其自古以來即享有權利的“族山”,且B村在牛山之上所植林木系侵占A村的土地所實施的“占地造林”侵權行為,雙方為此曾在20世紀60年代即因B村侵權造林而發生過集體械斗事件,故要求政府將補償權益劃歸本村。雙方援引的依據均包括《土地改革法》及人民公社時期有效執行的法令與政策。
A村認為,政府將林木權益單純地劃歸B村,但對林地權屬未作出任何確權結論,處理決定僅考量了B村對牛山之林的管理現狀而未考慮A村對林地所享有的歷史性權利因素。為此,A村與縣人民政府及第三人B村之間發生“林業行政裁決糾紛”之訴。
2 法理分析
在政府對集體林地、林權的確權與裁決處理中,歷史性糾紛案件往往發生在相鄰的村委、村民小組或集體經濟組織單位之間。由于所涉林權、林地在歷史上的地理分界和產權管理界限并不十分明確,政府在確權裁決中常陷入既必須依法處理又難以達到公平合理的“兩難”境地。
司法實踐中,涉及集體林權、林地的歷史性糾紛情形紛繁復雜。有的糾紛具有歷史持續性,可能從劃界發生糾紛時起歷經行政處理、行政復議及各類級別的行政訴訟而至今仍無定論,一直處于持續的申訴程序中;有的是原本雖有糾紛事實但各方認為爭議價值不大,故從未啟動相關行政確權或司法審理程序,后因涉及政府征地補償等現實利益的歸屬而引發糾紛。
更難處理的是,如果一方實際管理林權而另一方擁有地權,則管理林權的一方往往援引“管理現狀”的確權規則而要求政府和司法機關給予保護;而另一方則以林地系其“歷史性權利”之地為由,認為對方的植樹造林屬于侵權行為,從而要求將林地林權均確認歸己方所有。
2.1 正確認知《土地改革法》等歷史上有效的法令與政策在
確權糾紛中的可適用問題
“土改”不僅是一項根本性的土地所有制改革,而且是一項涉及“重構”中國社會階級的憲政改制運動。目前,《土地改革法》雖因失去了適用的歷史和現實條件而廢止,但在土地、林木確權的歷史性糾紛中,其有關規則依然具有最高確權效力。
本案爭議牛山在土改時屬于具有公益性質的山地、山林,而《土地改革法》第23條曾明確規定:“為維持農村中的修橋、補路、茶亭、義渡等公益事業所必需的小量土地,得按原有習慣予以保留,不加分配。”也即,此類山林不屬于土地改革運動征收和分配的范疇。事實上,土改運動也未對牛山整體作出任何重新分配決定,故牛山的歷史性權利一直屬于A村。
根據《土地改革法》第11條規定,“分配土地,以鄉或等于鄉的行政村為單位,在原耕基礎上,按土地數量、質量及其位置遠近,用抽補調整方法按人口統一分配”。顯然,土地改革是一項有規則、有步驟的法律實施活動,對土地分配的區域范疇嚴格以“村”或“鄉”為單位。也即,如果AB兩村土改時所在的鄉,均將土地的所有權結構打亂而重新跨鄉跨村分配的話,則全鄉各村之間土地的“地權結構”必須以土改后的結果為準;如果當年未徹底打亂原有各村的土地建制,從而沒有在各村之間進行“跨村”重新分配的話,則土改只是在原有的“村莊”范疇內進行。也就是說,原屬于A村的土地不可能分配給B村;同樣,原屬于B村的土地當然也不能給A村。
因此,有關縣級人民政府的處理決定或是復議決定,以及人民法院的司法裁判均應查明當年土地改革的歷史事實,以作出正確的確權結論。
2.2 在林業“三定”時錯誤發放林權證的,應當據實糾正,
且不得以此頒證行為作為確權依據
1981年3月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保護森林發展林業若干問題的決定》。其中,在“穩定山權林權,落實林業生產責任制”一節中明確規定:“凡林權有爭議的,由有關政府,組織有關雙方,協商解決。協商無效時,提請人民法院裁決。在糾紛解決之前,任何一方都不準砍伐有爭議的林木,違者依法懲處。”
本案中,1982年浙江省實施林業“三定”時,AB兩村之間在20世紀60年代因牛山爭議引發的歷史性糾紛并未消除,不符合給任何一村頒發林權證的法定條件。故該縣人民政府于林業“三定”時向B村作出頒發林權證的行政行為有違當時的政策法令精神,同時也未盡到向爭議另一方A村的通知或公告義務。
據此,應根據“尊重歷史事實,尊重集體主權”的原則對發證行為予以糾正,不宜以“時代久遠”為由而將侵權之舉合法化,更不得以錯誤頒發的林權證為據而作為目前確權的根據。
2.3 要正確認知歷史上的林權證和土地證的不同法律效力
當前,我國實行統一的不動產登記制度,但本案中縣政府給B村的林權證頒發于1982年,當時的林權證和林地證尚未合一,是兩種不同性質的權利憑證。原國家土地管理局辦公室在《關于林地發證問題的復函》中明確,土地管理部門依照《土地管理法》和《森林法》確定土地權屬后核發的土地證書與林業部門依照《森林法》頒發的林權證的性質不同,土地證書是土地使用權和土地所有權的法律憑證,林權證是地上林木所有權的法律憑證,各自具有不同的法律效力,二者不能互相代替。
因此,在縣級人民政府有關確權處理決定中僅涉及林權而遺漏了地權處理事項的,爭議各方可另行提請政府就林地權屬作出處理。
綜上,筆者認為,對上述糾紛的確權與裁決規則宜采取“尊重林地的歷史性權利,尊重林權的現實管理狀態”這一雙重尊重的基本原則,將林地確權歸于享有歷史性權利的一方,將林權確權為雙方共有,從而公平合理地解決有關歷史性糾紛。
[參考文獻]
[1] 張自于.中國林權改革發展之路[J].當代中國,2015(5).
[2] 張自強、高嵐.山林糾紛的類型梳理和成因探究[J].林業經濟問題,2013(3).
[3] 胡衛東.黔東南苗族山林保護習慣法研究[M].北京: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2012.
[4] 李土云.林區邊界山林糾紛產生的原因和對策[J].中南林業調查規劃,2013(2).
[5] 陳永富、程云行、李蘭英等.山林糾紛調處方法比較研究[J].浙江林學院學報(林業經濟版),20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