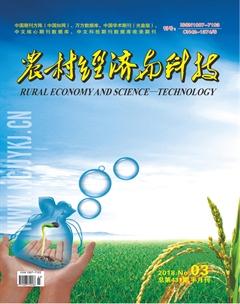長沙市耕地資源生態安全評價
曾爭 陳千逸
[摘要]隨著工業化、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城市建成區大幅度擴張,長沙市耕地資源面臨嚴重的生態安全問題。以耕地資源生態安全的概念和內涵為切入點,介紹了耕地資源生態安全評價的研究現狀,借助前人的研究成果構建評價指標體系與模型,對長沙市2009~2015年耕地資源安全狀況進行評價,基于評價結果分析了影響耕地資源生態安全的主要因素,并對維護長沙市耕地資源生態安全提出了相關建議。
[關鍵詞]耕地資源;生態安全;土地評價
[中圖分類號]F301.24 [文獻標識碼]A
引言
目前,耕地資源生態安全這一概念缺乏能夠得到廣泛認同的定義,也沒有形成獨立的理論體系,其理論主要來源于土地資源可持續發展理論、生態安全理論等方面的研究成果。通過對相關文獻的梳理,筆者將耕地資源生態安全的概念界定為:在一定的時空范圍內,耕地數量、質量保持總體穩定,耕地資源受外部環境干擾較小,耕地生態系統的結構與功能能夠維持健康穩定運轉并發揮出正常作用——持續穩定地提供人類社會發展所需的各種資源。耕地資源生態安全大體上包括數量安全、質量安全及生態環境安全三方面的內容,它與耕地資源生產能力、糧食安全、土地資源可持續利用以及整個社會經濟健康穩定的發展具有密切關系。
1 研究現狀
由于土地制度、社會經濟發展狀況、人地關系等方面的不同,我國學者對耕地資源生態安全評價的關注和取得的研究成果遠多于國外學者,已有文獻中對這一領域的研究表現出以下特點:①在研究的空間尺度上,前期以全國尺度為主,隨著時間推移針對某一地區的研究逐漸增多;②在研究的時間尺度上,由時點轉向10年、20年甚至更長時間;③在評價方法的選擇上,常用方法有模糊綜合評價法、綜合指數法、系統動力學方法等;④在評價指標的選擇上,現階段常見的、較為科學的評價指標體系主要有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壓力—狀態—響應評價指標體系、暴露—響應分析指標體系等,這些指標體系各有優缺點及適用范圍。由于每個地區的自然資源稟賦、社會經濟發展狀況不盡相同,因此需要根據研究區的實際情況選擇合適的評價指標體系。本文選擇長沙市作為研究區域,2009~2015年為研究時段,構建由14個指標組成的指標體系對長沙市耕地資源生態安全狀況進行評價與分析。
2 長沙市耕地資源生態安全評價定量分析
2.1 評價指標體系構建
根據前文對耕地資源生態安全這一概念的理解和定義,依據科學性、全面性、代表性和可操作性等原則,本文從自然、經濟和社會三個方面出發構建了長沙市耕地資源生態安全評價指標體系(見表1)。評價指標體系共分為目標層、因素層和指標層3個層次。在指標層中,自然因素層面的4個指標主要反映了耕地面積與質量變化情況;經濟因素層面的6個指標主要反映了耕地投入、利用、產出狀況;社會因素層面的4個指標主要反映了外部環境對耕地資源的影響。總的來看,這14個指標覆蓋范圍較廣,能夠全面反映出耕地資源生態安全的變化情況。
2.2 評價模型構建
2.2.1 確定指標權重。綜合對比了各種指標權重的確定方法后,筆者決定使用熵值法計算指標權重。熵值法是一種客觀賦權方法,它依據各個指標信息熵值的效用價值來確定權數。相比德爾菲法、模糊評價法、層次分析法等主觀賦權方法,熵值法得出的權數可信度高,適用于耕地資源生態安全評價這種多指標的復雜情況,其計算過程如下:
(1)原始數據標準化。公式為:
正相關指標: 式(1)
負相關指標: 式(2)
式中,Xij代表標準化處理后的值,xij代表第i年第j個評價指標的原始值,max{xj}和min{xj}分別代表第j個評價指標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2)計算第j項指標的熵值ej,公式為:
式(3)
表2 耕地資源生態安全類型劃分標準
S 安全等級 特征
≥0.9 安全 耕地生態環境未受干擾或僅受到輕微干擾,生態系統結構完整。耕地利用非常科學,能夠提供人類社會發展所需的各種資源,沒有生態問題。
0.9>S≥0.7 良好 耕地生態環境受到輕微破壞,但耕地數量和質量能夠維持在正常水平,生態系統結構還比較完整,功能發揮未受較大影響,可以保持較高的產出水平。土地利用情況良好,生態問題不顯著。
0.7>S≥0.5 敏感 耕地生態環境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壞,耕地數量減少或質量下降,但尚能維持基本的結構。耕地利用出現問題,功能發揮受到干擾,生態問題顯現。
0.5>S≥0.3 風險 耕地生態環境受到比較嚴重的破壞,耕地數量急劇減少或質量持續惡化,維持或恢復耕地生態系統的結構和功能比較困難,污染比較嚴重。
<0.3 惡化 耕地生態環境受到嚴重破壞,生態系統結構殘缺,土壤受到嚴重污染,功能退化。耕地利用、恢復非常困難,出現生態災害。
式中,,k=1/lnm;當Aij=0時,lnAij沒有意義,因此對Aij=0的情況加以修正,令Aij=0.0001。
(3)計算第j項指標的效用度dj,公式為:
dj=1—ej 式(4)
(4)計算第j項指標的權重Wj,公式為:
式(5)
2.2.2 計算生態安全綜合得分與劃分生態安全類型。在耕地資源生態安全評價指標體系中,每項指標都從不同層面反映了耕地的生態安全狀況。為全面反映長沙市耕地資源生態安全的整體情況,需要計算生態安全綜合評價得分S,公式為:
式(6)
按照基本等量、就近取整的原則,將S的取值范圍劃分為5個區間,對應5個安全等級,并對不同的安全等級進行定性描述(見表2)。
2.3 計算過程與結果
2.3.1 數據來源。本文研究數據主要來源于2009~2015年的土地利用變更調查數據、《湖南統計年鑒》、《長沙統計年鑒》以及統計公報。
2.3.2 計算結果。利用式(1)~式(6)得到長沙市2009~2015年耕地資源生態安全評價綜合得分,同時還可以統計出各個因素的得分情況(見表3)。
3 結果分析
從計算結果來看,2009~2015年長沙市耕地資源生態安全評價綜合得分起伏波動,耕地資源生態安全等級總體處于中下水平,情況不容樂觀:7年里最好的情況也僅是剛好達到良好等級,而2013年生態安全等級降至最低,接近于退化。觀察各個因素得分變化情況可以發現,2009~2015年“自然因素”得分在起伏波動中降低;“經濟因素”得分總體保持上升態勢;而“社會因素”得分則急劇下降。這些變化表明7年間長沙市耕地資源的數量與質量受到了較大干擾,盡管耕地資源利用與產出還是維持著較高的水平,但外部環境對耕地資源的影響逐漸加重。為了進一步弄清哪個因素與綜合評價得分之間的變化關系較為密切,筆者計算了S值與三個因素得分的Pearson相關系數,計算結果顯示,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自然因素”、“社會因素”與S值的相關系數分別為0.974、0.785,而“經濟因素”與S值的相關系數未通過10%顯著性水平檢驗。由此可以認為,長沙市耕地資源生態安全等級下降主要受自然條件、外部條件的影響。通過進一步觀察,可以推斷出上述變化的具體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1)城鎮建設用地擴張占用大量耕地是導致生態安全等級降低的主要原因。長沙市城市規模在過去幾年增長較為迅速,2009~2015年建成區面積由249km2增長至364km2,城市空間擴張侵占了大量耕地資源,2009~2015年長沙市耕地面積呈逐年減少的趨勢,從2009年的2.84×105ha減少至2015年的2.77×105ha,7年間耕地面積減少了1.04×104ha。各地區中耕地面積減少量最大的是河西地區(岳麓區、望城區、寧鄉市),共減少1.53×103ha;雨花區耕地面積減少幅度最大,降幅達到了24.28%,其次是芙蓉區,降幅為17.71%。與此對應的是,這三個地區也是最近幾年來長沙市的重點發展區域。
(2)占補平衡中補充耕地的質量無法與被占用耕地的質量相提并論。由于城市擴張占用的大多是質量較好的耕地,而新補充耕地往往在某些方面存在問題(例如坡度過大、海拔過高、灌溉不便等),難以和被占用耕地相比較,使得耕地質量整體下降。
(3)不合理的耕地利用方式破壞耕地生態環境。現代農業對農藥、化肥的依賴程度日益上升,雖然這些工業制品在短時間內有利于農作物的正常生長,但從長遠來看,長期使用化肥農藥將導致土壤板結、沙化,引起水土流失、生物多樣性減少等問題,這對于維護耕地資源生態安全極為不利。
(4)農業從業人員減少,拋荒現象增多。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從事農業所帶來的收益遠低于從事第二、三產業所帶來的收益,造成農業從業人員大量流入其它產業,耕地拋荒不可避免,最終影響到耕地生態系統的結構穩定性和功能完整性。
4 結論與討論
本文首先對耕地資源生態安全的概念與內涵進行探討,在此基礎上構建評價指標體系,利用熵值法計算指標權重,最后得到長沙市2009~2015年耕地資源生態安全綜合得分,針對得分情況進行評價與分析。鑒于以上研究結果,筆者認為未來長沙市對耕地資源的保護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①堅決貫徹執行耕地占補平衡政策,不僅僅要保持耕地數量總體不變,還要確保補充耕地的質量與被占用耕地的質量相一致或相近,從根本上維護耕地資源的生態安全;②開展土地整治工作:在耕地方面,要維持現有耕地的生產能力;對于生態環境受到破壞的耕地應進行土地修復,提高和恢復其生產能力;在建設用地方面,騰退超標的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和宅基地,用于生態環境建設,提高農村地區的生態環境質量;新增城鎮建設用地應盡量少占用耕地、不占用優質耕地,控制城鎮化發展對耕地資源生態環境的影響;③加大農業基礎設施的投入力度,提高農業生產過程中機械化、信息化水平,改善農業生產條件;建設一批高標準農田,利用生物技術改善新增耕地的土壤肥力,盡量使用生物肥料、有機肥料,減少對化肥、農藥的依賴程度;④提高農業從業人員的素質,培育擁有較高文化水平的農業工作者,以應對農業從業人員逐年減少的問題;⑤建立科學合理、行之有效的耕地流轉機制,將有限的耕地資源集中到生產大戶、農業合作社、農業企業等大型農業生產單位的手中,提高耕地資源的利用效率。
[參考文獻]
[1] 鄧慧.長株潭地區耕地資源生態安全評價與調控模式研究[D].長沙:湖南師范大學,2015.
[2] 張銳,劉友兆.我國耕地生態安全評價及障礙因子診斷[J].長江流域資源與環境,2013,22(7):945-951.
[3] 徐啟榮,趙海強,江云,等.安徽省農田生態安全預警信息系統研究與建立[J].安徽農業科學,2007,35(30):9615-9618.
[4] 郜紅娟,蔡廣鵬,羅緒強,等.基于能值分析的貴州省2000-2010年耕地生態安全預警研究[J].水土保持研究,2013,20(6):307-310.
[5] 文森.重慶市耕地資源安全與預警研究[D].重慶:西南大學,2008.
[6] 王軍.石家莊市耕地動態變化與生態安全評價研究[D].石家莊:河北師范大學,2009.
[7] 文森,邱道持,楊慶媛,等.耕地資源安全評價指標體系研究[J].中國農學通報,2007,23(8):466-470.
[8] 王國剛,楊德剛,蘇芮,等.生態足跡模型及其改進模型在耕地評價中的應用[J].中國生態農業學報,2010,18(5):1081-1086.
[9] 王富喜,毛愛華,李赫龍,等.基于熵值法的山東省城鎮化質量測度及空間差異分析[J].地理科學,2013,33(11):1323-1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