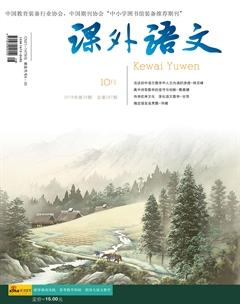一字傳神顯神韻
沈玉成
【摘要】古人寫詩,十分講究煉字,常是“吟安一個字,捻斷數莖須”,“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詩人常選擇最恰當的字眼來表情達意。本文以《泊船瓜洲》為例,感知詩人對家鄉的思念之情以及建功立業的人生追求。
【關鍵詞】煉字;情感;神韻
【中圖分類號】G633 【文獻標識碼】A
相傳,有一天黃庭堅在蘇小妹家與蘇軾閑談,蘇小妹出了一道題目,要求在“輕風細柳”“淡月梅花”兩句中各加一字,成為兩句五言詩。蘇東坡不假思索,隨口吟道:“輕風搖細柳,淡月映梅花。”蘇小妹說:“好雖好,但不算最好。”黃庭堅見蘇小妹否定了蘇軾的兩句詩,略一思考,說道:“輕風舞細柳,淡月隱梅花。”蘇小妹仍然說:“好雖好,但還不是最好。”兩人齊問蘇小妹怎樣才算最好?蘇小妹給出的答案是:“輕風扶細柳,淡月失梅花。”
蘇東坡和黃庭堅聽了不由地拍手叫好,因為在蘇小妹的兩句詩中,風只是“扶”著細柳,細柳不“搖”也不“舞”,可見,那風是多么“輕”了;在月光下,梅花簡直失掉了蹤跡,可見那月色實在是“淡”極了。蘇小妹在詩中緊扣了“輕”“淡”二字,用字可謂十分精當,達到了一字傳神的效果,為此,蘇黃二人甘拜下風。
對于詩中的煉字,古往今來,文人墨客為我們留下了許多錘煉佳話。下面,筆者以《泊船瓜洲》為例,談談詩人寫作此詩是如何盡展神韻的。這首詩寫于王安石離開生活多年的第二故鄉江寧,應宋神宗征召入京之際,寫給他的一位友人金山寺寶覺和尚離別之時,典型反映了他功成身退的人生理想。理解王安石的這種理想,我們首先要了解王安石與江寧的關系。
王安石本是江西臨川人,父親王益在外做官,少年王安石在 臨川跟著母親生活,每日讀書寫文章,以應科舉。16歲時,王益調任江寧知府,王安石隨全家遷到江寧桃花塢,并繼續著他的讀書生活。王安石有詩記錄自己在南京的閉門讀書生活:“桃花石城塢,餉田三月時。柴門常自閉,花發少人知。”宋仁宗寶元二年(公元1039年),49歲的王益病故在江寧知府任上,王安石把父親葬在南京牛首山,自己在牛首山守喪。宋仁宗慶歷二年(公元1042年),守喪期滿,22歲的王安石考中進士,外出做官,一直做到京官。從16歲至22歲,王安石一直生活在江寧,加之父親葬在江寧,江寧作為家鄉的概念已在王安石心中扎根。嘉祐七年(公元1062年)王安石的母親在京城病逝,王安石辭去知制誥官職,扶母親的靈柩回到江寧,把母親跟父親合葬,自己在牛首山給母親守喪。妻兒均住在江寧老宅上。三年守孝期滿后,王安石因病沒有離開江寧老宅,而在江寧辦書院講學。宋神宗剛即位,即宋英宗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九月,王安石被神宗任命為翰林學士兼江寧知府,半年后入京任參知政事。從嘉祐七年到熙寧元年,又是六年的江寧生活,江寧作為老家的概念在王安石的心中更加鮮明了。
其次,我們借助詩人的精心煉字來把握情感。詩中的“綠”字,歷來為世人所稱道,因為王安石在創作本詩時,也的確幾易推敲,從開始的“到”“過”“入”“滿”,換了十多個字,到最后才確定為“綠”字。其實,“綠”字在此處用法也并非王安石首創。此外,王安石還暗用《楚辭》“王孫游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和王維《送別》“春草年年綠,王孫歸不歸”的詩意。為此,“綠”字,不僅生動形象地表現了春天到來后千里江岸一片新綠的景象變化,表現了春天的生機勃勃,而且側面反映了詩人對前途充滿希望、充滿信心,更表現了江南綠了,家鄉也會綠的聯想,引出了作者對家鄉親人的思念之情,進而抒發了游子的宦游情懷。
其實,除了“綠”字,詩人對詩中的“一”“只隔”“又”等字也是精心挑選、仔細斟酌的;“春風”“何”也是別具匠心的。一水:一條河。古人除將黃河特稱為“河”,長江特稱為“江”之外,大多數情況下稱河流為“水”,如漢水、湘水等,這里的“一水”指長江。一水間指一水相隔之間,因為“京口”,古城名,在江蘇鎮江市,在長江南岸;“瓜洲”,鎮名,揚州南郊,在長江北岸。由此,在瓜洲和京口之間,只隔著一條長江,所以詩人就選取了“一”字,體現了選詞的準確性。
鐘山,今天的南京市紫金山,王安石在景佑四年(1037年)隨父王益定居江寧,從此江寧便成了他的息肩之地,第一次罷相后就寓居在江寧鐘山。而這首詩寫于熙寧八年(1075年)二月,是王安石第二次拜相進京之時途經金陵,泊船在瓜洲,遙望鐘山,相隔著數重山巒,可詩人卻只用“只隔”二字,極言鐘山近在咫尺,凸顯出此時詩人與鐘山的距離只是空間上的,而非情感上的,從而進一步展露出詩人心在故鄉,依依不舍回望鐘山之情。
“又”,再一次的意思,暖和的春風再一次吹綠了江南兩岸的田野。自然的四季可以循環往復,可是人生的四季能否再次陽光明媚呢?“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是說現在江南的草兒又綠了,我什么時候能夠在明月下回來看江南的綠色呢?
好像王安石不太舍得離開江寧,實在怕耽誤了江寧這大好春色。這哪里是一個政治家的抱負,哪里是一個不久之后極大影響了宋代政壇、文壇的政治家的抱負呢?實際上,作者是想說,我被征召入京變法,不是以我的意志為轉移的,但功成之后我還是會回來的,豪情和心滿意足溢于言表。
為此,此處的“春風”暗含著詩人對前途命運的一種欣喜、樂觀之情。“春風”既是寫實,又有政治寓意。“春風”實指皇恩,宋神宗下詔恢復王安石的相位,表明他決心要把新法推行下去,為此,詩人感到欣喜。他希望憑借這股暖煦的春風驅散政治上的寒流,以開創變法的新局面。
詩人之所以重視煉字,一方面是因為詩歌受到字數、平仄、對仗等形式上的影響,另一方面也是為了更好地描摹事物的特征以及更準確地表達自己的情感。成功的煉字是和煉意緊密結合在一起的。
(編輯:龍賢東)